马丁·瓦尔泽:不爱我的人无权评价我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苌苌)
 (
马丁·瓦尔泽
)
(
马丁·瓦尔泽
)
翻译过来的瓦尔泽(Martin Walser)的主要作品,除小说集《惊马奔逃》之外,还有他发表于1957年的第一部小说《菲城婚事》,他擅长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往往通过人物的自省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体现作者对人类精神的关怀。他曾经说:“我们这些读者不满足于世界本来的样子,所以我们读书和写作。谁读一本书,他就是为自己写这本书,它并不比音乐提供给演奏者的乐谱更多。”作家止庵说:“瓦尔泽是功力很深的作家。在同辈的作家中,伯尔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直面社会,格拉斯相对比较浮躁,老集中在历史的某个特定区域,相比之下,瓦尔泽是传统意义中的现实主义作家,离现实有点距离,他是对社会有所理解、有所沉淀之后的创作。”止庵说起“瓦尔泽直到晚年之前,都是比较沉稳的”,指瓦尔泽在2002年发表了令他“晚节不保”的小说《批评家之死》,在当年的德国文坛掀起轩然大波。2007年初,本刊曾邀请此书的译者、北大德语系主任同时也是瓦尔泽的研究者黄燎宇撰文介绍这本小说及背景。
此次中国之行,瓦尔泽在社科院做了一场关于《批判·认同·机趣》的精彩演讲。11月1日,在歌德学院举办的“德国之夜”关于批评界现状的讨论会上,他又与叶廷芳、汪民安、西川、李敬泽等探讨了为什么当今中国缺乏卓越的批评家。他们的观点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总体素质不行,批评家首先应该学问横贯中西,博古论今,可真有这等学问的人也不干这行,因为批评多少是个有自毁性的行业;其次,是知识分子型社会的缺失,缺乏德国那样的土壤;还有就是没有话语权,中国的批评家曾经在有话语权的时候,没有对文学的基本价值有个掌握,甘心屈于有创造力的少数。不过,最主要的是这些年来没有好作品出现。
三联生活周刊:西川说,中国没有好的批评家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型的社会,那在德国批评环境是怎样的?
瓦尔泽:在德国做批评,个人的态度很难和政治立场分开。我以前认识一个非常优秀的批评家,他写了很多关于我的恶意的批评,因为有一段时间他一直认为我是左派。他也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战后德国社会需要怀疑和批判,那个时候以及后来,我在政治上都采取了反对的姿态。我们的基本法应该保护人类的尊严,但在现实中它一直是被伤害的。慢慢地,他的批评态度有所改变,因为我后来写了反对东西德分裂的文章,他又开始把我说成是右派,又写了很多赞赏我的文章。其实,我觉得自己在这30年里没怎么变化,但公众对我的印象却有个质的转变,时代精神一会儿把我归为左的,一会儿把我归为右的,而我只是有感而发,态度是谦逊和保守的,近年更为保守一些。我有个印象,德国的批评相对英国和法国来说,确实政治倾向更浓一些。1961年,我作为联邦德国第一个为社民党写书的作家,编辑了一本叫《我们真的需要政府吗?》的书,当时虽然引起广泛讨论,但并没有产生实质的政治影响,社民党并没有赢得选举。我那时就已经意识到,政治不是属于我的游戏,我也无意当一个政治性的作家,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这么政治味浓厚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战后德国的反“反犹主义”,有时人们对犹太人问题说东不是,说西也不是,宁愿回避。您写作《批评家之死》的时候,是否有反“反犹主义”的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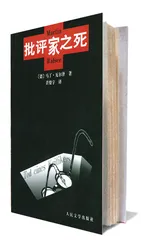 ( 《批评家之死》(中译本) )
( 《批评家之死》(中译本) )
瓦尔泽:当时这本书出来后,立刻被认为是本“反犹主义”的书。书中的主角,那位批评家碰巧是个犹太人,我写的就是个批评家,无论他是不是犹太人。我同意说这本书是本反“反犹太主义”的书,其实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是反“反犹主义”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位批评家是位非常强势的人,他总是滥用他的权力,比如利用电视媒体的宣传力量,这本书的主旨就是反对这种权力的滥用。如果说,这位批评家不是频繁出现在电视上,我也不会写这本书,因为如果在报纸上,他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他在电视上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评判一本书,通常是在观众接触到那本书之前,这里面就存在一种误导的可能。我的这本小说本来不是多么重要的书,因为这个丑闻把它炒作起来,这非常荒谬。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卡夫卡的,而且一段时间内,我只读犹太人卡夫卡的小说,所以说我反犹是非常可笑的。
三联生活周刊:鲁迅曾经说“与其被混蛋称赞,还不如战死在他手里”,您觉得和赖希-拉尼茨基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吗?
瓦尔泽:黄燎宇教授写过一个评论,说这本书是“对拉尼茨基的爱的表白”。我也在下面两句话里找到一些慰藉,一个是歌德说的“不爱我的人无权评价我”,还有是我说的,“没有对立面的东西都不是真的”。我本人经历过太多的认同,我认为,我只是从认同中才学到东西。如果认为一个作家因为认同而沾沾自喜是幼稚的,认同也是为公众做出的。一个作家不会对所有赞同的声音都会接受,还有一种他可以判断,就是那种没有理解的赞同。我从来没有真正批判过某人,总是给予一个积极的评价。我不喜欢的书,就根本看不下去。
三联生活周刊:您相信批评使文化进步吗?
瓦尔泽:批评家最直观的作用就是把一个作家捧起来,或者打压一个作家,再往后有什么意义就难说了。1998年,我在法兰克福发表了一次讲话,这个讲话也产生了丑闻,我描述像政治、教育和媒体所操纵的公众话语,在涉及德国的历史问题时总是有一些误解,我对此进行了批评。必须补充一句,我一般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发表讲话,比如获奖的时候。做完这个报告后,媒体又开始断章取义。我不想说服公众接受我的观点,我发表我的看法只是想了解他们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如果所有人都是抱着这样一种交流的态度,这样就能形成一种公众的意识层面,这对整个社会的态度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甚至发展成一种政治现实,影响政治决策。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把媒体称为“第四权力”,您认为媒体真正的作用是什么?
瓦尔泽:让媒体起到它真正的作用,这说起来有点乌托邦,媒体的存在,应该是检验社会中其他权力的运用是否合理,所以媒体应该怀着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权力的运用。这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媒体也是一种权力的话,那么谁来监督媒体呢?关于权力滥用,我有个很好的例子。在2002年,《批评家之死》还没有正式发表,我把手稿交给《法兰克福汇报》的一位编辑,问他能不能在报纸上发表。编辑周五把手稿交给老板,说周一打电话过来,但是我没等到电话,周二报纸上就出现他们主编写的一篇文章,公开地把这本书判定为一本“反犹主义”的书,并反对发表。其实这家媒体的做法是违反规则的,我就找到德国的媒体协会对它进行申诉,但没有达成共识,因为协会的头儿也是一家媒体的主编,经常给《法兰克福汇报》提供材料,他们互相认识,这是一条权力链,我无法和这种权力进行抗争。律师告诉我,你这申诉是无望的,我就觉得很无助。
三联生活周刊:有时媒体缺乏勇气行使这种批判的权力,是因为恐惧被其他权力打击,那媒体应该怎么办?
瓦尔泽:应该把矛盾的态度保持下去,如果醒过来,感觉有人恨你的话,这是一种很好的反应。谁要批判的话,就必须要毁灭?这个态度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人不可能把生活分成正确的和错误的两部分。实际上,我们应该克服的正是这种两分法。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一个批评家或者说一个公民,如何获得尽可能多的独立性?
瓦尔泽:我曾经写过一本小说名为《灵魂工作》(暂译),这本书讲的就是人类的依赖性,比如对上司的依赖和对体制的依赖,在这种依赖性中,真正的灵魂独立自主被破坏。小说中的角色是个司机,他有个非常好的老板,有个场景是他躺在床上想他的老板,但他也知道,他老板不可能同时在想他。我想说明的是,社会正常运行的条件就是这种依赖性,权力的运用是建立在这种依赖性上。20年后,我又写了本小说叫《畏惧之花》,针对这样的依赖性,得到独立的唯一方法就是金钱。必须要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独立性,而不是自由,因为自由又涉及宗教或者哲学的概念。公众可能不想听到这些——正是金钱,而不是政治、不是宗教或者哲学,是唯一可以对抗权力、获得独立自主的途径,这听起来有些野蛮,但却是现实。■ 瓦尔泽读书文学作家马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