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分析哲学与存在主义的中介的胡塞尔
作者:薛巍(文 / 薛巍)
分析哲学家开始借用现象学
特罗蒂尼翁说:“柏格森为德国人从胡塞尔向海德格尔过渡准备了条件,胡塞尔则使得法国人可以从柏格森过渡到萨特。”波伏瓦在她的自传中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个夜晚,萨特开始热衷于现象学的情形。年轻的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在柏林研究胡塞尔新的哲学方法,准备写这方面的论文。在一年时间里,他每次回巴黎都和萨特聊胡塞尔。波伏瓦写道:“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路灯饭店一起吃晚饭。我们点了他们拿手的杏仁鸡尾酒。阿隆指着他的杯子说:‘知道吗?伙计们,如果你是一位现象学家的话,你就能谈论它,并从中搞出哲学来!’听到这儿,萨特激动得脸色发白。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按照自己感受的那样来描写对象,并把这些弄成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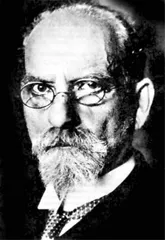
胡塞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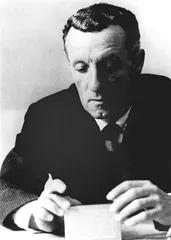
梅洛-庞蒂

海德格尔
对此,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肖恩·凯利(Sean Kelly)评论说:“如果说描述对象是现象学方法的核心,这就不难解释20世纪中晚期哲学上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两大阵营之间的分歧。毕竟,很难想象罗素会在一杯杏仁鸡尾酒面前变得脸色发白。”
一般说,英语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主要是分析哲学的天下,而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则风行于欧洲大陆。肖恩说:“显然我们不能满足于这种从国民性角度的解释,对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异同要做更加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变得更加有趣,因为这两大阵营之间的鸿沟正在自行缩小。这很不简单,想想两者之间的鸿沟以前是多么宽:直至1958年,形势还很紧张,在巴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英语国家的哲学家跟他们的法国同行吵得不可开交,当时还年轻的查尔斯·泰勒称之为聋子的对话。”
两大阵营之间上世纪中叶互相置若罔闻,如今互相有了好奇心。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有用英语写作的关于现象学的著作,美国人赫伯特·施皮格伯格在1960年出版了两卷本的《现象学运动》,随后威廉·理查德森出版了他同样厚重的关于海德格尔的著作,还附有海德格尔为之撰写的序言。但这两部解释现象学运动的著作,一个只是历史性的重建,记录谁对谁说了什么,一个只是翻译现象学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的著作。
1962年7月,哈佛大学举办了一个关于各种当代哲学的系列讲座,弗莱斯达尔宣读了题为《向分析哲学家介绍现象学》的论文。他在文章中说:“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之间,相互理解,甚至富有成效的交流,看来是可能的。而一旦这一关系确立,现象学就可以进而在分析哲学和存在主义之间起到一个交流中介的作用。”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的数学背景,使人觉得现象学具备某些精确性和逻辑严密性的特点,而它们正是分析哲学家一直孜孜以求并津津乐道的。到了今天,值得注意的是,“英美国家的学者开始借用现象学,开始从现象学的分支中寻找最可口的果实,相信现象学的果实能够给哲学提供营养”。
在分析哲学这个名称下,有各种流派,以致布赖恩·莱特(Brian Leiter)宣称“分析哲学的死亡”,因为当代英美哲学在方法和体系上是如此的多种多样,以致很难清楚地对它加以界定。但按照标准的观点,使20世纪的分析哲学获得统一性的是“语言学转向”。
语言学转向之后,哲学家们希望通过分析我们讨论相关问题时使用的语言来解决或消解哲学问题。以感觉为例,对语言哲学家来说,这类问题不应该通过思考感觉经验来解决,而应该考虑我们讨论感觉时使用的语言。一个很有影响的例子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伊丽莎白·安斯康姆通过分析关于感觉的报告中“看”之类的动词用法来研究感觉问题。显然分析哲学的这套方法不会让萨特感到激动。达米特同意,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区别就在于,胡塞尔的方法拒斥所谓的语言学转向。
近来,英美哲学至少在两个领域已经暗暗拒斥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首先是形而上学,其次是心灵哲学。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正是这两个领域的当代英美哲学家研究现象学文献的心情最为急切。
形而上学家蒂莫西·威廉姆逊说,“逻辑和想象力复杂的相互作用”引导着当前的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的核心是本质直观:观看一个东西时,我们尝试想象对象如何和现在不一样,通过本质变更建立一个视域,对象在其中改变但又不失其类型的同一性。最终,想象变更将带领我们达到不能再变更的属性,让我们看到事物的本质。正是胡塞尔的这一观点让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哥德尔在他生命的尽头深深地受到了吸引。
现象学对心灵哲学的影响更大,这首先是因为现象学研究最主要、最成功的对象便是我们自己的意识状态。长期以来,在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英美哲学忽略了这一领域。在过去10年间,主流的当代英美哲学界重现发现主观经验的重要性,在这种背景下,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和梅洛-庞蒂的著作也就跑到了英美哲学家们的案头。
面对事物本身而非分析语言
现象学致力于描述事物本身,描述活动跟哲学家们的其他工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果解释、理性的重构、先验的证明、概念分析、理论构建等。现象学认为,单纯地、不带先入之见,尽可能完整、准确地描述对象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将现象从对它们的先入之见中区分出来需要一定的训练。
可以通过感觉问题来理解现象学的特点,感觉在近代笛卡儿、洛克、休谟等人的认识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些经验主义的哲学家们相信,我们从对世界的感觉中发展出观念和思想,思想只不过是我们得自感觉的图像不够生动、鲜明的拷贝。经验主义在20世纪的继承人仍然将感觉看做呈现在心灵中的图像,这种图像随后被作为观念而加以复制、保存。在20世纪,这种图像经常被称作感觉材料。
他们认为,可见的感觉材料跟投射在我们视网膜上的物理图像是吻合的。比如,从某一个角度看过去的硬币,由于它投射到视网膜上的图像是椭圆形的,感觉材料也是椭圆形的。当这枚硬币转动时靠近或离开观看者时,我们看到的图像也相应地变化。
罗素认为,人们对感觉材料的认识是无法纠正的,我们觉得看到的是红色的感觉材料,但现实世界中跟它相应的不一定是一个红色的物体,对此我们毫无办法。
现象学认为,经验主义对感觉的分析是不准确的。胡塞尔认为,当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斜着看一枚硬币时,我们看到的也是圆的硬币。我们可以有意让自己看到椭圆的,比如闭上一只眼睛去看。但要看到椭圆形的硬币需要下特殊的功夫,以为我们视网膜上的图像是椭圆的,我们看到的就是椭圆的,这是错误的。
有趣的是,确实有人以感觉材料的方式看世界,有证据表明,一些能够根据记忆描摹出物体细节的艺术家依赖的就是这样的图像。近来有神经科学家认为,很多著名画家看物体时没有立体感。这些极端的例子说明,经验主义所说的观看方式并非常态,胡塞尔对它的拒斥是正确的。
从这一简单的例子开始,胡塞尔对感觉经验做出了更多的观察。他发现,我们倾向于以三维的方式感知物体,观看一棵树时我们会感觉它的体积。感觉材料理论很难解释三维的视觉经验。一些感觉材料论哲学家,像罗素,努力把体积感还原成一系列关于对象的观念。胡塞尔反对这种做法,因为我们可以相信一个物体只有一个面(比如在看电影里的建筑物时),但仍感觉它是三维的。
胡塞尔像一位天才的诗人一样,在他对人类经验的描述中揭示出其以前没被注意到的侧面。这一方法让他的学生感到非常神奇,他们把对胡塞尔关于感觉和意识的描述扩展到对自欺(萨特)、怨恨(马克斯·舍勒)等各种道德情感的描述。梅洛-庞蒂曾经概括道:“现象学的任务是揭示世界和理性的神秘。这项任务像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瓦莱里和塞尚的工作一样艰苦,因为它是一项非凡的任务,需要同等的专注,同等的把握世界和历史的意义的意愿,由此它融入了现代思想的共同努力。” 哲学研究萨特现象学哲学存在主义分析哲学胡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