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利眼饲养员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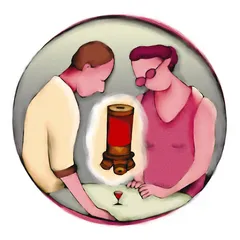
酸溜溜的老爹艾本斯坦写了本《势利》,以解读当代美国上流社会,或者说,所谓上流社会。其中有一章叫做《势利眼的餐桌》,集中牢骚了美国当代势利眼们的食物状况,以及他们是被什么样的餐饮风气喂肥的。
艾本斯坦老爹说,其实这股“食物势利眼”的风气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打那个时候起,知识分子光谈论电影就显得不够尊贵了,他们把罗伯特·奥尔特曼(Robert Altman)、亚瑟·潘(Arthur Penn)从充满热情、喋喋不休的语句中挪走,填充上最近新开的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和科西嘉风味的餐馆的名字。如露西斯·比碧这样的食物评论家已经开始以抱怨美国食物普遍质量低下的态度来赢得各色读者的心,而某些在欧洲住了几天或几个月的美国籍小说家,如玛丽·麦卡锡,则已经公然以最势利的语气,不停地诉说对美国超市的极端厌恶,把美国人吃的白面包说成不亚于心灵毒药的东西。
艾本斯坦回忆说,在过去30年左右的时间里,有几件事极大地丰富了美国人菜单上的内容:越来越多的国外旅行;国外食品的被引入,且人们对它们的兴趣也越来越大;超级市场的发展;素食主义的传播;全民对健康饮食的关注;对营养和保健食品从未停止过的担忧。“记得我在芝加哥某条大道边的一家叫加不里尔的餐馆里第一次尝到比萨饼,当时觉得自己就像在天堂一样。而仅仅过了20年,每一个人都能毫不费力地说出Pesto(香蒜酱)、Marsala(马沙拉白葡萄酒)和泡制白松露油。又有谁能想到,最后大家认识的意大利油醋的品种超过了美国州的数目,而你知道的顶级初榨橄榄油的品牌一定比真正的处女还要多。”
而如今,那一段历史仿佛隐约在中国当代重演。当餐厅和食物的选择越来越多的时候,美食不幸就沦为了势利眼的重要武器,那些被认为是“高级食物”的东西被用来玩弄颓废、显示品位、展示对生活细节的热爱,或者成为某人与欧洲大陆之间的联系。餐馆越来越成为一个让人出风头的地方,而不是单纯享用自己喜欢的食物。所谓的餐厅评论家层出不穷,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拥有懂得美食的背景和渊源,因为“祖上是做官的,经常参加某某名人的饭局”,或者“从我往上数四代就开始去欧洲留学”,但评论食物的出发点却是挑剔和炫耀,很少从他们的嘴里听说本地的哪种东西是好吃的。中国人以前对食物也有虚荣心,但那不失为一种天真烂漫的铺张浪费,就好像罗马时期的宴会上会出现将较小的鸟依次塞入更大的鸟的身子里烹调这样的玩意儿一样,中国人则是通过满汉全席(食物的多)、用萝卜雕的龙或者用西瓜雕的灯(让你眼花缭乱倍儿感豪华)来展示其纯朴可爱的好大喜功的心情。当时如曹雪芹般能制造出“茄鲞”这样冷感而令人目瞪口呆的菜肴的人还没有几个,所以真正的具有现代意义的餐桌上的势利眼仍未发展成气候。而如今,那些强调“我对味精过敏”、“你们餐馆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盐”,以及宣称自己特别钟情某些新式烹饪法或广东口音侍者的势利眼比比皆是。且他们新一波的浪潮则是,请人到自己家里来吃饭,由私厨烹饪,或是展示自己刚从某高级烹饪学习班向某米其林带星厨师学来的一道小菜。
“好的食物是这个世界中上帝最美好的祝福之一,但是,就好像性一样,要陷入危险,最快的方法就是过分谈论这件事情。”艾本斯坦老爹如是说,也援引了小说家玛丽·李纳特的话:“某些人是食物和红酒之王,食物确实是个好东西,但要以此谋生就有点过了,他会一直嗅个不停,老实说,那样的晚上可不好过。”我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乐于有一顿丰盛而美味的晚餐,因为食物确实能抚慰人的心灵,但同时,我们大多数人也都不会喜欢这样的饭桌:有个从头到尾把脑袋放在红酒杯里猛吸的品酒师,或是没有喝到她要的牌子的矿泉水就忧愁到不行的贵妇,又或是面对食物的一点点瑕疵就要把主厨从后厨叫出来以法语进行训话的法国大菜专家。
跟朋友吃顿好饭,才是真理。■(文 / 殳俏) 势利眼饲养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