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话是谁发明的?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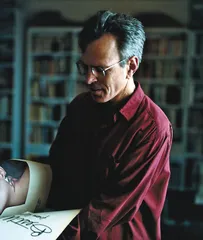 ( 吉姆·霍尔特
)
( 吉姆·霍尔特
)
读大学时,美学课上老师无奈地说“美学不美”。大学里没有专门研究笑话的课程,不然老师也会说,关于笑话的理论并不好笑。英国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写道:“笑跟食、色一样,是人类社会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但同时它又具有文化和历史的特殊性。”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笑,不管他们是什么民族、用什么语言,笑声都是一样的。而且,他们几乎都用一模一样的字词来表达笑声。在阿尔巴尼亚语中狗叫声是“ham ham”而不是“汪汪”,在匈牙利语中猪叫声是“rof rof”而不是“哼哼”。甚至灵长类动物也会笑,达尔文率先指出,亚里士多德错误地以为人类是唯一会笑的动物。打那之后,很多学者挠黑猩猩的腋窝、观察它们的玩耍,确认它们也会笑,或者接近于笑。人类笑声是呼气时发出的,黑猩猩吸气时也会发出笑声。这一区别也许非常关键。
但在生理刺激之外,笑话、漫画、图片和滑稽表演引起的笑就不一样了。美国人觉得好笑的东西,英国人不为所动,100年前的漫画也不再令今人觉得好笑。笑声无法穿越空间、时间、年龄甚至族群障碍。
如何解释生物学上笑的普遍性和文化上的差异性呢?理论家和科学家们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他们指出胳肢引起的笑并不是反射性反应,胳肢自己几乎不会发笑。意在威胁而非善意的胳肢也不会让人笑,只会让人尖叫或落泪。结论就是,胳肢和笑之间的联系是社会性的,而非生理的。
另一方面,有很多关于笑的理论,试图说明笑的共同点和机制。吉姆·霍尔特在《你已经听过的话就打断我》一书指出,大部分笑的理论能解释若干种笑,但解释不了所有种类的笑。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古代哲人认为,笑话表达的是优越感以及取笑和奚落别人。这种理论能够解释跟种族、宗教、醉鬼和倒霉蛋有关的笑话,但解释不了为什么双关语会让我们发笑。迈伦·科恩(Myron Cohen)有很多关于犹太人的段子,比如,一位犹太祖母在海滩上照看她的孙子玩耍,突然一个巨浪把他卷进了海里。她恳求上帝把她唯一的孙子送回来,一个巨浪过来,她的孙子被冲回了岸上,毫发未损。她抬头看着天空说:“他刚才是戴着帽子的!”一位客人问餐厅老板马克斯为什么餐厅边上没有停车场,马克斯轻蔑地说:“笨蛋!我要是有停车场的话,还用得着开饭馆吗?”
在近代更为流行的是“滑稽理论”,认为笑源自范畴或意义上的乖离。神经科学家拉玛·钱德朗这样解释笑的起源:当一群人在丛林中,明显感到受到威胁,这群人中第一个注意到实际上并没有威胁存在的人会发出笑声。它是有传染性的,于是所有人都笑了出来。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当一种紧张的期待突然消弭于无形时就会引人发笑。他举例说,一个英国人打开一瓶啤酒,泡沫涌出时,一个印度人感到很惊奇,人们问他为何如此吃惊时,他回答说:“令我惊奇的不是有泡沫出来,而是你们是怎么把它放进去的。”这种理论的问题在于,没有进一步指出为何乖离会让人觉得好笑,为何有的乖离好笑,有的并不好笑。所以弗洛伊德的“释放理论”更加合理,受到压抑的想法和冲动得到释放,所以人会发笑。这一理论的问题在于,按照弗洛伊德的逻辑,笑得最欢的应该是那些性压抑最严重的人,因为一旦不受压抑时他们释放出的能量最大。但事实与此相反,英国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的研究证实,最放荡的人笑得最响亮。
 ( 吉姆·霍尔特的《你已经听过的话就打断我》 )
( 吉姆·霍尔特的《你已经听过的话就打断我》 )
霍尔特在书中追溯了笑话的历史。他说,经典笑话最早出现于古代希腊和罗马。古希腊神话中的帕拉墨得斯发明了很多实用的东西,数字、钱币、灯塔、三餐,还有笑话。弗洛伊德在《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中引述了一个笑话:一位皇家子弟在他的领地巡游时,看到人群中有一个人跟自己长得很像。他把那人召过来问道:“你妈妈以前在宫里当过差吗?”那人回答说:“没有,殿下,但我父亲在宫里当过差。”这个笑话现存最早的版本出现于奥古斯都时代的一个笑话集。
《连线》的记者问:“新的笑话来自哪里?”霍尔特回答说:“过去我所有的笑话都来自华尔街。现在有了网络,笑话到处都是但又哪儿都找不到。但笑点都是文化上的、数百年来反复以不同面目出现的观念。”■(文 / 小贝) 笑话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