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72小时
作者:袁越 ( 5 月 16 日清晨10 岁的蒋禹琦与同班另外两名同学被困 80 多小时后获救 )
( 5 月 16 日清晨10 岁的蒋禹琦与同班另外两名同学被困 80 多小时后获救 )
粗壮的手指与生命之路
5月15日早7点,成都市一家广告公司叫张文龙的老总开着自己的越野车载我去灾区。他是成都车友会的成员,他们组织了30辆车,分成3个车队,载着自费采购的食品和水运往彭州、什邡和绵竹等重灾区。虽然时间还早,可公路上已经行驶着很多军车,它们和一支支打着“抗震救灾”等旗号的志愿者车队一起全速驶向灾区。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绵竹。绵竹位于德阳市,距成都大约100公里,街道上到处是前来救灾的士兵和运送物资的大卡车。起码从表面上看,绵竹市区受灾并不是特别严重,倒塌的房屋不是很多。我们离开绵竹继续向北行驶,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路边的房屋大量被毁,越向北越严重。又开了大约15公里后,车驶进绵竹以北15公里处的汉旺镇,我立刻感觉像是进入了一个灾难片的现场,空气中迷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烟尘把天空染成了黄色。路边的房屋倒了很多,没倒的也都七扭八歪的。街道上临时搭建了一排3平方米的蓝色专用救灾帐篷,每座帐篷要睡8个人。
汉旺的救灾指挥部设在汉旺广场,广场对面就是一处倒塌的居民楼,一群武警士兵正在废墟上奋力挖掘。家属们戴着口罩,焦急地站在一边守望。现场虽然有一台吊车,但因为钢筋和水泥板纠缠在一起,不敢轻举妄动,官兵们只能用手一点点清理碎砖。距离地震发生马上就要72个小时了,时间不等人。
汉旺镇坐落在山脚下,通过一条盘山公路和山里的清平镇相连。从清平再往北可以到达茂县——一个目前只有空降兵才能到达的重灾区。我想去清平看看,却被一个当地警察拦下。“清平走不通。”他告诉我,“两座山垮了,把夹在中间的公路完全封死了,你走都走不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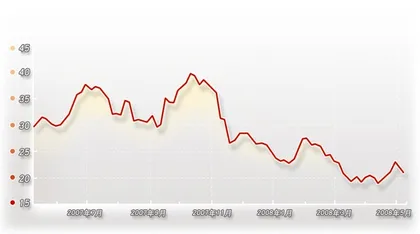 ( 5月14日,绵竹汉旺镇的救援人员正在安放一位遇难者的遗体
)
( 5月14日,绵竹汉旺镇的救援人员正在安放一位遇难者的遗体
)
“昨天有3个人从山上爬下来,结果被山上掉下来的石头砸死一个。”旁边一位老乡说。
公路就是生命,这次抗震救灾战役遇到的最大敌人就是道路不通。
( 5月19日晚,成都市民在天府广场点燃蜡烛祭奠遇难者 )
我不甘心,找到一个名叫代荣的当地人,他同意用他的小面包车载我抄小路上山看看。“我今年22岁,经历过洪灾、冰雹、龙卷风和霜冻,但地震是最厉害的,躲都没法躲。”他一路上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代荣开车绕过警察的关卡后,终于上了山,沿着一条布满碎石的盘山公路向山上开去。右侧的高山和公路几乎成直角,山坡因塌方而露出黄色的泥土,从山上掉下来很多大石块,直径最大的有3米多,把公路砸出一个个大坑。我们只走了十几分钟就被警察挡住了去路,前面塌方,走不过去了。一排士兵背着水壶急速从身边走过,看来他们准备徒步进山。
 ( 5月17日,志愿者在绵竹遵道镇向受灾群众分发食物
)
( 5月17日,志愿者在绵竹遵道镇向受灾群众分发食物
)
我对自己的登山技术没有信心,只好掉头回汉旺。正在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里时,一个请求搭车的年轻人给我指明了方向:“我舅舅昨天刚从清平跑出来了,他是从坑道里自己挖出来的。他叫胡加仑,小名胡有娃,住在安县桂花村桂花九组。”
我立刻知道我要去哪里了。
 ( 胡加仑就是用这双手为自己打通了一条生命之路
)
( 胡加仑就是用这双手为自己打通了一条生命之路
)
桂花村位于汉旺镇所在的射洪县和安县县城之间,距汉旺大约10公里。这个村虽然行政上属于安县,但距离安县县城有45公里。从汉旺到桂花村之间的乡村公路基本保持完好,但都是小路,大卡车很难开进去。我看到沿途大部分民房都已损毁,农民们在院子和地头搭起了简易帐篷,依靠醒目的红、蓝、白塑料布为一家老小遮挡风雨。
桂花村实在太小了,地图和路标上都没有它的踪迹,就连附近的村民都很难说清具体位置。我们一路问过去,在走了很多弯路后,终于到达了桂花村九组。
 ( 5月15日,由于缺乏饮用水,安县黄羊村的村民只能用河水做饭
)
( 5月15日,由于缺乏饮用水,安县黄羊村的村民只能用河水做饭
)
“胡有娃!有人来找你啦!”村里的小孩子几声大喊后,一个身穿棕色衬衫的小个子男人急匆匆走过来。听说我从北京来,他腼腆地搓着双手,有些不知所措。我注意到,他的手指粗得像10根胡萝卜。
“我很幸运,活着回来了。”他缓缓说,“要不是我当时在坑道里,也许就被砸死了。”
 ( 5月17日,绵竹遵道镇,孩子把从家里抢出的几件衣服紧紧抱在怀中 )
( 5月17日,绵竹遵道镇,孩子把从家里抢出的几件衣服紧紧抱在怀中 )
“我老公要是死了,我们家就完了!”胡加仑的妻子一边哭一边拉过一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对我说,“这是我儿子,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没了老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胡加仑看着妻子,面容凝重。他努力地用半生不熟的四川普通话向我讲述他的逃生故事。
“我在清平一个磷矿工作,每个月能挣1000多块钱,比种地强多了。我被分在131A组,同组的还有邓明和邓建两兄弟。当天我们组在海拔1247米的地方作业,距坑道口大概有1000多米吧。地震的时候可怕极了,我一下子撞到墙上,又被反弹回来,撞到后面的墙上。多亏坑道很小,也就3平方米吧,这才没被撞死。震完后,通向上面的道路完全被封住了。我们3人想了半天,决定不能指望外面来人救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于是我们开始沿着水平线挖。我们3人排成一排,前面的人挖下来的土传给后面的人,一点一点往前挖。我也不知道挖了多少米,最后终于见到亮了。”
 ( 陈坚正在废墟下坚韧地等待着救援。遗憾的是经7小时营救获救后,终因伤势过重故去
)
( 陈坚正在废墟下坚韧地等待着救援。遗憾的是经7小时营救获救后,终因伤势过重故去
)
“我们出来的时候大概是第二天下午,3个人又累又饿,但还是决定立刻往山下跑。当天余震不断,山上不断有石头飞下来,我们必须很快躲到大石头后面,否则肯定被砸死了。我们跑了2小时跑到龙庙,实在跑不动了,就在龙庙过了一夜。第三天一早我们继续往山下跑,可是因为滑坡,山里都是碎石头,根本没有路。我们3个连滚带爬,直到下午14点才下了山,回到了家里。”
“清平镇还有多少人没下来?”我问。
“我也不清楚。清平镇大概有1万多人吧,房子都毁了。我们的矿上也有很多工人,当时大部分人都在井下,只有很少的人活着出来。”
胡加仑对于很多数字的记忆并不准确,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他对自己创造的奇迹也常常语焉不详。不过,他只是一个常年工作在井下的矿工,还能怎么要求他呢?
我们谈话的地方是他家客厅。两层的红砖楼,居然看不出一点被震坏的痕迹。“这房子是我用打工挣的钱盖起来的,我们九组只有我这间房子没坏,其余的都倒了。”胡加仑说,“我这次死里逃生,真得感谢我的老婆。以后我们要好好过日子,钱挣多挣少无所谓了。”
采访结束后,我和胡加仑握手道别。他的手指像木头,硬得扎人。就是这双粗糙的大手,为主人挖出了一条生命之路。
路是死的,人是活的
“记者同志不要走!你来我家看看吧,帮我们传递个消息。”一位打着赤膊的中年人见我从胡加仑的屋子里出来,立刻上前拦住我,“我们这里断水断粮3天了,请你帮我们呼吁一下,让政府给我们送点救灾物资吧。”
当时救援队还未能顾及这里,胡加仑的门前聚集着20多个村民,互相争着说情况。一位老大妈哭着对我说:“我儿子出去打工还没回来,我家的房子又全塌了,我可怎么活啊?”一位老大爷拽住我的胳膊央求道:“你给我家拍张照片吧,我的房子全倒了,所有的粮食都被埋在下面了,我不敢去挖,只能去田里头捡东西吃,再这样下去就活不了了。”我看到他手里拿着几个刚摘下来的豆荚,正在剥里面的青豆吃。
村民们簇拥着我在村里转了一圈。这里果然像他们说的那样,除了胡加仑家,没剩下一间好房子。有不少房子虽然还立着,但已经完全变形,不可能住人。一堆堆廉价的瓦片和木桩子堆积在一起没人清理,几只鸡在瓦砾堆里觅食,但更多的鸡被砸死在鸡笼里挖不出来,空气中有一股浓重的腐尸味道。
“我爷爷被掉下来的横梁砸死了。”那位打赤膊的人指着一片废墟对我说,“我们没地方火化,只好就地埋了。”这人叫毛运科,他所有的衣服都被埋在瓦砾堆里,这几天只好一直光着上身。他告诉我,桂花村九组一共120人,只死了2个老人,其余的人地震时都在田里干活,逃过一劫。
“地震后都3天了,没人给这里送过吃的。”另一位村民抱怨,“不过我们最需要的是水。到现在只有一个志愿者来过我们村子,带来的水只够每10个人分一瓶。”
“你们平时怎么喝水呢?”我问。
“我们平时喝井水,地震后井水有毒,喝不得。”他当场给我演示了一下,用手泵压出的井水像黄泥汤,即使没有毒,也要沉淀好一阵子才能饮用,更何况由于地震造成的地壳运动,地下水中很可能含有某些有害的矿物质,“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喝稻田里的灌溉用水,再这样下去要发瘟疫了”。
村民带我去看稻田,不少田里的水都干了,秧苗东倒西歪,还有几块田明显不平,一边高一边低。村民解释说,地震把地面给震歪了,所以才会这样。他们还带我去看了一个地震造成的地洞,稻田里的水从这里流了下去,整块田早已干涸,肯定颗粒无收。“我们不敢再下田种地了,怕掉下去。”毛运科对我说。
村子里还种了不少小麦,眼下正是收割季节,金黄色的麦穗煞是喜人。可村民们告诉我,如今这里都时兴雇用外地来的收割机,地震后他们都跑了,村民们也根本无心收割。
“我的村子也是这样。”司机代荣对我说,“今年的春小麦都烂在地里,白种了。”
离开了桂花村,代荣又带我去他舅舅家看了看。这里位于绵竹市的永中村,也是一个重灾区,救援队因为都在救人,政府来送过一些方便面,但带来的水很少,只有75岁以上的老人才能分到一瓶。所幸他家的井水并不是很黄,沉淀一下,再煮开了勉强可以喝。他家的主要问题是缺粮,因为储藏粮食的那间屋子没有塌,但门已经严重变形,没人敢打开那扇门。“我真希望那间屋子塌掉,反正将来肯定是推倒重建,震塌了反倒省力了,还可以把粮食挖出来吃。”代荣的舅舅对我说。
他舅舅在外打工多年,5年前花2万块钱建了3间瓦房,可现在一家5口只能挤在一个棚子里,外面用毯子盖住。据他说,红、蓝、白塑料布原来每米8块钱,现在则是80块,他们买不起。“现在要是按原样盖3间房,少说要花7万块。我打工每年只挣万把块钱,要哪年哪月才能攒够这笔钱啊!”
“我今天刚送一户人家去汽车站,全家移民去外省打工,把老人也带走了。”代荣告诉我,“现在种地赚不到钱,房子再没了,就没理由再住在这里了。”
从永中村出来,我决定继续在附近转转。我看到一位志愿者开着自己的车子来到一个小村庄,给受伤的村民治病。我看到一家3口把自己的车停在路边,车后面贴了一个牌子,上写“手机免费充电”。我还看到一辆从成都开来的面包车停在一个名叫泉新的小村子,村民们排着队从志愿者手里领取饼干和水。一位村民哭着对我说,村里一位受伤的老人至今没有药品,只能等待志愿者送。
泉新村距离汉旺镇的“救援物资调配中心”只有10分钟车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志愿者的车辆排成长队等待卸货,仓库里堆满了他们运来的各种物资。政府派来的运输车辆一上午运出去8车,但还是赶不上志愿者的热情。另外,政府调集的运货车辆都是大卡车,许多乡村小路开不进去,那里的村民只能寄希望于志愿者。
志愿者的大量出现是这次地震和唐山地震最大的不同。那时肯定也有无数好心人,但没有能力前往唐山抗震救灾。32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大批先富起来的老百姓终于具备了这个能力。如果说政府是通往灾区的大路,那么这些志愿者就是小路,他们主动肩负起为政府分忧解难的责任,有效地弥补了政府工作的缺漏。
志愿者,一个多么美好的字眼。一个拥有无数志愿者的国家是震不垮的。
北川之夜
离开了汉旺,我搭志愿者的车穿过安县进入北川羌族自治县。一位骑摩托车的当地人自愿给我们带路,我们说了声“谢谢”,他不自觉地向我们行了一个军礼。
北川县城很可能是这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幸好这里距离平原不远,道路很快就修通了。政府在距北川县城5公里左右的地方开始设卡,一连设了好几道,由武警和军队士兵分别把守,没有政府开的采访证不让进。
晚上大约19点左右,我终于搭上重庆电视台的采访车“混”了进去。距离县城越近,车就越多,救护车、运输车、采访车、军车、大客车等各式车辆把只能容纳两条车道的公路挤得满满的,大家只能缓缓移动。满身尘土的救灾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从车缝中匆匆走过,队伍中夹杂着不少老百姓和记者,大家戴着口罩,遮挡空气中呛人的尘土。
我搭乘的采访车在距离县城3公里远的地方就走不动了,我下了车,随着人流向县城方向走去。途中经过北川中学,地震时大约有2000多名学生正在学校上课,据说只跑出来几百人。“北川抗震救灾指挥部”就设立在中学操场上,由绵阳市的副市长亲自担任抗震救灾总指挥。
道路从这里开始基本上就中断了,只能步行。工程兵们正在抢修公路,救援人员只有从旁边一条小道下山。我发现沿途大部分楼房都倒塌了,没倒的也都发生了严重变形。从山上滚下来的大石头把很多原来停靠在路边的汽车和三轮车砸了个稀巴烂,也把进城唯一的一条公路给堵住了。我小心翼翼地在碎石间穿行,还要时刻注意不踩到停放在路边的遇难者尸体,他们大多已经被装进了绿色塑料袋。就这样走了大约2公里,终于进入了北川县城。
县城坐落在一个狭窄的山谷里,绝大多数房屋都已经垮掉了,碎砖烂瓦堆积成一座几十米高的垃圾山。我看见地上散落着一沓打印纸,捡起来一看,居然是一份《北川羌族自治县民族地区财政政策落实情况调研报告》。读后才知,北川是古代英雄大禹的降生地,1953年被定为“革命老根据地”,1986年被定为“省定贫困县”,2003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北川羌族自治县,今年是该县成立5周年。
北川全县一共有16.1万人,其中大约有1.3万人居住在县城里。放眼望去,四面环山,可以想象地震前这里应该是一个仙境般的世外桃源。可现在环绕县城的山体很明显地发生了大面积滑坡,石块和泥土把建在山脚下的城区整片整片埋在了下面。县城被湔江一分为二,由一条被震歪了的铁索桥相连。如今河道已被泥石流堵住,原本奔腾的河流变成了一个安静的悬湖,墨绿色的湖水上漂浮着大量杂物。
此刻是5月15日晚上19点半左右,天就要黑下来了。我所在的半边县城出奇的安静,但河对岸还能看见几处灯火。我冒险走过铁索桥,摸黑穿过一片干涸的河滩,手脚并用地爬上了一座50多米高的瓦砾堆,顺着灯光来到一处救援现场。5名来自江苏省消防总队的消防队员正在试图用一架小型千斤顶顶起水泥预制板,救出被压的一位26岁的年轻人名叫陈坚。他的双腿被3块水泥预制板压住了,动弹不得。
“陈坚,坚持住!”四川电视台的一名女记者不断地跟他说话,为他鼓劲。一名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正在用手机向全国听众直播抢救过程。据他们介绍,陈坚是在当天下午14时左右被消防队员发现的,此时距离地震发生正好过去了72个小时。消防队员立刻展开救援,但由于预制板太重,消防队员们连续奋战了5个多小时,仍然没有把陈坚救出来。
陈坚是来北川打工的,虽然他3天3夜粒米未进,只喝了一点水,但他下午被发现时神志依然十分清醒。四川台拍下的录像记录了他对记者说过的一段话:“我说实话,头天晚上我真的真的坚持不过去了,我很想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是我回头一想,唉,我不能,我不能失去他们。说实在的,我不想放弃我家里面的任何一个人,所以说我要坚强……我也只有坚强,我必须要坚强,为每一个珍爱我的人,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我觉得我要对得起他们,我要对得起他们为我付出的那么多的好。我希望你们大家也一样,不要在任何的困难面前吓倒!”
天渐渐黑下来,消防队员们不时地把头探进废墟中查看情况,商量对策。为了省电,几名记者都暂时关掉了机器。晚上20点后,突然废墟堆上方传来一阵欢呼声,一名消防队员传来喜讯,又有一人被救了出来。后来得知,被救的女孩叫刘行,今年22岁,是四川农业大学4年级学生,此次她利用实习的机会回家探亲,地震时和奶奶在一起。发现她的是3名志愿者,当时她奶奶已经去世了,而她在被救出来后神志依然十分清醒。
21点08分,一名消防队员终于把千斤顶放在了一个正确的位置,顶起了预制板。几名消防队员立刻冲下去抓住陈坚的上身,拼命把他拽了出来。在摄影灯的照射下,我看到他的脸上罩着一层土,伤口留出的血早已结成了痂。他虚弱地趴在地上,不断呻吟着,但神志似乎依然清醒,还能回答记者的提问,甚至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手机对全国听众说了一句:“我能坚持下去!”
这十几名来自江苏的消防队员为救陈坚,奋战了6个小时,早已筋疲力尽。为了节省电池,很多人关掉了头灯,现场一片漆黑。幸好月亮升起来了,朦胧的月光为我们减轻了些许孤独感。一名消防队员用对讲机向总部发出了这个好消息,并请求担架支援。等待期间,四川电视台的女记者不断地跟陈坚讲话,鼓励他坚持下去。大约半小时后,几名消防队员抬着担架赶到了,可是,在场的消防队员连把担架撑开的力气都没有了。听说这里人手不够,江苏消防总队的总队长牛跃光亲自赶来帮忙,随他前来的还有一名向导,据说是北川县人大副主任杨天德。
21点30分,大家终于把陈坚抬上担架,用绷带固定住,然后消防队员们开始收拾工具,准备撤离。救援工具非常重,一个便携式钻头就有将近100斤重,一般的女孩抬都抬不起来。牛跃光说:“如果有人帮忙抬一下就好了,大家都累得没劲再抬人了。”
21点40分左右,大家在向导的带领下开始往回走。由于周围太黑,向导自己也分不清方向,一开始他带着大家上山,准备和救援刘行的队伍汇合,一起从南边下山。可走了一段大家发现走不通,又折返回来,准备冒险从一个陡坡直接下到河滩。我们排成一排,小心翼翼地踩着碎砖头和水泥板往下走,还要时刻提防不要被突起的钢筋绊倒。突然那个女记者一声大叫,然后大哭起来,原来她在黑暗中踩到了一具尸体。
大约23点左右,大家终于下到河滩。我突然感到大地摇晃了一下,之后从废墟堆上传来一声巨响,大概是什么东西被震掉了。我觉得自己十分幸运,因为我们刚才就是从那些倾斜的屋檐下走过来的。
可是,刘行却开始出问题了。她不停地哭,说自己肚子很疼,最后她拼命用最后的一点力气请求我们为她翻个身。我和一名消防队员帮她翻身,我看到,她面容姣好,似乎没有受伤,但脸色惨白,嘴唇发黑。我问现场唯一的一位军医,为什么不立即为他俩输液。军医回答说,下午输过了,光是陈坚就输了1000毫升,把带来的生理盐水都用光了。
休息了几分钟后,几名消防队员用一块门板抬着刘行往回走。我落在后面,却听到四川电视台那个女记者高声喊起来:“陈坚,你醒醒!你醒醒!”军医连忙走过去,发现陈坚已经没了呼吸。他立刻掏出一块纱布盖住他的嘴,开始为他做人工呼吸,并使劲按压他的胸腔,陈坚始终没有反应。最后军医用手电筒仔细检查了陈坚的瞳孔,冲大家摇了摇头。
我看了一眼手表,此刻是2008年5月15日晚上23点25分,陈坚在坚持了3天零9个小时后,终于和这个世界说再见。大家围成一圈,默哀1分钟。女记者拉住陈坚的手,一边不停地喊他的名字,一边号啕大哭。军医用纱布为陈坚清洗脸上的灰尘,然后拍了拍他的脸,对他说:“都坚持到最后了,你傻子啊!”
大家用一床棉被裹住陈坚的遗体,把他永远留在了北川。
快到零点的时候,我终于走出了县城,回到了马路上。此时还在工作的人已经很少了,四川省红十字会搭的两个急救帐篷还有人在值班,帐篷前放了几把椅子供人休息。我坐下休息了一会儿,听到一位医生在一旁叹气。过去一问,才知道刚刚被抬上来的刘行也死了。
“抬上来的时候就没气了,我们实施了20分钟的急救,也没能挽回她的生命,太可惜了。”
我呆坐在椅子上,感觉所有的力气都用光了。我本想打个盹,却怎么也睡不着。我的脑子里出现了大量幻觉,总觉得此刻我仍然在废墟上行走,而我的手机却一直在响,我刚要去接,却一脚踩空,掉进了废墟……其实,为了省电,我的手机早就关机了。
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凌晨4点,我还是睡不着,索性站起身,和正在值夜班的医生们聊起天来。刚才那位治疗刘行的医生名叫梁忠军,来自山东烟台,另一位值班医生名叫范宁,来自香港地区。两人都有超过10年的临床经验,这次都是作为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来到北川。北川的管理权归总指挥部,据说他们派了军队医疗队下到县城,所以没有让红十字会的医生们下去。
“这里的所有人都很努力,但是相互间协调得不够好,需要总结经验。”范宁说,“比如,这里应该设立一个救护车专用通道,可是现在这里杂车太多,很多时候都只能用担架往外抬。救人的时候,时间就是生命,必要时甚至必须动用直升机,否则就来不及了。”
范宁大夫还告诉我,对被埋了很长时间的伤员来说,一旦救出来,必须立即打通静脉(就是输液),有时需要输液1万毫升以上。光输液还不够,如果病人身体的一部分被压得太久造成坏死,则必须立即把这部分肢体进行包扎,否则坏死的肌肉释放出来的肌红素等蛋白质,以及钾离子等电解质就会随着血液循环进入内脏,导致肾脏或心脏功能衰竭。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病人几分钟内就会死去。
“你看这次有很多病人被压着时还好好的,一旦被救出来,很快就不行了,原因就在这里。”范宁补充说,“如果看到明显的肌肉坏死,有时光包扎都不管用,必须立刻截肢,才能保住性命,可惜我们这里条件简陋,很难做到。”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病人一旦被救出来,很容易兴奋,这会加速病人的体力消耗。”坐在一旁的梁忠军补充说,“很多电视剧里描写救援,旁边的人都在不断跟病人讲话,鼓励他坚持下去。他们的本意当然是好的,但是这时候病人的身体是非常虚弱的,他们最需要的是安静,不要过多地去刺激他们。”
我们聊了很久,我的心终于平静了下来。他们坦诚地对我说,他们早已习惯了死亡,面对病人的时候不再轻易动感情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冷静,以便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话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真的很难。
新的一天
第二天早上,我再一次下到北川县城,在初升的阳光下最后一次看看这座城市。我知道,在这里原样重建很不现实,北川很可能将永远地从地图上被抹去。
一群难民模样的人从山上走了下来,他们衣衫褴褛,随身只携带了很少量的东西。原来他们是住在山上的农民,地震后一直不敢下山,熬了3天后弹尽粮绝,只好冒险下山逃生。
一排排士兵扛着铁锹从他们身边走过,营救还在继续。几个志愿者爬到一处废墟上,不断地喊着:“这里还有人吗?这里还有人吗?”
这声音在北川的山谷间回响,经久不息。 陈坚72小时北川中学生命北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