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教授的寻妻奥德赛
作者:苌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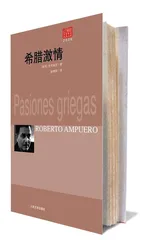 ( 《希腊激情》
)
( 《希腊激情》
)
小说《希腊激情》的故事很简单,布鲁诺教授原籍智利,因为政治原因辗转来到他心仪的美国。定居后他娶了位同样来自南美洲的理想妻子,好不容易熬到在学界立稳脚跟,女儿上了大学,他开始憧憬安逸的晚年的时候,妻子却离家出走了。妻子在电子邮件中告诉丈夫,不要等她了,她不会回家的,请别再费心找她了。理由是“我需要时间和空间寻找自我,自由支配我的生活”。布鲁诺以前对家庭有些心不在焉,长期奉行性和爱分开的双轨制政策,有过几次外遇,并都得到了妻子的宽容。但这次妻子来真格的了,他有些傻眼了。彼时布鲁诺正经历中年危机,对妻子的话,他感到难以理解,但只有行动起来才能阻止自己胡思乱想,于是踏上了漫长曲折的寻妻之旅。
故事套用了荷马史诗《奥德赛》的框架,回家的路途漫漫,布鲁诺和奥德修斯同样相信——人生可以利用其他女人寻找快乐,即使并不放弃自己对珀涅罗珀的爱情,当然他并不如奥德修斯那般智勇双全。但小说紧紧扣住了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在物质的满足很容易解决的情况下,人的精神和道德观却越来越空虚迷茫。布鲁诺的生活方式在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都具有代表性,如何平衡道德和生理的取舍?或者像布鲁诺那样不被人为制定的道德观所束缚,但又如何在自我享乐和伤害他人之间做取舍?是解决生活中的精神困境,还是随波逐流?小说的另一个主题是逃避现实,家庭对于布鲁诺就像出家人的山,现实中问题层出不穷,一个学者远不如政客领袖的身段来得灵活,变节的速度、适应现实的能力远跟不上后者,对于不如意的事情,尚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里逃避到山上,以求平静,但山上出事了,他只能往山下走,从此明白,其实无路可逃。
除了“权力就是春药”的老说法以外,一项科学研究表明,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比如艺术家、诗人——知识分子如果有胆儿的话,可能也包括他们——更容易有多个性伴侣,表面上是因为他们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决定的,但也因为他们分泌的多巴胺高于常人。随着年龄增长,多巴胺的分泌日益依赖于外界的刺激,比如通过寻找挑战与激情,而已经变得大胃口的多巴胺接收器也就需要更多的激情来满足。所谓“喜新厌旧”其实符合人之常情,但很多时候有婚姻法和道德观的束缚,人们才能长期结合在一起繁衍和养育后代,保持社会和谐和生产力旺盛。那项研究报告最后还安慰性地说,其实,最有挑战性的可能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那个人,和那个我们认为了如指掌的人一起生活,可能在瞬间变成最冒险的尝试,而这事儿就恰巧发生在布鲁诺教授身上。
妻子对“自我”的追寻,让布鲁诺一时间怀疑他们是不是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太长了,是不是应该像他们的美国朋友那样购买一些教夫妻间如何互相忍让和学习、如何相敬如宾的瑜伽大师的傻瓜读物。妻子甚至连离家出走的原因都不屑于向他解释,布鲁诺觉得她丝毫不顾忌他对她的感情,感到深深受到伤害。甚至觉得找到妻子也不一定想和她一块过了,只是想探个究竟。尽管你尽可以相信百年之后的布鲁诺也会花心不死,但也是在他寻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身上还是有浓浓的人情味儿。他从南美洲一直找到他们初恋时度假的希腊小岛克里特,尽管这是场没有任何确定性的旅程,但他只能冒险,只有让自己在路上,他才能减少坐卧不安的感觉。在心里他一直珍惜他妻子法比阿娜对他的真情,凭着这份纯情他准备和妻子白头到老,因为他觉得这份真挚的感情是他的精神支柱之一,是不可替代的,也是排他的。她在丈夫的丑闻暴露后,采取了冷静、镇定和宽容的态度,给了布鲁诺很大的慰藉,但也最终使她不堪重负并导致了信任的崩溃。
布鲁诺在大学里教的是“乌托邦与地狱史”,非常有隐喻色彩。人类从古至今追求乌托邦的理想,但现实中却不断生出“活着即地狱”、是苦难的感叹,对此,布鲁诺深感哀伤和悲观。如果说作为专业人士,他在美国生活得还算幸福的话,那作为人他的代价就太高了。那种深深的孤独,在热情的南美洲大陆是不可想象的。青年时代的共产主义理想破灭了,激情消失了,他感觉非常寂寞,却无人与说。他自己的生活也是个证明,直到妻子离去,他才发现他的全部幸福似乎建立在妻子的存在上,它的根基如此虚无缥缈,妻子一离开,覆手就成了他的炼狱。他曾经研究《奥德赛》,其实《奥德赛》就是一个反乌托邦式的作品。奥德修斯一心要收复属于他的东西:他的伊萨卡岛、妻儿,全然不理会众神通过热情的女人许诺的天堂。对于一个接近50岁、在很大程度上要为第三世界落后的政治乌托邦思想负责的拉丁美洲裔教授的悲观主义论调的研究,他的美国同事会怎么想,布鲁诺不再关心,唯一能触到他敏感而痛苦的神经的,就是法比阿娜的离去。
 (
罗伯托·安布埃罗
)
(
罗伯托·安布埃罗
)
布鲁诺本身是个虚无者,甚至认为对乌托邦和地狱的探索都是没有意义的,于是对课程也都是敷衍了事的态度。无论对工作还是家庭,他都带着一种表面上看去玩世不恭和逢场作戏的态度,甚至在寻妻途中又和一个法国女孩和一个意大利女孩发生了关系。一旦生理性冲动占了上风,他就毫不犹豫地拜倒在美人脚下。就性格而言,他比那些“有贼心没贼胆”的人要有趣,在他身上,非理性的冲动和冷静的思考是分工明确的,他以为做人只要听自身动物性的召唤即可,和年轻女孩的接触,是他滋养自己的一种方式——出于中年危机,寻找一种打败衰老进攻的方法。但带来的长久后果是既破坏了自己的家庭幸福,也毁坏了别人的幸福。法国姑娘弗朗索瓦兹本来要与未婚夫举行婚礼,布鲁诺和她上了床,而且不仅是一夜情,那可怜的未婚夫给布鲁诺打来威胁电话,要求他退出,扬言要他好看。但另一方面,布鲁诺和弗朗索瓦兹的任性,也是出于他们对乏味式幸福的不屑。布鲁诺认为宗教的天堂和政治上的乌托邦一样,都是一种没完没了的重申,具体到个人,就是重申一种塞满美德、繁荣和幸福的生活,因为永恒,也就没有过去和未来,因而也是一种乏味的生活。
布鲁诺和妻子的矛盾还在于他对妻子始终缺乏足够的了解,不仅对她的成长环境,甚至到后来发现他连妻子的真名都不知道。而男人对女人的故事缺乏聆听或者选择遗忘,布鲁诺认为是为了在生活中不受伤害的一种无意识策略,为了没有感觉地站起来的一种生存方式。在他小时候,大人们就告诉他,回忆和乡愁削弱男人的意志。他很奇怪在宗教著作和《神曲》里,地狱里最坏的惩罚是重申遭受的折磨,而不是遗忘,那才是最残忍的。布鲁诺和妻子的连接点是他们的女儿,由于父母国籍不同,她掌握多种语言,在美国受教育,却与美国主流格格不入,但这也给了她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的方式。还有一个时不时冒出来的董甘探长,坚持认为,乌托邦和地狱史只不过是文学,认为人类的各种生活早已经出现在世界某地的一部长篇小说里,所谓文明进步,不过是换几个小花招而已。他认为没有地狱存在,也就意味着所谓这个说法只是对坏心眼的人的一种挟制而已,而他也认为现实本身就像地狱,这对一个探长来说很容易找到说服点。布鲁诺也觉得,人们会为了满足自己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他们会假装坦诚地亲热,会信誓旦旦地表现出一副忠诚的样子,其实眼里瞄的是背后的利益。街上无忧无虑跑来跑去的人可能就是地狱里遍布的骗子和伪君子,敢情还不如他呢。“不造反的天使不一定忠于上帝,甚至更坏。”这就是布鲁诺思索的结果,只有糟糕的文学和好莱坞电影让我们相信,丑恶的都是丑人,他们是因为生得丑才丑恶的。
全书由布鲁诺的叙述和他妻子对自己出生地的寻访经历交叉构成。不过他妻子的叙述那一部分像个不入流且毫无悬念的豪门小说,显然缺乏一本好小说的活力,中段不够爽利,作者后劲不足,仅仅为了拖延找到妻子的时间而显得拖沓。这本书去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中西葡拉美文学入选作品。作者试图回答,对于男人来说,爱情是什么?因为爱情对于女人来说,就是无条件、无保留的全面献身,是不把爱分开的决心。“激情与逃离”,是智利裔美国作者罗伯托·安布埃罗始终喜欢探讨的主题。他1953年生于智利,1973年考入智利大学教育学院语言文学系,同年由于政治原因流亡古巴,曾就读于哈瓦那大学语言文学系。1980年前往德国工作,2000年定居美国,在爱荷华大学获艺术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现在该大学教授文学与写作课。我国之前曾出版过他的《斯德哥尔摩的情人》。《希腊激情》最早被用做卡赞扎基斯的小说名,他写于1948年的一个小说(也叫《基督再次受难记》),讲一个小村子的村民每隔7年排演关于基督的戏剧,导演戏剧的村长给每个戏剧人物都找到现实的性格对应,比如基督由一位谦逊的牧羊人扮演,而牧师由一位刚愎自用的村领导扮演,暗示他们总把自己的意志当上帝的。小说就转入戏剧情景中,后来演着演着,牧羊人说话办事越来越像耶稣……并从基督的故事和村庄的角度同时探讨个人意志与集体的关系等。有的人认为这是比他的《最后的诱惑》还要好的一本小说。不过除了卡赞扎基斯的出生地也是克里特岛外,两本同名小说看上去并没什么联系。 乌托邦奥德赛布鲁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