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预期的非理性
作者:薛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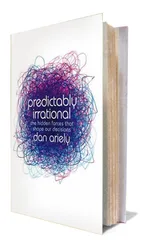
非理性的主宰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道:“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是占主导地位的人性观,大多数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普通人都这么认为。的确,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我们的身体和心灵能做出很神奇的行为。我们看到远处抛来一个球时,能迅速估算出其轨迹和落点,然后移动我们的身体和双手去接住它。我们能够轻松地学会新的语言。我们能够学会下棋。我们能识别几千张面孔而不混淆他们。
传统上,经济学家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行动者,会对经济利益的激励做出一定的反应。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弗洛伊德的洞见可以像亚当·斯密的洞见一样有用。迅速崛起的行为经济学让更多的经济学家涉足无意识领域,探讨人性影响市场的方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丹·艾瑞里(Daniel Ariely)教授在《可预测的非理性》一书中研究了情感、期望、环境和社会规范在经济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艾瑞里感兴趣的不是极端的、会登上报纸头版的非理性行为(比如布兰妮)。他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自相矛盾的行为。比如,为什么即使能得到5美元,也没几个人愿意在太阳下站两个小时,却有很多人愿意为了一个免费的价值4美元的冰淇淋而等待更长的时间?艾瑞里的答案是,因为我们高估了免费的东西的价值。
为什么在购买一支25美元的钢笔时,很多人愿意为节省7美元而走很远的路,但在购买价值450美元的设备时,就不会为了省7美元而多跑路?因为我们对钱的概念是相对的。为什么收费很高的律师拒绝以30美元的价格为穷人提供服务,却愿意免费那样做?因为慈善活动的社会价值高于冷酷的市场指令。
 ( 丹·艾瑞里和《可预测的非理性》
)
( 丹·艾瑞里和《可预测的非理性》
)
传统的经济学假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推断所有可能的选择的优劣,然后按照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行动。要是我们犯了错误,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呢?对此传统经济学也给出了解释:市场的力量会制伏我们,迅速地将我们带入正途。然而,现实中的经济生活跟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相反,充满着错误的计算。《纽约客》的评论说:“真正奇怪的不是为什么我们做了那么多错误的经济选择,而是为什么我们仍一往情深地接受这样的经济学理论。”
作为一门学科,艾瑞里所研究的行为经济学只有大约25年的历史。它的出现主要是上世纪70年代以色列裔美国心理学家阿莫司·特沃斯基与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克赫曼的研究成果引发的。特沃斯基和克赫曼在研究人们如何应对不确定性时发现,人们在行动时会持有一些固定的偏见,人们倾向于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出一些结论,如果他们最近看到过车祸,他们就会过高地估计死于车祸的危险。还有比这更神奇的例子:在一项实验中,特沃斯基和克赫曼要求参加实验者估计非洲国家是联合国成员国的比例。结果发现,他们可以通过在受试者面前转动幸运转盘来影响他们的反应,如果转盘上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数字,受试者也会说出一个很高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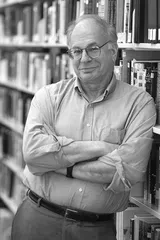 ( 丹尼·克赫曼
)
( 丹尼·克赫曼
)
随后,特沃斯基和克赫曼最初的发现得到了证实,并在多个实验中得到扩展。艾瑞里和他的同事们在一项实验中让MIT管理学院的学生在一张纸上写下他们的社保卡的末尾两位数。然后让学生们在同一张纸上写下他们是否愿意付那么多钱去买一瓶酒、一本书或一盒巧克力。最后,要学生们写下他们愿意为这些东西最多支付多少钱。他们写好后,艾瑞里问他们,他们的社保卡号对他们的出价有没有影响。学生们予以否认,但当艾瑞里列出结果后,他们都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自己。社保卡号从00到19的,出价也最低,平均为67美元。卡号尾数为20到39的,平均愿意出102美元。尾数从80到99的学生平均愿意花198美元。“如果要从这些实验中得出一条教训的话,那就是我们都是一场游戏的玩物,我们根本不清楚它的魔力。”
艾瑞里曾经注意到,《经济学家》杂志提供三种订阅方式:网络版59美元,印刷版125美元,印刷版加网络版也是125美元。看到这种巧妙的订阅广告,很多人都会选择最后一种,而不会选择最便宜的网络版。“如果它只列出前两种选择,我们无从判断是59美元的网络版实惠还是125美元的印刷版实惠,但是列出三种价格后,我们可以知道,印刷加网络版125美元的订阅价要比订阅印刷版本身125美元实惠,因为前一种方式相当于免费赠送了网络版。这说明人在做选择的时候,并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一个内在的价格表告诉我们商品值多少钱。我们会比较一件东西优于另一件东西之处。大多数人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除非在一定的背景下来问他们。”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最清楚每个人的需要和利益所在的是他们自己,所以政府无法代替他们来做选择。按照艾瑞里的理论,人是非理性的,所以政府需要适当地引导他们,甚至替他们做出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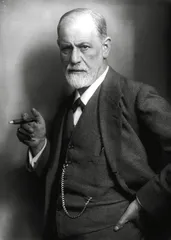 ( 弗洛伊德
)
( 弗洛伊德
)
行为经济学的慰藉
艾瑞里注意到,我们很多人的行为并不是那么理性,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创见,但他更有价值的发现是,我们的非理性行为既不是随机的,也不是毫无章法的,它是系统性的,由于它会反复出现,所以是可以预测的。也就是说,在同等条件下,大多数人都会做出同样的反应、犯同样的错误。“坏消息是,我们匍匐于强大的非理性力量之下,好消息是,我们能够认出它们,采取一定的措施。如果你知道每次你饿着肚子去超市的时候你都会买过多食物,你就可以下决心,以后你饿肚子的时候坚决不进超市。”
他认为制度的安排必须考虑个人行为中的非理性心理因素,人人都知道没有免费的午餐,消费必须付钱,道理人人都明白,但支付时还是感到很痛苦。假设你坐游轮沿长江到三峡游览,现在有两种支付方式,一种是在上船之前付钱,另一种是在旅行结束时下船付钱,你更喜欢哪个呢?从传统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显然后付比先付好。然而考虑支付的痛苦,你会发现后付未必就好,因为设想一下你刚刚经历了快乐旅程,但想到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为此而付钱,你会高兴吗?
艾瑞里说他的发现不仅有趣,而且有益:“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兴高采烈地购买自己用不着的东西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服了1分钱一粒的阿司匹林之后仍感到头疼,但如果吃了5毛钱一粒的阿司匹林之后就不觉得头疼了吗?你知道为什么人们在被要求背诵‘十诫’的时候会比那些没这么做的人更诚实吗?读完本书后,你将知道这些对你的个人生活、商业生活和你的世界观很有意义的问题的答案。比如,在理解了关于阿司匹林那个问题的答案之后,不仅对你选购药品有意义,对全社会面对的健康保险的成本和有效性问题也很有意义。理解了‘十诫’对诚实度的影响也许能够帮助我们防止下一起安龙公司那样的财务造假事件。”
如果制定政策要考虑人的行为的心理因素,那比单纯运用经济杠杆要复杂多了,这将是非常庞杂的任务。行为经济学是对经济学长期以来的基本假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还是说它只是揭示了人类的有趣但相对来说微不足道的弱点?对此经济学家们意见不一。提姆·哈福德认为,艾瑞里设计了很多巧妙的实验来研究人的行为,问题在于我们能从这些实验中得出多少普遍化的结论。我们在做决定时,大体上还是理性行事的。
《纽约客》的记者克尔伯特说:“如果说能从行为经济学中得到什么安慰的话(这种冲动本身也许就是非理性的),那就是,非理性并不总是坏事。毕竟,对于别人,我们最看重的跟经济利益关系不大。谁希望自己的朋友或者爱人非常精于算计?一些说明人类弱点的实验也揭示了他们的好心。艾瑞里研究过人完成某项任务的意愿跟经济报酬高低的关系。如果支付一定的酬劳的话,被试者愿意帮助别人搬走沙发,或者用电脑做某种累活。如果给的报酬比较少,他们就不太愿意干,但不给他们任何报酬要他们付出劳动的话,他们倒愿意一试。这表明人还是愿意保持尊严和乐善好施,哪怕没有经济上的回报。”■ 预期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