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格拉与多元文化主义
作者:娜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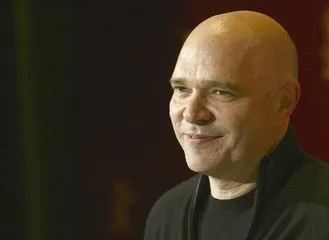 ( 安东尼·明格拉
)
( 安东尼·明格拉
)
出身意大利移民家庭的明格拉身上既有英国文化的清晰文雅,又有意大利人的热情洋溢。他以电影导演闻世,但他的文化兴趣十分广泛,“足球、歌剧、电影、音乐和文学都在其内”,是一位知识型导演。跟他合作过几部电影的制片人斯科特·鲁丁(Scott Rudin)回忆说他的谈话中总会提及他阅读的书籍,他看到的戏剧等等。他的创作生涯是在大学教戏剧期间开始的,以剧作家成名,1990年导演电影《一屋一鬼一情人》(Truly,Madly,Deeply),本为电视制作的电影,但获得好评在影院上演,从此步入影坛。2000年他还跟著名导演西德尼·波拉克联手成立了Mirage独立制片公司,参与制作的都是一些富于思想性和人文性的电影,如《迈克尔·克莱顿》、《安静的美国人》等。波拉克说,明格拉感兴趣的“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魔术,而不是那种造假的魔术……现在人人都在制作快速脱衣快速掏枪的电影,他感兴趣的是诗意,用故事、广阔度和丰富性让观众得到享受”。这句话用在《英国病人》身上再恰当不过。
明格拉属于西方自由派文化人士,多元文化的拥护者,有开放的眼界和慷慨的心灵,对于当代社会有参与的热情,而非躲在象牙塔里搞艺术的自我中心者。他的政治观,也许在他最后公映的影片《破门而入》(2006)中表露得最为清晰。这部电影因过于努力地想为西方当代城市生活的问题寻找一个令人安慰的出路,显得有些过于人工与勉强,不能算他最成功的作品,但却最直接地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正直的人的品格。
故事的主人公威尔是伦敦的一个发展绿色建筑的建筑师,跟瑞典来的金发女友同居10年,她的女儿有成长问题,而这对男女本身的家庭和感情生活也存在危机。威尔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师,将办公室设在伦敦的King's Cross地区,这是穷人和移民出没的地段。结果搬去没多久办公室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盗,《破门而入》的片名就是由此而来。偷盗团伙中的一个男孩——米罗来自波斯尼亚,其母亲阿米拉是个在家开业的裁缝。威尔跟踪米罗来到他家,结果与阿米拉发展出一段情,当米罗被警察抓获,威尔的证词将会决定这个男孩的前途的时候,每个人都面临艰难的选择……
这个故事触及西方当代都市的一些典型问题:中产阶级的家庭危机,贫民区与移民潮带来的社会矛盾,不同文化在密集的城市区域里的撞击。面对这些问题,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反应不同。明格拉代表的是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观点,他们对大英帝国的侵略扩张殖民史带有负疚感,因此对于殖民时代之后,当年大英帝国殖民地国家的移民大量涌入所带来的问题抱有一种历史观,也即片名所说的:破门而入。当年西方殖民者去第三世界难道就不是非法入侵吗?对右派来说,他们拒绝将今天的问题回溯到那一出发点,跟资本主义原罪相联系,也拒绝自由左派的负疚感。总之,《破门而入》是这样一种文化论争背景中的故事,明格拉以一种正面的心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将不速之客进入自己的生活看做生活重整的动力,“破门而入”带来了新能量,最后让自家凝滞的空气有了流动,坏事可以变好事……而建筑师威尔也属于上述“负疚派”,他的善举最后也帮助了那对波斯尼亚母子,双方都不断说“对不起”。但这个善良的结局却让两派都不容易满意:右派对“对不起”觉得好笑,而左派知道,事情也不是连说多少“对不起”就能这么轻易解决的。
虽然被社会观念弄得有些束手束脚,结尾有些人工化的皆大欢喜,但是整部影片还是不乏可看之处,编剧出身的明格拉善于撰写真实的对话,但是最有活力的是影片对伦敦当代生活景观的表现,充满敏锐的观察也充满对这个复杂的多元文化都市的热爱。明格拉也是善于发掘演员潜力的导演,《英国病人》、《冷山》和《天才瑞普利》3部电影将5位明星送上奥斯卡提名台(拉尔夫·菲恩斯、裘德·洛、芮妮兹·薇格、朱丽娅·比诺什和克里斯汀·斯考特·托马斯),但我觉得《破门而入》中比诺什演的波斯尼亚母亲证明她真的是当代最棒的女演员:可以毫不费力地摆脱明星和美貌的定型,表现真实的活生生的女人,同时又充满动人的原生态魅力。对比之下,明格拉在《冷山》中用同样以美貌和演技并重的妮可·基德曼就显得有一种明星的自恋而没那么出色。
 ( 《破门而入》剧照
)
( 《破门而入》剧照
)
《破门而入》太急于表达对当代城市生活问题的思考和出路,所以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明格拉享誉影坛的“二战”史诗片《英国病人》其实也表现了非常开放的观念,拍得非常好看,也很有力量,属于可以重看的电影——第一遍是感受,第二遍是思考,这跟小说的出色也分不开。小说《英国病人》的作者迈克尔·翁达杰也是一位移民家庭背景出身、来自双重文化的作家,他1943年出生在斯里兰卡,兼具荷兰殖民者后裔、僧伽罗族、泰米尔族等血统,11岁去英国,后来定居加拿大。《英国病人》1992年获英国文学布克奖,其人其书都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引人注目的“后殖民时代”的英语文学,包括印度作家、加勒比海地区作家、南非作家等等。其实90年代以来最有意思的英语文学作品往往出自英国之外的英语作家,这些作家都是英国殖民地文化的产物,而他们的作品又反过来影响和丰富了原殖民者的文化。整个世界都处在这种交错中,完全由单一文化和国家来界定文化身份显得很过时,无论是明格拉还是翁达杰都代表着一种世界性跨越国界的文化人物,在两种以上的文化传统里成长,让他们天生就有一种开放的世界观和多元文化的共容性。明格拉本身具有意大利和英国文化的血脉,又在英国和好莱坞之间进出,拍的片子也是在好莱坞商业发行系统中的偏艺术片,但是从艺术片的角度来看他又是完全在商业系统中运作的导演,这些都不是一个定位就能给界定的身份。
让明格拉看中《英国病人》的原因也在于它是一部典型的后现代小说。叙事完全非传统,语言充满诗意,也充满隐喻,其政治观则巧妙地隐含在叙事中。1945年“二战”结束时的意大利托斯卡尼郊外的别墅里,4个不同程度被战争损害的人偶然凑到了一起:一位加拿大女护士叫汉娜,看护着一个全身烧焦的“英国病人”;一位曾为英国情报局工作的前小偷不约而来,他以前认识汉娜的父亲,现在想从汉娜那里拿到一些麻醉剂,因为他已吸毒成瘾;服务于盟军的印度工兵吉普整天忙于销毁德军埋下的各种地雷和炸弹,他成为加拿大女护士汉娜的情人。“二战”结束时也是大英帝国解体之时,过去与未来都折射在此时此刻。神秘的“英国病人”烧焦的身体有一种象征性,象征着废墟上的欧洲文明,而除弹的却是来自英国殖民地印度的士兵,看护他的是加拿大护士……渐渐的,“英国病人”的过去慢慢浮现,实际上“英国病人”原来根本不是英国人,而是匈牙利贵族,在北非沙漠以地图测量家的身份出现,跟英国贵族女人凯瑟琳发生了一段婚外情。为了回到凯瑟琳的身边,他为德国情报机关工作,最后跟自己心爱的女人的身体一起葬身火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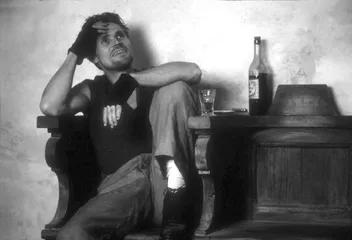 ( 《破门而入》剧照
)
( 《破门而入》剧照
)
“二战”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每个人的国籍与种族身份都影响着他或她的命运,但是在北非沙漠里,“英国病人”和凯瑟琳的爱情抵抗着这种人为的界定。“英国病人”在沙漠中绘图,他完全抛弃了自己的国籍身份,也不愿受家庭束缚,他的职业也寓意着:以国家民族来界定人性,有如在沙漠上画线,沙漠是无边界的,流动的,就如同人性,如同爱,也应该是不由国籍、种族、制度等等人为的界限来界定的。但是,凯瑟琳死了,“英国病人”烧焦了,因为“二战”不容许个人的存在。而战后,加拿大女护士与印度士兵的爱情,也在广岛炸弹的惊雷中,终究被打下了国家、种族、文化的烙印。
但是无论如何,作者将爱视为唯一能超越国界、超越时空、超越种族、超越阶级的力量,地图的概念寓意着人类非要在地理风景上画线,有如国家民族在人性上画线,但是最终回到人的灵魂深处,这些线其实都是外在强加的。
这部非线性叙事的小说人人都说太难搬上银幕,但是明格拉呕心沥血做到了。他花了一年半时间独自一人改编剧本,花了很多精力找钱,而拍摄时间两年,最终大获成功。这部影片有太多令人感兴趣的元素:北非沙漠风景代表的原始力量,意大利别墅代表的欧洲文明的废墟与再生。外在的地理风景与人的情感故事有力地结合在一起,男人女人的激情,鲜活的身体与濒临死亡的身体,阅读与记忆,在史诗般的画面上呈现细微的个人情感,现在、过去、未来……沙漠对于欧洲人一直有种莫名的吸引力——那种异教文化和不同地理环境给予人的既恐惧又吸引的感觉,《阿拉伯的劳伦斯》就是拍出了一个英国人在沙漠的这种体验。而《英国病人》把沙漠风景与故事跟欧洲文明风景交叉在一起表现,将视角拉得更开,地理风景与灵魂风景互为参照,是一部“个人化的浪漫史诗”。 格拉文化多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