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艺博会:藏家与艺术的聚会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中国还没有国际化的当代艺术市场
中国还没有国际化的当代艺术市场
大约三四年前,皮埃尔·胡伯找到中国观念艺术家周铁海,想让他帮着在中国做一个国际性的艺术博览会,他们是交往了10年的朋友。那时皮埃尔也只是有一个模糊的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之后,艺术市场肯定会跟进。
20世纪早期,艺术市场的边界明显分布在巴黎周边。20世纪80年代,艺术市场中心转移到纽约,并逐渐扩展和覆盖了整个美国与欧洲大陆。而今天,他感觉正在见证又一次地理上的变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那批西方人并不能代表西方主流艺术界,只是极少数人的兴趣。用已故巴塞尔艺博会亚洲顾问乔纳森·纳帕克的话来表述,西方观众对中国艺术家的兴趣现在越来越浓,不过并不如中国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急遽增长。西方艺术界对它普遍的认知和好奇从5年前开始。
 周铁海现在的身份是上海艺博会国际当代艺术展亚洲顾问。这个展会在9月6日到9日期间曾是全球当代艺术界的热点,至今余热未消。“皮埃尔最初想在印度、中国、巴西、俄罗斯各做一个艺博会,实现遍布各大洲艺术网络的设想。最后他选了中国作为开始,理由很简单:这里经济发展和市场活力所受到的世界关注度高于其他三个国家,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为也更对欧美主流艺术界具备冲击力。”
周铁海现在的身份是上海艺博会国际当代艺术展亚洲顾问。这个展会在9月6日到9日期间曾是全球当代艺术界的热点,至今余热未消。“皮埃尔最初想在印度、中国、巴西、俄罗斯各做一个艺博会,实现遍布各大洲艺术网络的设想。最后他选了中国作为开始,理由很简单:这里经济发展和市场活力所受到的世界关注度高于其他三个国家,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为也更对欧美主流艺术界具备冲击力。”

 对亚洲和中国,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前任总监塞缪尔·凯勒(Samuel Keller)在2006年也已经有他自己的判断,凯勒说他需要5年来观察这块区域的艺术市场趋势。作为全球最具品牌效应的艺博会,巴塞尔一向矜持又谨慎,2002年他们选择迈阿密作为伙伴合作举办海滩艺博会,为这个项目考察了6年。而今年66岁的皮埃尔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用来等待,他观望两年后就决定落地,抢先老东家巴塞尔一步打亚洲牌。
对亚洲和中国,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前任总监塞缪尔·凯勒(Samuel Keller)在2006年也已经有他自己的判断,凯勒说他需要5年来观察这块区域的艺术市场趋势。作为全球最具品牌效应的艺博会,巴塞尔一向矜持又谨慎,2002年他们选择迈阿密作为伙伴合作举办海滩艺博会,为这个项目考察了6年。而今年66岁的皮埃尔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用来等待,他观望两年后就决定落地,抢先老东家巴塞尔一步打亚洲牌。
在中国,皮埃尔还要选择一次:北京,还是上海?皮埃尔到北京看了几次场馆,包括现在“艺术北京”租用的农展馆,他觉得不错。但皮埃尔最终还是舍弃了北京,展会高层一致投票落地上海。他跟周铁海大致说过两个理由:世界上顶级的几个艺博会都没有放在艺术中心的先例,瑞士巴塞尔、美国迈阿密都是商业中心,而不是画廊、艺术家工作室集中的城市。经验在经过无数次成功验证后,就有获得尊重的理由。周铁海的理解是:北京本来就有几个面积宽阔、密度集中的画廊艺术区,日常交易活跃,在这样的艺术中心办博览会,做得再好也不容易凸现,所谓缺少对比度。另一位参与上海展会的中方成员也谈到洛伦佐没有公开的权衡:很多人都认为北京对于上海的优势,在于它有数量庞大的自由艺术家,有他们的工作室所组成的艺术区,当代艺术的创作和学术氛围都优于上海——但在洛伦佐看来,这恰是他舍弃的原因之一。他的博览会将带来世界顶尖的画廊参展,这些参展商又将带来最有实力的藏家,如果展会在北京,这些藏家就可能被中间人带往艺术家工作室,在利益权衡下,他们很可能会撇开参展商,和某些艺术家直接交易。洛伦佐遵守游戏规则,既然是博览会,就要保证参展商的权利。
上海的优势在哪里?欧美人普遍对这个城市有认同,生活环境方便。这位中方人员透露了一个小细节,在陪同洛伦佐考察场馆时,他说理想的展会至少具备三个条件:展馆区域环境单纯,附近有高档酒店,从酒店到展馆在舒适方便的步行距离之内。很显然,上海展览馆比北京农展馆更接近他的理想状态:场馆对面有上海最好的五星级酒店波特曼,符合全球重要藏家和画廊主的入住要求。从波特曼到展馆,步行穿过繁华的南京西路就可以了。世界上重要的收藏家也就是100多位,这次皮埃尔几乎把他们都带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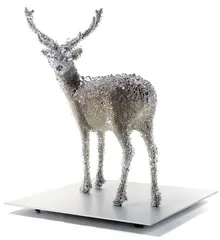 现在说一个博览会好也没有新鲜词,通常就是:国际化。怎么算国际化?身处陌生的中国,这些人搭建了一个彼此熟悉的“购物环境”,这可能算是国际化最具象的呈现。周铁海以他南方人的细致,说了几个看似不相关却让他印象深刻的细节。比如展会日期,并非简单考虑季节气候和组织者的个人喜好就可敲定,为挑选一个合适档期,皮埃尔和洛伦佐用了排除法:首先一年中最适合展会的季节是4月到11月,但4月底5月初有芝加哥艺博会,还有苏富比、克里斯蒂两大拍卖行在纽约、伦敦的春拍。6月有巴塞尔,7、8月是欧美传统的夏日长假,也不是上选。10月巴黎有巴黎艺博会(FIAC),11月苏富比和克里斯蒂举行秋季拍卖,12月是迈阿密海滩艺博会——这样筛选后,9月成了最合适的档期。同样在9月,上下旬也有很大差别:考虑到持续10天的犹太新年一般都在9月中下旬,全球最重要的艺术策展人、艺评家和收藏家里面犹太人又占了多数,他们最后决定将上海的展会日期确定在9月上旬,和犹太新年错开,“在我看来,这就是国际化最实在的表现形式”。周铁海说。如果前两届上海艺博会国际当代艺术展成功,9月这个日期就会像巴塞尔的6月一样,变成全球当代艺术界为上海和中国、亚洲专门留出的4天约会。
现在说一个博览会好也没有新鲜词,通常就是:国际化。怎么算国际化?身处陌生的中国,这些人搭建了一个彼此熟悉的“购物环境”,这可能算是国际化最具象的呈现。周铁海以他南方人的细致,说了几个看似不相关却让他印象深刻的细节。比如展会日期,并非简单考虑季节气候和组织者的个人喜好就可敲定,为挑选一个合适档期,皮埃尔和洛伦佐用了排除法:首先一年中最适合展会的季节是4月到11月,但4月底5月初有芝加哥艺博会,还有苏富比、克里斯蒂两大拍卖行在纽约、伦敦的春拍。6月有巴塞尔,7、8月是欧美传统的夏日长假,也不是上选。10月巴黎有巴黎艺博会(FIAC),11月苏富比和克里斯蒂举行秋季拍卖,12月是迈阿密海滩艺博会——这样筛选后,9月成了最合适的档期。同样在9月,上下旬也有很大差别:考虑到持续10天的犹太新年一般都在9月中下旬,全球最重要的艺术策展人、艺评家和收藏家里面犹太人又占了多数,他们最后决定将上海的展会日期确定在9月上旬,和犹太新年错开,“在我看来,这就是国际化最实在的表现形式”。周铁海说。如果前两届上海艺博会国际当代艺术展成功,9月这个日期就会像巴塞尔的6月一样,变成全球当代艺术界为上海和中国、亚洲专门留出的4天约会。
事实上是全世界都要来利用中国这个平台
因为上海艺术博览会当代艺术展,董梦阳担任首席执行官的2007“艺术北京”得到了比从前多上几倍的关注度,因为他们的展期就在9月的19〜23日。上海头3天是VIP专场,很多圈子里人在场馆里转一圈,第一反应就是“董梦阳他们怎么办”。皮埃尔他们把水平线已经抬得很高了:画廊质量、展览结构、学术表现以及到场收藏家的分量和数量都完全可以和世界上最好的艺术博览会相比。还有工作人员透露,巴塞尔艺博会的最新团队到展会现场后,因为眼前不断晃过熟悉的画廊主人和大藏家而变得面色凝重,估计是痛感巴塞尔的资源被两位前任挖到了上海。董梦阳后来也告诉记者,他那几天确实收到大量手机短信,他不否认自己有压力。皮埃尔请他去上海参加开幕酒会,“真是不太想去,满场都是熟面孔。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好比女朋友跟人走了,不看见也罢,亲眼看见总归心里不太舒服”。从资金投入量这样的硬件,到皮埃尔和洛伦佐两位国际大腕的团队组合,董梦阳自认无法相比,“我的预算最高1000万元人民币,他们至少是我们的3倍”。周铁海证实了上海展会资金支持雄厚,而且据他说,投资方博罗尼亚展会集团在5年内没有盈利要求。如果不是冲着抢滩中国展会市场而来,谁愿意如此流水一般花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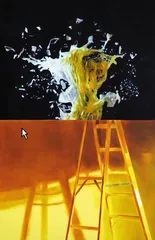 任何国外展会要想在中国落地,必须有中国合作方。董梦阳自称,对中国本土艺术市场的了解是他目前最能依靠的资本,但他暂时还不想和任何一家欧美展会集团合作,“事实上是全世界都要来利用中国这个平台,和他们自己叫板”。2004年,董梦阳和同事在北京科技会展中心做成了第一届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CIGE),那次经历让他强烈体验到:好的,未必是适合的。他们请到70家左右参展商,多半是商业味道很浓的画店,董梦阳形容它们是“798的琉璃厂”。也有十来家国外画廊是参加过巴塞尔的,日本有名的小山登尾夫画廊也来了,小山带了他们最好的当代艺术家村上隆的作品,结果没卖出去,中国买家对他作品的价位根本没有心理接受度。2005年在众所周知的一场内耗后,董梦阳自己带团队转而经营“艺术北京”品牌。那年他千辛万苦将纽约一流的高古轩画廊请到了北京,带来满墙安迪·沃霍尔,每幅大约10万〜11万美元,“我找了很多藏家去谈,没人成交。对面画廊挂的王广义作品,卖得却特别好。我后来反省,觉得请高古轩这样的画廊来还早了一点,做了不合时宜的事。中国藏家还在投资艺术品,没到消费艺术品的阶段,他们不会轻易接受自己不知道的艺术家,价格高就更不行了”。
任何国外展会要想在中国落地,必须有中国合作方。董梦阳自称,对中国本土艺术市场的了解是他目前最能依靠的资本,但他暂时还不想和任何一家欧美展会集团合作,“事实上是全世界都要来利用中国这个平台,和他们自己叫板”。2004年,董梦阳和同事在北京科技会展中心做成了第一届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CIGE),那次经历让他强烈体验到:好的,未必是适合的。他们请到70家左右参展商,多半是商业味道很浓的画店,董梦阳形容它们是“798的琉璃厂”。也有十来家国外画廊是参加过巴塞尔的,日本有名的小山登尾夫画廊也来了,小山带了他们最好的当代艺术家村上隆的作品,结果没卖出去,中国买家对他作品的价位根本没有心理接受度。2005年在众所周知的一场内耗后,董梦阳自己带团队转而经营“艺术北京”品牌。那年他千辛万苦将纽约一流的高古轩画廊请到了北京,带来满墙安迪·沃霍尔,每幅大约10万〜11万美元,“我找了很多藏家去谈,没人成交。对面画廊挂的王广义作品,卖得却特别好。我后来反省,觉得请高古轩这样的画廊来还早了一点,做了不合时宜的事。中国藏家还在投资艺术品,没到消费艺术品的阶段,他们不会轻易接受自己不知道的艺术家,价格高就更不行了”。
皮埃尔他们也遇到这种疑问。展会结束后,国内外媒体普遍叫好,但也有人对它作为交易平台的一面表示担心。皮埃尔和洛伦佐的组合有无可置疑的号召力,带来了全球一流的收藏家、一流的画廊,带来了目前在欧美艺术市场最受关注的西方艺术家作品,如安迪·沃霍尔、弗洛伊德、劳申伯格,但有人怀疑中国的本土收藏群体是否有愿望和能力接受它们。对此皮埃尔的回答是需要过程。他带来的很多藏家和画廊同样不了解中国当代艺术,比如巴黎最好的画廊之一“朗贝尔”(Yvon Lamberr)就告诉记者,他们从未接触过中国当代艺术。纽约的朗画廊(Max Lang)虽然也签有张洹这样的中国艺术家,但他们这次带到上海的仍以美国战后和当代艺术为主,像售价250万美元的涂鸦艺术家巴斯奎特(Jean Michel Basquiat)作品《无题》和900万美元的《Catharsis,1984》,480万美元的沃霍尔的黑白《玛丽莲·梦露》。纽约另一家顶级画廊詹姆士·科恩(James Cohan)在展会第二天以26万美元卖掉了比尔·维欧拉一件录像作品,45万美元卖掉一件雕塑,买主都是台湾地区一位女收藏家。当法国女记者报道没有中国内地藏家在展会期间买了作品的时候,皮埃尔向《每日电讯报》记者的爆料说,“一位很有实力的中国内地收藏家出人意料地收购了15件作品⋯⋯”
丹麦法思高(Faurschou)是北欧最有影响力的画廊之一,1680万美元的弗洛伊德作品便是他们带来的,在上海展会期间有多家博物馆、基金会表示有兴趣购买。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在该画廊收藏中约占20%比例,现场一张岳敏君的《无题》标价50万美元。现场记者还看到了日本艺术家小山登尾夫,法思高有意签下他的作品。画廊主人让·法思高(Jean Faurschou)先生表示,他参加过世界各地的博览会,这次是高品质的,如果继续努力,他认为将是亚洲最好的艺术博览会。前面同样的问题提交给他:没有成交的话,是否感到失望?他回答说,法思高画廊经营了21年,对短期利益并无兴趣,“任何事情,耐心都是重要的,要有长远打算”。
对此周铁海也持和董梦阳不同的观点。周铁海选择性看到的,是超前消费环境对消费观念所具备的培育和催化功能,他举了路易威登的例子,“10年前它在上海开店还门可罗雀,绝大多数中国人连路易威登是什么东西都没听说过,谁能相信今天它会拥有如此规模的中国奢侈品消费群体?这个群体的数量和能量已经让所有世界奢侈品牌都不敢轻视”。
3个国际艺术博览会多不多?
一个经济实力不错的画廊每年能参加几个博览会?有“法国当代艺术代言人”之称的巴黎Daniel Templon画廊经营了40年,每年固定参加5个艺博会:巴黎两次,布鲁塞尔、巴塞尔、芝加哥各一次。画廊主人解释说,参加什么地域的博览会主要从自己签约的艺术家和作品来考虑,像他代理了不少美洲艺术家作品,所以在欧洲之外会选择去芝加哥。上海是他最新的选择,主要原因在于信任两个策展人,想跟着他们看看中国市场,其实到目前为止他还从未经营过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北京明年我也会去一次,然后在上海和北京之间选一个。”他的想法在欧美参展商里有代表性:多数在北京、上海选一处固定下来,少数可能因为来一趟不容易而两边兼顾,但要是让画廊在一年内参加3个中国的艺博会基本没可能。所以董梦阳的判断是,“我认为地区性淘汰肯定是要发生的,最后剩下北京一家,上海一家。两年见分晓”。周铁海更乐观一点,“中国现在一南一北3个艺术博览会,我觉得并不算多。巴塞尔艺博会期间,这个小城周围同时在开5个博览会;迈阿密海滩艺博会档期,城里大小有12个博览会,都和艺术品交易有关。中国3个展会不一定两年下来就谁生谁灭,大家可以各自调整方向,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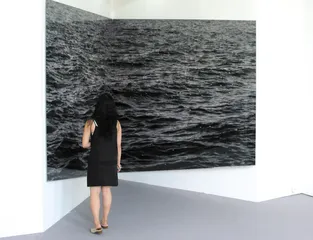
 “艺术北京”今年已经审时度势地把定位调整到主打亚洲牌,不再费心劳力去追求参展国家这样的数字统计。上海今年画廊的比例分配大约是欧美百分之五六十,亚洲百分之五六十,中国画廊在亚洲区占15%左右。“艺术北京”中国画廊的展位达到了40%,然后是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他们想利用中国平台整合亚洲的当代艺术资源,一起把亚洲这张牌握紧在手里,吸引全球藏家。上海的展位费最低一档收取30万元左右,和巴塞尔等地的价位基本一样,而“艺术北京”只有六七万元,他们觉得这对于本土画廊是能承受的价格。前巴塞尔亚洲顾问乔纳森分析过欧美地区艺博会上亚洲画廊极少的原因,资格审查严格之外,高昂的费用也是障碍,除了少数有固定客户群的画廊,其余亚洲画廊都很难承担得起那笔参展费。
“艺术北京”今年已经审时度势地把定位调整到主打亚洲牌,不再费心劳力去追求参展国家这样的数字统计。上海今年画廊的比例分配大约是欧美百分之五六十,亚洲百分之五六十,中国画廊在亚洲区占15%左右。“艺术北京”中国画廊的展位达到了40%,然后是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他们想利用中国平台整合亚洲的当代艺术资源,一起把亚洲这张牌握紧在手里,吸引全球藏家。上海的展位费最低一档收取30万元左右,和巴塞尔等地的价位基本一样,而“艺术北京”只有六七万元,他们觉得这对于本土画廊是能承受的价格。前巴塞尔亚洲顾问乔纳森分析过欧美地区艺博会上亚洲画廊极少的原因,资格审查严格之外,高昂的费用也是障碍,除了少数有固定客户群的画廊,其余亚洲画廊都很难承担得起那笔参展费。
 “中国当代艺术应该不再停留在邀请西方人来、让人知道你的层面,而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标准和模式来服务经营。”巴塞尔艺博会新任命的亚洲顾问田霏宇(Philip Tenari)说的这句话现在看来挺有道理。上海艺博会国际当代艺术展选择了高标准国际化,“艺术北京”选择了依托本土来改装巴塞尔模式。国外空降团队在上海的第一次亮相接近完美,本土的艺博会霍然间被拉开了距离。但艺博会是长跑运动,谁的模式更适合中国现在下结论毕竟早了些。淘汰,还是共生?5年为期。■
“中国当代艺术应该不再停留在邀请西方人来、让人知道你的层面,而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标准和模式来服务经营。”巴塞尔艺博会新任命的亚洲顾问田霏宇(Philip Tenari)说的这句话现在看来挺有道理。上海艺博会国际当代艺术展选择了高标准国际化,“艺术北京”选择了依托本土来改装巴塞尔模式。国外空降团队在上海的第一次亮相接近完美,本土的艺博会霍然间被拉开了距离。但艺博会是长跑运动,谁的模式更适合中国现在下结论毕竟早了些。淘汰,还是共生?5年为期。■
专访皮埃尔·胡伯——
我提供的是一个当代艺术的“结构”
作为艺术总监,皮埃尔为上海挑选参展画廊确立了完全不同于其他艺博会的标准:先挑作品,再选画廊。作品入选后,按照艺术家的意愿邀请他签约的画廊参展。皮埃尔对这个新标准非常自信,他相信有眼光签下好艺术家的画廊不可能品质低下,而通过画廊的中介作用最终又将把艺术家和作品置于整个事件的中心——这正是他为上海艺博会当代艺术展设置的“哲学”和“结构”。在访谈中,皮埃尔反复提到这两个词:哲学,结构。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呈现给我们的这个展览,觉得对事先的设想实现了多少?50%、70%,或者100%?
胡伯:我对“杰出艺术家”和“惊喜的发现”两个部分非常满意,达到了我的期许。从下周开始我将为明年做准备了,体现出来的哲学观点将是相同的,结构也不做改变。但我对画廊部分的满意度只有50%。原因很多,比如选择上的缺陷。第一年很难,画廊对来中国参展有担心,担心经济上不成功,东西卖不出去,有些好的画廊因此临时决定退出,我们在选择上便有所妥协。明年不会妥协了,希望在这部分的满意度明年能达到65%或者70%。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艺术总监,是否关心最后的成交总额?
胡伯:我个人不关心具体数字。但商业上的成功对参展画廊非常重要,随着每一次举办,它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的目标是制定一个中长期计划,使大众能更好理解当代艺术的含义。随着大众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深,会有更多人购买。我希望今年其中一部分参展画廊在商业上成功,等到明年再来,他们不单将在展会期间获益,有的是长期获益。我们会有一本日程,不仅是在这5天之内交易,而是此后一周、一个月、一年甚至几年间的长期关系。我提供给他们的是一个当代艺术的“结构”,这个作用超过了广告。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中国的收藏家群体有什么印象?他们选择当代艺术作品的纯中国趣味会不会影响到你对展会高度国际化的预期?
胡伯:在过去三周,我去南京、北京、香港、澳门转了一圈,和十几位中国收藏家和艺术家见面,并把他们请到了展会。我可以透露的是,他们都从展会买了作品,特别是一些偶发艺术作品。偶发艺术在内地展出机会很少,但这些中国藏家接受起来好像并不困难。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些藏家自己告诉我的:他们以为只能在拍卖会上买到的作品,这里原来也能买到,而且价格更合理。他们能接受新观念,我相信假如今年有15个中国藏家买了作品,明年就会是50个,后年将是100个。同时,我也从欧洲带来上百位收藏家,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接触最多不过5年,我在中国举办展会,对他们来说同样也在经历一个熟悉和了解的过程,这和中国藏家是一样的。
 我现在想在中国做的,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当代艺术市场体系。12年前来中国,在北京只看到一个画廊,乌里希克买作品都是直接找艺术家本人,现在我能看到400家。但和中国的收藏家聊天,他们都告诉我,这件是在拍卖行买的,那件也是在拍卖行买的——要改变现状,必须为他们打造平台。有些艺术家的作品在画廊价格合理,一进入拍卖行,就有泡沫进去了。收藏家从画廊买作品,拍卖行再对他所付的价格做个检测,正常的市场应该是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拍卖行必须尊重这个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与连续环节,不能直接去艺术家的工作室干扰他们,破坏本该由画廊提供的筛选和培育过程。画廊的角色正是新兴年轻艺术天才的支持者和赞助人,其实也正是为将来可能的回报寻找机会。■
我现在想在中国做的,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当代艺术市场体系。12年前来中国,在北京只看到一个画廊,乌里希克买作品都是直接找艺术家本人,现在我能看到400家。但和中国的收藏家聊天,他们都告诉我,这件是在拍卖行买的,那件也是在拍卖行买的——要改变现状,必须为他们打造平台。有些艺术家的作品在画廊价格合理,一进入拍卖行,就有泡沫进去了。收藏家从画廊买作品,拍卖行再对他所付的价格做个检测,正常的市场应该是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拍卖行必须尊重这个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与连续环节,不能直接去艺术家的工作室干扰他们,破坏本该由画廊提供的筛选和培育过程。画廊的角色正是新兴年轻艺术天才的支持者和赞助人,其实也正是为将来可能的回报寻找机会。■
放在任何一个艺术博览会,这都算得上豪华阵容:
洛伦佐·鲁道夫,1991〜2000年的巴塞尔艺博会总监,成功地把巴塞尔重新建构成一个世界顶级的艺术博览会,随后创建了迈阿密海滩艺术博览会。在2000〜2003年担任法兰克福书展总监期间,他让法兰克福成为全球出版业和文学书籍业的顶级展览。
 皮埃尔·胡伯,全球最重要的当代艺术收藏家和画廊主,是最早推动中国和印度艺术家进入国际艺术市场的艺术经纪人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他是著名的巴塞尔艺博会策略团三大军师之一。
皮埃尔·胡伯,全球最重要的当代艺术收藏家和画廊主,是最早推动中国和印度艺术家进入国际艺术市场的艺术经纪人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他是著名的巴塞尔艺博会策略团三大军师之一。
意大利博洛尼亚会展集团,中国承接外展的重要合作伙伴。对于前两个合伙人,它存在于这个铁三角的重要意义在于资金。 国际艺术博览会中国艺博会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