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莫里森的爵士乐
作者:苌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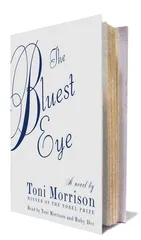
( 《最蓝的眼睛》 )
在1993年,成为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之前的一年,托妮·莫里森发表了小说《爵士乐》。小说讲一个情杀的故事,起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这部小说是按照爵士乐的演奏方式写就的。
传统的爵士乐是这样,先一起进入主题,到了中段,各乐器各来一段独奏,他们的独奏可能围绕主题,更多是即兴发挥,每个人都是当时绝对的主角,创造的效果和乐手的水平有关,性格有关,还和当天的心情有关。同一支曲子不同时间听,感受各有不同。体现在小说中,就是莫里森采用了多角色多角度的叙述方式,事件主人公轮番上阵各说各话,读者得以了解事件的全貌。主人公的叙述可能回溯到自己的祖母时代,涉及当时的黑人社会问题,一个简单的故事,被讲得既有纵深,又有宽广,而结构还不失清晰。
1906年,乔和妻子维奥莱特从南方乡下来到纽约谋生。20多年后,俩人的爱情和梦想都已在大都会迷失。乔爱上了一个18岁的姑娘——多卡斯,同样自小失怙的两个人在彼此身上找到慰藉。然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法承受之爱,乔开枪打死了女孩。女孩在即将失去生命时,拖延时间阻止人们找到凶手。而维奥莱特则跑到葬礼上滋事。到最后,他们的夫妻却又琴瑟合鸣,像一支真的爵士乐曲那样回到共同的主题。为什么会是这样?托妮·莫里森站在各人的角度上讲述他们的心路历程,营造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想象的世界。
“多角度叙事法”并不鲜见,莫里森师承福克纳,但以爵士乐的节奏即兴发挥,则是她在文学上的一次探索。她在序言里说:“我对爵士乐所预见和引导的现代性,以及它那不可理喻的乐观,感到震惊。无论真实情况如何,无论个人命运和种族前景如何,爵士乐坚持强调过去会回来折磨我们,却不会将我们套牢,它要求一个未来——并且拒绝将过去看做是‘别无选择的旧唱片’。”
主人公的回忆经常把读者带到过去。维奥莱特的祖母在白人家做佣人时,照料过一个从小被娇生惯养的黑白混血儿。因为出生时皮肤是金色的,所以取名叫“戈尔登”。戈尔登在长大过程中一直当自己是个白人,后来得知真相后,出发去寻找他的爸爸,当那个“世界上最黑的黑人”出现时,问这个金色皮肤的男孩“我们认识吗?”他说:“不,爸爸,我们不认识。”莫里森小说的气质有点像这个男孩,尽管现在美国黑人的境遇比上世纪初好太多,但她从来不回避隐藏在历史中的大堆问题,美国的历史也是黑人的血泪史,莫里森的笔调始终是冷峻的。“一共两种白人。”书中的主人公说,“可怜你的和不可怜你的,两种都差不多。都对你没有尊重。”
 ( 2006年11月,托妮·莫里森在巴黎卢浮宫 )
( 2006年11月,托妮·莫里森在巴黎卢浮宫 )
不仅是文学上的成就,托妮·莫里森小说最大的价值是对西方白人价值观驱动的这个世界的警醒和对黑人文化的保持和强调,她的小说中的美学和人文价值观并不局限于种族意识和政治领域。1931年,托妮·莫里森出生在俄亥俄州一个工人家庭,大学上的是华盛顿专门接受黑人学生的霍华德大学,后来又在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福克纳小说的硕士。一方面她继承了美国经典文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她始终站在黑人的立场上写作。她的小说题材都是围绕表现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
托妮·莫里森当年是霍华德大学的校花,当看到其他精英同学那种一心要做“高级黑人”的架势,她很不以为然。所谓“高级黑人”已经是在拿白人的价值取向来要求自己。她曾经说:“黑人来到美国遭受过两次奴役,被贩卖做奴隶的肉体奴役,早已经成为过去,但精神奴役则一直在发生,就是黑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全盘接受白人的价值观,以追求改善物质生活为己任,逐渐抛弃了本民族的一些优良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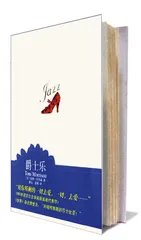 ( 《爵士乐》 )
( 《爵士乐》 )
莫里森的成名作是发表于1969年的《最蓝的眼睛》,讲一个黑人小女孩祈祷能有一双像白人那样的蓝眼睛,但她拥有一双蓝眼睛后,仍然无法摆脱残酷的命运。小说发表的年代正是民运风起云涌之时。有黑人提出“黑人是美的”的口号,但托妮却直指这种提法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和黑人的境遇。“把一个白人概念翻转过来仍然是白人概念,身体美的概念作为一种美德是西方世界最不足道、最有毒害、最具破坏性的观点之一,把问题归结于我们是否美的症结来自于衡量价值的方式,这种价值是细枝末节,并且完全是白人的那一套,致力于这个问题上,是无可救药的精神奴隶。”在《爵士乐》中我们看到,对多卡斯迷人之处的描写并不是强调外貌,而是更多着墨于她似水的柔情和性格。
《爵士乐》是托妮·莫里森1987年开始创作的讲述黑人生活三部曲中的一部,第一部《宠儿》讲更早一些年里的事,女黑奴塞丝从南方农场主的庄园逃出来,为了不让孩子重复自己做奴隶的悲惨命运,就杀死了刚刚会爬的女儿“宠儿”,18年后,宠儿重返人间,不但加倍索取母爱,而且不择手段地扰乱母亲刚刚回暖的生活。“塞丝悬在生活的龌龊和死者的刻毒之间,对生或死都提不起兴致。”托妮写道。这是一部充满苦涩诗意的小说,她说她想探讨的是“自由”对女人意味着什么。妇女地位在近几十年的好转,让她特别想关注黑人妇女曾经经历过的不同寻常的历史。在那段历史中,婚姻是被阻挠的,不可能的或非法的,而生育是必须的,“但是‘拥有’孩子,对他们负责,就像自由一样不可思议。在奴隶制度的特殊逻辑下,想做家长都是犯罪。”第三部《天堂》发表于1997年,我国尚未引进出版,作者写了一个与周边的白人社会不相往来、竭力保持纯净黑人血统的“孤岛”,到了最后无法继续生存的故事。
“一般对巴别塔故事的理解是它的垮掉是不幸的。都认为那塔的垮掉是语言混杂、言语不通造成的。如果有了统一的语言,便能使建造通天塔的工作顺利进行,天堂便可达到了。但那是谁的天堂呢?”莫里森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致奖辞中提道。她说只要大家都拿出点时间来理解其他的语言和文化,就能在地上建立一个活人的天堂,而不是死者的天堂。多年来她透过小说告诉人们,在美国的有色人种应在接受主流文化的同时保持自身的优秀传统,与其他民族一起共建多元文化,才是生存的王道。■ 文学小说托妮·莫里森托妮莫里森爵士乐黑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