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商业化30年
作者:袁越
( 赫伯特·波伊尔 )
转基因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把物种A的某个基因转移到物种B的细胞内。经过转基因后,物种B仍然是物种B,只是多了那么一点额外成分罢了,和“人造新物种”这个听起来有点吓人的概念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转基因并不是把外来基因胡乱塞进一个新细胞那么简单,因为基因本身只是一张草图,在没有建成大楼(蛋白质)之前,这张图几乎毫无价值。要想让这张草图发挥作用,必须把它放在总建筑师的文件夹(染色体)里,那里已经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建筑草图,偷偷塞进一张别的图纸,比较容易蒙混过关。否则,这张图就很容易被扔掉(降解)或者被遗忘,转基因就没有意义了。
说白了,从事转基因工作的科学家就像间谍,他们的任务就是骗过总建筑师,在特定的地方塞进一张“假图纸”,代替原来的真图纸,其结果就是在大楼的屋顶上换一块自己想要的瓦。
转基因的故事必须要从1972年说起。那年11月,在美国夏威夷召开了一次生物学会议。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斯坦利·柯恩(Stanley Cohen)听了赫伯特·波伊尔(Herbert Boyer)所做的报告,大受启发。这个柯恩的主攻方向是大肠杆菌细胞里的一种环形DNA链,叫做“质粒”(Plasmid)。通俗讲,质粒就好比是大楼旁边的自行车棚的设计草图,因为和主楼是分开的,所以单独用一套图纸。正因为如此,质粒这个小密码箱很容易从细胞中被偷(提取)出来,任凭科学家随意摆布。可是,柯恩一直找不到打开这个小密码箱的钥匙。
这个钥匙被波伊尔找到了。这位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报告说,他发现了一种酶,可以识别一段特定的DNA顺序,然后在中间切一刀,把DNA链断开。柯恩听了波伊尔的报告,立刻意识到他可以利用这种酶的特性,在质粒的特定部位切下一小段DNA,再换上自己想要的新DNA(假图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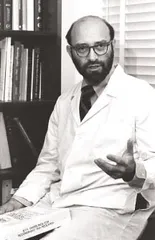 ( 斯坦利·柯恩 )
( 斯坦利·柯恩 )
1973年,柯恩从一种非洲爪蟾(Xenopus laevis)的染色体上切下一小段DNA,“偷偷”塞进了大肠杆菌的质粒中。结果这个被蒙在鼓里的大肠杆菌依然按照草图修建了一座座停车棚,全然没有意识到停车棚上的一块瓦片已经被换成了非洲爪蟾的DNA。
如果可能,科学家们肯定愿意为这个倒霉的大肠杆菌立一块碑,因为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被人工“转了基因”的物种。它的出现标志着一门新的学科——生物工程学(又叫基因工程学)——的诞生。
有趣的是,柯恩一开始只对这个间谍行为本身感兴趣,对掉包的这张新图纸的巨大潜力视而不见。最后还是波伊尔意识到了这个新技术的巨大潜力。1976年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转基因技术可以用来让细菌帮助人类生产有用的“瓦片”(蛋白质),比如胰岛素。
与此同时,一个名叫罗伯特·斯旺森(Robert Swanson)的28岁的风险投资家不知从哪里听说了这个“间谍实验”。他对生物工程一窍不通,却凭着自己的本能,相信这一新技术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他想方设法约到了波伊尔,两人在伯克利校园外的一间名叫“丘吉尔”的酒吧里聊了10分钟,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两人各自拿出500美元,成立了一家公司,取名Genentech。波伊尔辞了职,专心开发转基因技术的商业潜力。他首先看中了胰岛素,因为这是治疗I型糖尿病的特效药,肯定有市场。不过,当时胰岛素的基因还没有找到呢!
波伊尔赌对了。第二年,也就是1977年,胰岛素基因就被找到了。同年,有人尝试把大鼠的胰岛素基因转到大肠杆菌中,获得成功。那个被转了基因的大肠杆菌开始按照新图纸,合成出了大鼠胰岛素。值得一提的是,大鼠等高等哺乳动物的胰岛素不但结构相似,功能也几乎相同。事实上,在转基因胰岛素获得成功之前,医生们就是从牛或者猪的胰腺里提取的胰岛素。这种牛(猪)胰岛素完全可以用于人类糖尿病的治疗,但是少数病人会对这种外源蛋白质产生免疫反应。
1978年,波伊尔成功地把人类胰岛素基因转进了大肠杆菌,“骗”它们生产出和真品完全一样的人胰岛素。3年后,Genentech上市,股价从35美元的开盘价一路飙升至89美元。两位开创者当初的500美元一夜之间变成了8000万美元。
Genentech是公认的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也是目前世界上第二大生物技术公司。该公司去年的销售额为76亿美元,雇员超过10万人。由这家公司开发的用转基因技术生产的胰岛素已经全面代替了牛(猪)胰岛素,成为大多数糖尿病人的首选药物。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多种人类蛋白质药物用转基因的方式生产出来,包括人干扰素、人类生长激素、红细胞生成素和乙型肝炎疫苗在内的多种产品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商品化生产,没有发现问题。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转基因产品都没有毛病,这只是说明,转基因本身并不是个可怕的怪物,正相反,人类已经享受了30年转基因带来的好处了。 商业化转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