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424)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李开周,困困,布丁,舒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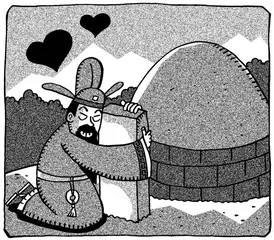
墓碑写作

◎李开周 图◎谢峰
不管哪个时代,只要有文字,那就有媒体,只要有媒体,就有为媒体服务的人,比如说,作家。唐朝的媒体不像现在这么种类繁多,那时候既没有电视,也没有互联网,担负传媒任务的,只有邸报、书籍及墓碑。邸报是官方新闻,不需要作家供稿。书籍是自费出版的,即便由书商出版,也不给版税。而唐朝又盛产作家,那么多作家,只有一部分吃上了财政饭,一部分被吃财政饭的包养了,还剩一部分运气差些,只能做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靠什么养活自己呢?如前所述,墓碑也是媒体之一,唐朝的自由撰稿人,甚至吃上财政饭的专业作家,有不少就靠这个赚钱。
墓碑很有含金量。刘禹锡写《祭韩吏部文》,说“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指的就是韩愈给人写墓碑,其稿费非常之高。还有一位叫皇甫的作家,“碑三千字,每字值绢三匹”。这种稿费标准,比起现在有些作家自定的“一个字五块钱”来,显而易见还要更牛。
韩愈和皇甫的成功例子在那儿摆着,自然吸引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写墓碑的行列。《容斋续笔·卷六》载:“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卖然。”也就是说,大家都来吃这碗饭,写墓碑的人数超出了市场需求,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在买方市场里,同行即是冤家,此作家与彼作家抢写同一块墓碑,就会闹出些不愉快。比如说,刚得知有谁家里死了人,急赶过去毛遂自荐,门口却早有一帮同行排队等活儿了;组织纪律性差些的,就不排队,“致有喧竞争执,不由丧家”。文坛里总是不免争吵,但是像唐朝时这种争吵,并不比现在作家们的互掐更体面。
我们没有理由贬低唐朝作家们的墓碑写作。坦白地说,那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市场交易,交易之后,丧家得到了文字的安慰,作家得到了稿费的补给。另外,墓碑虽小,五脏俱全,碑文是作品,丧家是读者,一块块墓碑是传媒的载体,把碑文刻到墓碑上去,就是发表,这个过程,跟在报纸上发表随笔、在杂志上发表故事没什么区别,如果您不反对,也可以把一方碑文当成一部出版发行的单行本。
想搞好墓碑写作也是要费一番脑筋的,许多有识之士“录名于凶肆”(《大唐世语·卷十三》),也就是说,在棺材铺注了册,这样可以早些得知谁家又死人了,对唐朝的作家来说,死人这种好消息相当于约稿信。我们无从知道,像韩愈这种号称文豪的人,是不是也会到棺材铺注册,按常理他会,因为作家需要吃饭。
厕所脸专栏
◎困困
英国专栏作家露西·凯拉韦,要在报纸上开一个问答专栏之前,疑惑自己是不是长了张“厕所脸”。所谓“厕所脸”,就是一群人坐屋里,走进来一个陌生人,别人都不看,就单单走向她问:“厕所在哪儿?”长一张“厕所脸”的人总让人觉得更有亲和力,特别想让人问问题,也比较适合开问答专栏。我不知道中国的问答专栏作家有没有长“厕所脸”,但大多长了张“厕所嘴”。哪个编辑要开这样的专栏,总希望写手能刻薄地对待那些提出问题的读者。
几年前的《南方周末》上,有个专栏叫“我是鸡汤”,有什么问题就发到“问一问Ask One Ask”邮箱里,他的回答不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而是挖苦一下问者,讥讽一下社会,再感慨一番人生。尖酸刻薄中还不忘了显得有文化。比如一人问,我也想去英国留学,可花钱多又滥大街,我该不该去?“鸡汤”先嘲讽了一下花了大钱去野鸡学校读书的人,接着回答:“失去耐心,相信迅速,已经开始损害我们的存在与思维。有细心的人做了统计,克里斯托弗·霍格伍德指挥的《田园》比卡拉扬的快了许多,而约翰·埃利奥特·加德纳指挥的巴赫作品《马太受难曲》更被讥为失去了庄重的缓慢,听起来像是耶稣背着十字架以舞步冲向受刑地。大师们都快得乱了方寸,我们变得急功近利看来是在所难免!”
这种有刻薄之后的文化底蕴,还不如杭州电台的万峰老师,索性斥骂一番,来得痛快淋漓。听长辈回忆80年代的“知心大姐”问答节目,轻声细语循循善诱帮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以前的人还有组织问题没解决,个人问题没解决,现在问的都无关世界观,答的又愤世嫉俗。这两年“厕所嘴”问答专栏更成了主流,连扯点文化都省略了,正义感多傻呀,只剩下刻薄挖苦。比如我常看的两个女专栏作家,同样问题问:我上一次恋爱受伤过重,随便嫁个老公,如同行尸走肉。甲女答:听起来你现在还是行尸走肉,对着镜子狠狠抽自己几个嘴巴,怎么能做这么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乙女反问:你见过不如同行尸走肉的婚姻吗?
又看几个外国的情感问答专栏,专栏作家还是一副好欺负的厕所脸。比如网络杂志《Slate》上的“礼貌与道德建议”,Salon的“既然你问了”。回答温和而无趣,都如同蒙田再世,全是大道理:“父母的权威大部分时间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兽与兽的差别远不如人与人的差别大”,“命运总是看准了时机来捉弄人”……问问题的人却厉害了,以上三条道理分别回答的是:“我发现我的父母在我床上做爱”,“我发现我女儿是个婊子”,“我爱她,可她并不知道我杀了她的爸爸”。长厕所嘴的是问者,有时候回答完全可以不看,光看问题就可了解世俗百态。
问答专栏既然允许写者没话找话地胡喷,不如让提问者也是厕所嘴,在专栏里交锋一下。反正这年头谁也不想解决问题,那就发泄个痛快。让他们看两张厕所嘴脸贴在一起好。
幸福家庭美好时光
◎布丁
今年1月,看到Art Buchwald的讣闻,就是给《华盛顿邮报》写专栏的那个包可华,林语堂说过“他有见识,有良知,机智,敢把普通社论不敢说的话,以滑稽诙谐的态度说出来”。网络上一搜,还能看到一位“活着的林语堂”评价包可华——上海作家小宝说,“在我出山以前,全世界专栏文章他写得最好”。
包可华生于1925年,2005年还在给《华盛顿邮报》写文章,他的大概路数是弄一个虚拟的场景,弄一篇虚拟的对话,讨论美国政治问题。我翻出一本书,《企鹅专栏作家》,里面搜罗了西方100多个专栏作家的代表作,看一看包可华上世纪70年代都写了些什么。他写了一篇《新新尼克松》,把尼克松拆成三个人,一个是旧尼克松,一个是新尼克松,一个是新新尼克松,“水门事件”前后,三个尼克松之间有对话,有戏剧性场面。《华盛顿邮报》传奇性的总编辑布莱特里说,包克华的专栏不会让你乐疯了,但总会让你笑。
澳大利亚一位专栏作家说过,专栏只是为读者写就,是为报纸截稿日期所写,“专栏不是为永恒而写的”,所以,包可华那些评论时事的文章,现在读起来多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有一篇代表作看起来很容易,文章叫《为什么不写一本书》,作者说,世界上有好多地方不适合写伟大的书,玛萨的葡萄园就是一个。你早上起来到大海里游一会儿泳,吃早餐,然后在看得见大海的房间里坐下,写下一本书的第一句“这是美好的时光”,这时候你看见一只海鸥飞过,又看见海上的一艘船,拿起望远镜盯着那船看上半小时,孩子们都起床了。你要送孩子上学去了。然后给孩子收拾家具,下午给编辑打个电话,告诉他这本书写得很顺利,正要动笔继续写下去,邻居过来说,海边有新打捞上来的龙虾,于是你们一起开车去海边买龙虾,书什么时候都可以写,龙虾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新鲜,总之,到了晚上,这部书稿还只有一句话“这是美好的时光……”
玛萨的葡萄园,是马萨诸塞州南面的一个岛,岛上有海滩,有很多有钱人的别墅,包可华的消夏别墅就在那上面。看了这文章,很容易想起鲁迅先生的一篇杂文,叫《幸福的家庭》,说一文学青年构思一小说,写下“幸福的家庭”这一题目,幻想书中男女主人公说着英文,吃着“龙虎斗”,但老婆买来的白菜、家里的琐碎事、几十个子的零用钱,最终让这文学青年没有写出好小说。
前些天,某女文青的MSN签名是“谁能借我3万块钱”,问她借钱干什么,她说要去希腊,办签证需要有3万块的存款证明,借钱就为办证明办签证用。问她去希腊干什么,她说要去希腊写小说。以前我也老幻想,能在大海边上找一处房子写书,但现在看,去三亚或者烟台青岛,要比去希腊现实一些,到了烟台,写不出书还可以回北京,并不损失什么,但去了希腊写不出什么来,那可是毁灭性的打击。
中医和西医
◎舒达 图◎谢峰
研究生一年级的那个春天我遭受着严重皮肤过敏的困扰。原本光洁的脸庞变成了崎岖起伏的丘陵,息斯敏、开瑞坦轮番轰炸后也不见好转。
于是闺密向我推荐了她的表妹、时为中医药大学一年级新生的未来孙思邈。一个黄沙落定的周末早晨,我在清华南门的749路公共汽车站恭恭敬敬迎接了这位将来的女药圣。药圣妹妹一身精干打扮,说话斩钉截铁,酒瓶底眼镜后面的眼神流露出出身名医世家的坚定自信,我马上长舒一口气,庆幸自己可能真的是找到了传说中济世的那把壶。药圣妹妹背着硕大的双肩背包,看样子还挺沉,但在从车站到我宿舍的路上,她不下5次拒绝了我企图帮她背一下的请求。我想我是太多事了,作为一名行将接受治疗的患者,我更好的选择可能是先向医生描述一下病情。
但是药圣妹妹仍然用严厉的眼神拒绝了我。到了我宿舍放下包,别说喝杯水,她甚至没有让我们俩都好好喘上一口气,就抄起我的手腕号起脉来。在我半是因为紧张半是因为疲劳而加快的脉搏里,她一定捕捉到了倏忽缥缈的病因。一放开我的手,她就哗啦一声拉开背包拉链,一件接一件往外掏,5分钟后成功地把我的书桌变成了一个新开张的杂货铺。药圣妹妹开给我的处方计有:参苓白术散、复方青黛丸、蝉蜕定喘汤和薏米冬瓜汤。在我对着桌上一大堆脏兮兮的知了壳子发愣的同时,药圣妹妹走笔如飞,在我的刑法笔记后面写下了一长串的注意事项:不能再吃虾、蟹、贝,不能再喝啤酒可乐等冰冷饮料,不能跑出去被冷风吹,不能深夜还不睡。药圣妹妹又刺啦一声划着了火柴,原来她还要给我做个香薰的耳疗。尽管她那支臭烘烘的香把我烫得着实不轻,但面对如此热情的没穿白衣的天使,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治疗临近结束时,药圣妹妹还免费为我们宣讲了《黄帝内经》的主要章节。我们一宿舍三个人的古文底子都相当不扎实,可我们用点头表示会心的时候却都很用力。
药圣妹妹开的方子我坚持熬着喝,直到两个电炉都被楼长作为违章电器没收了才停下来。这时季节悄悄从春天变成了夏日炎炎,我的皮肤过敏却没有见好。恐慌迫使我转投西医的怀抱,到底还是我在医科大学临床专业的高中同学拯救了我:两瓶硼酸溶液就让我可以出门约会了。但是相对于背着大包送药上门的药圣妹妹,我对这个西医同学却并不感激,尤其是当我知道他端给我吃的西瓜是放在藏尸柜里冰镇的、切西瓜的刀不久前还切开过4只小白鼠以后。 读书文学小说作家生活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