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422)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石头,削铅笔,大仙,丁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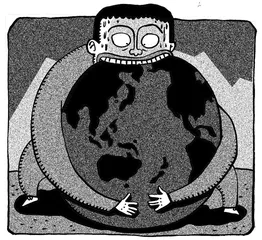
人到了一定程度——权力达到一定程度、实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疯到一定程度,脑子里就不可避免会浮现出包圆儿的念头。古代鉴于科技水平低,限制了人的想象力,包圆儿仅限于过去式:给我所有已经出现的东西,例如《永乐大典》。现代人却有更大的野心,要做包圆儿终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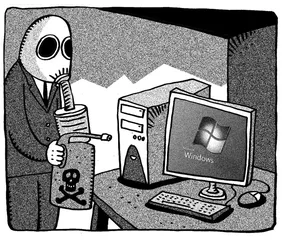
英国人戴维·洛奇的小说里有位很有派头的莫里斯教授,一个美国犹太人,研究简·奥斯汀。他有一个纯粹梦想,梦想编一本“简·奥斯汀和一切”的书,以塞众人之口。就是说这本书一旦出来,便宣告奥斯汀研究事业的终结,以后再有人不管从任何角度想研究奥斯汀,对不起,请查阅奥斯汀大全某某页,也甭管你的观点有多么匪夷所思。打算用这种包圆儿的方法还奥斯汀一个清净。
这么一说鼓励了我。其实我也有一个纯粹梦想,梦想从三皇治世,五帝为君拍起,一直拍到剪辫子穿西装,拍它几百万集的电视剧,戏说正说明明胡说非说正说一元二气三纲四维五常六畜七星八卦九嫔十帅,您说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窠里蹦的普天之下率土之滨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玄龟负书是王八祥瑞,就没有一丁点落下的。赶这部电视剧一出来,大家伙儿就看去吧,120个频道24小时连播,看谁拖死谁。从此断了不肖子孙再拍大戏的念头,也好还列祖列宗一个清净。
真挺解恨的。可是相比刘慈欣那更加梦幻的野心,戴维·洛奇或者石头,都是小巫见大巫。刘慈欣写了那么多科幻小说,《诗云》并不是其中最好的一篇,也读过很久了,却总是出其不意地从某个角落跳出来,让人没办法忘掉。宇宙中有一个神,捉到地球上一个中国诗人。神受了诗人的蛊惑,决定做一个超越李白的伟大诗人,然而总不成功。后来它编了个软件,按照格律,做所有汉字的全排列。“到那时,我就写出了所有的诗词,包括所有以前写过的和以后可能写的,特别注意,所有以后可能写的!超越李白的巅峰之作自然包括在内。事实上我终结了诗词艺术。直到宇宙毁灭,所出现的任何一个诗人,不管他们达到了怎样的高度,都不过是个抄袭者,他的作品肯定能在我那巨大的存储器中检索出来。”终极吟诗的结果,是一片与银河系相仿的闪闪的星云,其中每一片晶体上都贮存了海量的诗句,所有已经及将要出现的那些直指人心的好句,沉陷在无数梦呓之中。仰望星空,不由人不颤栗。
起名风波
文/削铅笔
最早时候我的英文名是Polo,它是马可·波罗的Polo,我可以想象这个名字跟随着马可·波罗伴着驼铃从百年时空隧道向我呼啸而来。它还是polo衫的polo,红的,绿的塞满我整个衣橱。最重要的是它是意大利语,因此在我看来,无论是发音还是字母都相当迷人。可是当我主修葡萄牙语,需要起葡萄牙语名字的时候,才知道不能再使用原本的英文名字了。那是在葡语视听说课上,葡语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两列name list,一边是男孩子的名字,一边是女孩子的名字。
我的选择是Paulo,因为我觉得它和Polo很相似,可是老师觉得不妥,她说前两届师哥都有叫Paulo的,而且这个名字适合比较肥胖的人。我除了知道食物有男女之分外,没想到名字竟也有胖瘦之分。情急之下我选择了另一个名字,Felibe。因为我非常喜欢《Friends》里菲比这个名字,何况Felibe还是一个男孩子的名字。老师也同意并且登记在花名册上,于是我就兴高采烈地带着自己的新名字离开了。
后来在食堂或其他什么地方碰到了杨班长,她说她课上起的名字是Linda,但她是非常非常不满意的,她想要换一个新名字。也就在那时我才明白当初选名字的范围太小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字典里好好挑一个名字。
回宿舍后我就开始抱着字典大翻起来,一开始我非常想找一个以F开头的名字,之前在一本外国杂志上说鬼佬们偏好以F开头的名字,因为这样念起来非常悦耳,哪知道查完所有以F开头的名字后都没有看见一个称心如意的。于是我开始耐心从A到Z挨个挑,一边挑还得念出声来,防止音不副其实。翻了两三遍都没有收获,就在我心灰意冷地妥协继续叫Felibe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了 scar这个名字。
于是我便开始了在广院叫 scar的幸福生活。有一次和同学去找外教Lilyana,她拿出一本葡语名字释义,我一查竟发现 scar于我的个性极其吻合。Lilyana翻译给我说 scar这个名字来自日耳曼。在葡国很多作家都叫 scar,看来在葡国人眼里,这个名字还是有文采的,不至于有一天到了葡萄牙被人笑话。
我的室友叫Tiago,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因为用巴西的葡萄牙语念起来和“我爱你”的发音非常像。我另外一个室友叫Ricardo,在世界杯期间叫应该会比较振奋人心。
这几天新闻上到处都是新一届奥斯卡奖提名的消息,当我看到图片中那个叫 scar的小金人,还有背景上用金字写的 scar时,心情都相当激动,好像上了红地毯般。没想到短短一年,我就和这个奖项有了多多少少的联系。
公车上书
文/大仙
首都公交打折以来,媳妇买了“交通一卡通”,我有时也蹭着用。刚开始,上车刷卡还不习惯,一忙叨就把《北京青年报》发我的胸卡当交通一卡通乱刷,刷得售票员直犯愣。后来我越刷越利索,这种错误就不再犯了,交通一卡通就是好,四毛钱能从大望路坐到天涯路,要坐出租车一起步也就没了。所以,我给“交通一卡通”写了一首中年儿歌:交通一卡通,幸福往上涌,花了四毛钱,城西到城东,花了八毛钱,旧宫到故宫,花了一块二,寡妇见老公。
至今我还保持着出行坐公交车的习惯,比如坐特3到单位上班,专挑印有孙燕姿大照片的车坐,在她那句“统一冰红茶,年轻无极限”的忽悠下,感觉自己“夕阳无限好,朝霞更满天”。我最烦坐车身印有“李文开锁”的公交车,香港歌星什么时候学会开锁了?我的心好不容易刚上了一把锁,不让自己心猿意马老起邪念,有人就要给我开锁,把邪恶的念头放出来,非让我对人生放弃把持。
20多年前,我天天坐公交车上下班,公交和我心连心,没有公交步难行。那时候的公交车比较非理性,不是大站停小站不停,就是小站停大站不停,而我经常在介于大站与小站的中站下车,等了半天才能等到中站停的车。还有比非理性更加妖蛾子的公交车呢,比如那时我老坐的302,车一进站售票员就喊:就到和平街北口!我当时就急了,质问售票员:凭什么呀,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到完和平街北口你干吗去呀?售票员也不客气:你管着吗?我爱干吗干吗!还有的车,比如403,一进站售票员就报:牛王庙、东大桥、永安里。我半天没反应过来,是这三站不停呢,还是就这三站停?后来我的语言反应如此之快,就是那时被售票员报站名给训练出来的。
那时,正值我文学青年旺盛的发育阶段,在拥挤的车上,一手扶着车,一手托着书,扶着的是公交车,托着的可是世界名著。在列·托尔斯泰和阿·托尔斯泰之间,感觉自己是仙·托尔斯泰。我在车上看的更多的是诗歌,有一次看得兴起,竟把郭沫若翻译的歌德从默诵变成了朗诵: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郎哪个不曾怀春?这是人间的至善至纯!可是为什么会有惨痛飞迸!在全车人异样的目光中,我感到自己是一个“诗歌病人”。管着吗?我心想:这是艺术!
还有一次,我面前坐着一位留着“扣边儿”发型的女孩,端庄肃穆,很像过去常在筒子河边儿溜达的林道静。我的诗意立马盎然,掏出小纸片就开始抒写。公交车一颠一颠的,笔尖儿一颤一颤的,我在洁白的纸笺上为“扣边儿女孩”写下海涅的诗句:“星星们动也不动,高高地挂在天空,千万年彼此相望,怀着爱情的苦痛。”趁着她凝视窗外的工夫,我把海涅的小纸片塞到她天蓝色牛仔裤与座椅的缝隙中,然后急忙下车,心像小鹿一样通通直跳。
杀毒记
文/丁凌云 图/谢峰
这两天给家里电脑杀毒,有一个“灰鸽子”变种病毒总杀不掉。我把瑞星升级到最新,又安了Ewido木马专搜,每次开机还是会提示找到那个病毒。我一时被它折腾得晕头转向,于是转向求助于“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在bbs给我留言,解决方案就一个英文单词——Ubuntu,我以为是什么又新又牛的杀毒软件,赶紧一搜,才知道原来是另一种操作系统,Linux内核的。我本来就头晕目眩了,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我又问了另一个“专业人士”,这人还“厚道”点,留言是一句话:“我早就摒弃Ubuntu转投fedora怀抱了。”得,问询的结果总是这么让我悲愤不已。
电脑技术本来是为了方便人们的生活所创,到了现在,反而形成了等级分明的技术门槛——几个人制定协议标准,一撮人共同开发,一群人开始使用,最后形成这派那派,看着似乎是“玉米”“凉粉”。用苹果的,用Unix的,Linux的就是高精尖,要么三维界面,要么全DOS界面,透着霸权垄断射出来的酷劲——我有这知识,我会高精尖,你不会吧,赶紧学去吧,学会了就不觉得麻烦了。我是不会,而且就为我这点破需求就学那么多高精尖干吗呀,我们门槛是低,我们用户群却最多呢,你们曲高和寡有什么用?吵架干仗一开始,紧接着就是隔阂和偏见,于是无聊就出现了。
牢骚发完,还是得面对问题,鉴于“专业人士”给出的解决方案着实不靠谱,我冷静下来仔细分析了一遍这个“灰鸽子”变种,每次它都是一开机就迅速感染iexplore.exe(就是IE浏览器),让这个倒霉蛋不停地被杀毒软件解剖割瘤,自己反而悄无声息地隐藏了,当真狡猾至极!我就想出一个办法,你不是每次都借鸡下蛋吗,我把鸡藏起来你不就现形了嘛。于是我进安全模式,把iexplore.exe放进回收站,再进普通模式。就在他满世界找“鸡”的时候,我用瑞星“灰鸽子”专杀工具,一下子就把那小子给揪出来了。我心里一阵惬意,原来傻大憨粗的杀毒软件,也得靠我聪明的头脑指路!跟“专业人士”一交流,他们说:“你这小心眼耍得还挺好”。与人斗,其乐无穷啊。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