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法国小说:得大奖的和好看的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苌苌)

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两本近年的法国小说,弗朗索瓦·威尔冈的《在我母亲家的三天》和让-保尔·杜波瓦的《一个法国人的一生》,两本书放在一起看挺有意思,如果让你猜猜2005年的龚古尔奖青睐哪一位,你觉得会是谁?还是用10万字写3天比用20万字写一生,更符合刻板的、注重文学性的龚古尔评委的趣味。
威尔冈的小说采用小说套小说的结构,前半部分像是一篇写作笔记,主人公就是一个作家,打算写一本《在我母亲家的三天》的小说,具体构思尚未完成,但他和出版社都对这个事先想好的书名很满意,版税甚至已经预付。他决定去看望住在南方的母亲,寻找灵感,却一直不能成行。似乎下一分钟就可以踏上回母亲家的路,但他总是拐到岔路上去,忙于日常杂务,阅读,处理和女人的关系,或者被其他写作题材分心。
在小说的中间,威尔冈附上了小说主人公、作家威尔格拉夫写的小说《在我母亲家的三天》。没有他的“写作笔记”好看,这种小说套小说的结构也不是评论的重点,因为早已有人用过了,但威尔冈发扬了这种结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较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对威尔格拉夫生活状态的描述,如何被有选择性地取材,经过想象力加工,运用到他的“小说”中。在这篇“小说”中,威尔格拉夫笔下的主人公威尔斯坦也正在写作一本小说《在我母亲家的三天》,于是作家威尔冈在这本小说里创造了双重甚至三重自我。
再回到威尔格拉夫的生活,直到年近九旬的母亲在花园摔倒受伤,他才和5个姐妹一起赶到她身边。终于能在母亲家待3天了,可母亲却在医院里。母亲一直关注他的写作,恢复意识后,她说:“我没有为你的小说提供一个结局,但我为你摔了一个精彩的跟头。”母亲摔倒后,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在花园里躺了两天,小说中最感性的叙述由她娓娓道来:“我两次看见太阳升上淡紫色的无际的天空,我听见各种各样的声。我永远也想不到有那么多动物走过我身边,我看到一条灰蜥蜴,它的目光是那么亲切,我惦念着你,就跟它说了。”母爱是人生永恒的主题,这位总是显得漫不经心的作家终于流露出内心深处的温柔。
“我能生活在法国是多么幸运啊!在美国,对作家是不会这么宽容的。”书中主人公感叹道。威尔冈是那种似乎不怎么考虑读者的作家,意识流式的叙述,有时离题万里,忽地就讲到沼泽地蝴蝶的生活,但书中不乏一个60岁的法国知识分子对人生的感悟。威尔冈是个作家的儿子,但是父亲要求他从事电影而不是写作,于是他成了电影评论家和导演。直到1997年才开始发表小说。这“三天”花了威尔冈7年的时间,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拖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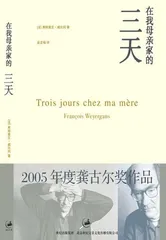 (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
(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
小说中有多少部分来自真实生活我们不得而知,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作家的生存状态就在他絮絮叨叨的叙述中展现出来:主人公无论干什么心里都惦记着那小说,为此焦虑不堪,却宁愿去忙别的事情。版税花完了,税务机关来讨债,编辑对他绝望,而亲人对他忧心如焚。人为什么要拖延?是个心理学家几经探讨的问题,从事创作性工作的人更容易成为拖延者,比如达·芬奇。一个结论是,躲避艰难的工作引起的焦虑,而这焦虑可能来自拖延者追求完美的个性。威尔冈曾经在他妻子说他写得不好时,毫不犹豫地扔掉了200页手稿。可为什么关于母亲的题材,比一本写火山的书更让主人公威尔格拉夫难以思考下去呢,只有去书中寻找正确答案。
无论如何,旅行中最好别带着《在我母亲家的三天》,那会让你睡着的。相对而言,《一个法国人的一生》是比较好看的小说,近50年发生的世界大事和法国政治事件嵌入小说的时间背景中,干脆以总统的任期划分章节,从戴高乐写到希拉克。由此,一个法国人的一生和时代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作者杜波瓦从主人公的童年讲起,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他10岁的小哥哥死了,这种伤痛贯穿了他的一生。除此之外,主人公的个性是模糊不清的,也许是作者刻意弱化的结果——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年届半百的法国男人身上。家庭作风开放的男同学给了他最早的性启蒙,青年时代和朋友组乐队,为了文凭学习,参加“学运”,带女友非法堕胎,后来被一个好婚姻拘囿,远离青年时代的放纵,成为家庭妇男,在不知不觉中,跨越了小资产阶级的阶梯进入资产阶级。经营公司的妻子很能干,顶住了金融风暴的冲击,但在全球化中败下阵来。他本人成为摄影书作者,获得意外成功,经历了一番风光。然而,在生命即将进入老年时,他却不得不面对一系列人生的打击。
关乎一个人命运的小说,很能引起人的阅读兴趣,更何况作者有老练的通俗小说作家的文笔,无论是伤痛还是兴奋都被推至极端,主人公的命运起起伏伏,强烈牵动着读者的情绪。另外就是那些所有人耳熟能详的世界大事,总是出现在主人公的生活背景中,虚实相交。“我原原本本记得1967年11月8日的那个家庭晚餐,在那时,电视宣布了格瓦拉的死。”在学生们占领南特学院所在地政府的那一天,他开上了他的第一辆小汽车,在法国最后一个死刑犯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天,他的儿子出生了。比较有喜剧性的场面是他和一个女孩初次在汽车旅馆幽会,那天也是阿波罗登月的日子,女孩完全被电视里3个穿着航天服的人吸引过去了,懒得搭理他。
小说虽然好看,就是有点肤浅。这个青年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后来成了一个愤怒的中年。先是戏谑一番密特朗,拒绝了给总统拍摄照片的请求,又说希拉克是个“土里土气的没有一点策略的政治家”。为什么那么讨厌他们?书中没有写,不清楚法国读者读来是否有默契,但外国读者读着难免觉得莫名其妙。他提到各种各样的事件,甚至参与其中,有时发表态度,表明左翼立场,但经常显得不够冷静,没有任何具有洞察力的见解。涉及了尽可能大的时事信息量,尽可能多的人种:他的一个情妇和一个犹太教士好上了,因为怀孕而被教士嫌恶;老友中年危机,抛妻弃子,爱上了年轻的马格里布女郎;儿子娶了个日本太太,她的叔叔,一个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有一段很日本式的故事,因为未能给国家增光而自杀。
在杜波瓦的笔下,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的结合,大多带着消费社会的烙印,小说最后是一个《达摩流浪者》式的结尾:“我们处在虚空的边际,在世界的峰顶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这是个完全清楚读者想要什么的作者,总让人怀疑他的诚意。然而帕慕克的出现,已经证明小说的好看性和文学深意并不矛盾,法国当代小说还有很多需要弥合的地方。
“20世纪末至今的法国文学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作家死了以后大家乱写,群龙无首。”法文翻译家余中先说,“有的人标新立异,不从属别人。有的关注现实,随着时代变化笔法,但是再也没有有分量的作家的作品,比如对社会现实对人存在状态的深刻关注。”目前出版社正拜托他审读的获得今年龚古尔奖的美国人乔纳森·利特尔用法语写的《善良者》,在他看来是近年少有的特别让他眼前一亮的作品,这部小说通过一名前纳粹高级军官的内心独白,记录了纳粹在“二战”东线战场迫害反抗者和犹太人的暴行。只是900多页的长度让他犹豫是不是接下翻译的工作。
“法国文学的规律很有意思,每个世纪之交都是通俗文学占上风,中间则出现各种流派。”《法国小说发展史》的作者、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中国法国研究会会长吴岳添说,“20世纪的法国文学出现过超现实主义文学、存在主义文学和新小说,究其本质,都是以表现世界的荒诞为己任。到了七八十年代,现代派小说盛极而衰,1984年,杜拉斯的《情人》大卖,开创了世纪末通俗小说的繁荣。这之后法国小说就没有流派了,全部都是通俗文学,这当中有档次高的也有档次低的,法国当代小说的特点,就是作者关心的都是人的存在状态,描述的是很个人化的感受。有的作品反映学生运动、战争,有一些政治元素,但不同于‘二战’期间大家一致抗德,而是派别分立,社会价值观分化。不过从以往的文学发展规律中,可以预料到在新的文学流派必然会在新世纪开始不久之后产生,也许就存在于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的作品中,现实主义小说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汲取了现代派的手法和观念,未来的法国文学必然在此基础上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小说大奖法国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