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化艺术:第6届上海双年展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苌苌)

观念:仍然和艺术有关
今年的上海双年展的主题是“超设计”(Hyper Design),“思维上的变化蛮波澜壮阔的”。总策展人张晴说他自己也是刚刚跨过“超设计”的门槛,在过去的两年中,双年展的策展人团队不停地延伸这个主题的深层含义。他用了几个例子,打破了一般人常识中关于“设计”的狭隘定义:“在《鸿门宴》中,设计是谋略;在《牡丹亭》中,设计是超越生死的戏剧性;在现实中,‘一国两制’、‘美伊战争’、经济模式、俩人谈恋爱,无不是一种设计。等把作品拿出来,又发现‘超设计’是流动的,变化无穷。”
来看展览的悉尼双年展主席露卡·尼茨(Luca Belgiorno-Nettis)女士觉得这个主题很好,“反映了当代艺术的特征,是艺术上一个重要的思考”。“超设计”的英文名字,“超”采纳的不是super,不是trans,不是beyond,而是用了一个比较让人晕菜的“hyper”。包括中国美院院长许江在内,各位策展人、馆长、每个人都给出了不尽相同,但又彼此融合的解释。
历届上海双年展的主题——“海上·上海”、“都市营造”、“影像生存”都是和这个母体城市相关连的,今年也不例外,“超设计”恰恰再现了上海发展的语境。hyper来自希腊语,字面上的意思是“在……之上”,在德语中至今还体现着这层含义,尼采提出的对哲学产生震撼力的“超人”概念,就是以这个字作为词首。意大利波伦亚现当代美术馆馆长伽弗兰科·马拉涅罗是本届双年展的策展人之一,他说:“Hyper明显带着‘过剩’的意味,是对规则定式的挑战、竞争和反抗。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就挺‘超设计’的,新的摩天楼不断涌现,在老街上投下阴影,城市景观由各种元素拼合而成,而不是连贯协调,上海的城市建筑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自由度,也因此成为展示当代艺术的绝佳场所。”
按照策展人之一黄笃的理解,“超设计”是一个当代的概念,应当表现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技术美学、艺术和人之间的关系。“超设计”就是再设计、解构设计、反设计,是把设计作为一个超越对象,分析其深层文化含义。许江说:“‘超’既包含被修饰物的某种超越形态,又包含着被修饰物走向反面的词组暗示。与‘设计’组合在一起,一方面呼唤我们的设计要跨越,另一方面唤起我们对设计无度现象的警觉。”“总之,‘超设计’就是无法设计。”张晴说。

在这个变化无穷的策展理念指导下,可纳入其范围的艺术作品,可以海量来形容。但在上海美术馆馆长李磊心中还有一把现实的尺子:“展览法律上的责任由我来承担。”李磊说,他的原则是使上海双年展成为中国文化建设中一个积极的建构因素,而非解构因素。“第一,要渐进式革命,而非暴力式革命;第二,上海美术馆要为老百姓服务,而不只是一小撮学者;第三,有责任给公众健康的引导。当代艺术首先要活着,长期性可持续性地活着。对于咱们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构建和谐社会,我们不是政治家,但我们应该有社会责任。”
“超设计”不是讨论设计问题,而是用当代艺术的方式,用多样的媒介,讨论当代设计化生存的问题。2006年上海双年展打开了设计与想象、艺术与设计、艺术与日常实践的边界,并且充分照顾到了公众的接受程度,7个分别来自英国、意大利、韩国等地的策展人挑选了来自世界24个国家的118件艺术品,大多数明亮、安全,令人愉悦,不会超出你对一个政府行为的艺术大展的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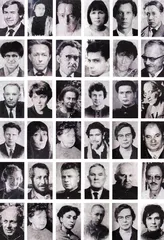
没有潮流,只有风格艺术家
当代艺术是一个国家当下生活状态最前端的体现,它的发展和社会转向有密切关系。半个世纪前,美国上上下下为波普运动推波助澜,因为战后膨胀起来的野心,纽约想和巴黎争夺世界艺术中心的位置;60年代,“贫穷艺术”在意大利兴起,因为国家经济繁荣,美好一片天,艺术家不满意自己被忽视;出现于我国的政治波普,也是和国家转型中的矛盾冲突有关。90年代以后,世界格局发生转变,苏联解体了,乌托邦破产了,世界变平了,恐怖主义把我们吓颓了,群体性运动玩不起来了,没有了集体解救方案,自救吧。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中国的艺术和西方处在同一种标准下——市场化强调个人的存在,个性加强,个人化突出,消费关系决定了明星艺术家的诞生。没有这个主义那个流派,只有村上隆、达米安·赫斯特、张晓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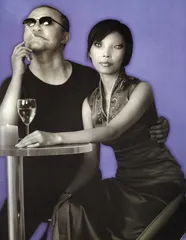
难以说清世界当代艺术的潮流是什么,因为“多元化”就是它的潮流。全球化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只有经济原因造成的特殊景况下的小潮流。其中一个趋势,是由那些明星艺术家带起来的后现代风格主义。参加上海双年展的美国艺术家马修·巴尼就是引领这种风格的“三剑客”之一(另两位是以铂金和钻石打造人类头骨的达米安·赫斯特和从《外星人》、《指环王》中提取造型的帕特里夏·皮西尼尼)。
后现代风格主义承袭自巴洛克艺术。“巴洛克”在艺术性上着重强调感情投入、流动感、戏剧性和夸张性,马修·巴尼从第一次染红头发,装扮成怪里怪气的人面兽模样时,就上了这条道儿了。他的参展作品是和歌星女友比约克合作的《涂绘约束》第9号,这是一部试验影像作品,以日本文化为依托,讲了一个关于“茶事、凡士林、神道秘密婚礼以及鲸鱼变身”的故事。片中比约克要在一只装满数千加仑凡士林的大盆中沐浴,欲图说明人的意志力在身体处于物理性约束下,所能达到的极限。

按照鲍德里亚的观念,后现代的一个特点是“仿真”。后现代幻象,或者说,后人类想象——叙事抽象,紧密结合技术美学,制造出另外一个现实,《黑客帝国》是其典范。马修·巴尼的美国式当代艺术,还带着高度发达的技术化社会和发达资本主义文化的特征,这部以他的想象世界为蓝本的电影是拿钱堆起来的,在一艘停靠在长崎湾的日本捕鲸舰队的母舰上拍摄完成,有好莱坞大片的质感,曾经参加过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并且进入商业渠道发行。“艺术娱乐化”,也是当代艺术的一个潮流之一。2000年,在美国沃克艺术中心举办的“让我们娱乐吧——生活的负罪快感”展览,大约就是这个趋势的开端。
“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寻找一种均衡性,是这届双年展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保持这种均衡性对观众来说,就是作品容易阅读,但也不是简单的快感。”黄笃说。他找来的荷兰艺术家马尼克斯的参展作品《跑步机》是双年展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马尼克斯的作品总是和观众形成有趣的互动,两个月前,他刚参加过在北京举办的新媒体艺术大展“代码:蓝色”,那次他制作的多媒体装置《空间声音》会随着参观者的数量和动作改变运动状态,如果现场令它“不舒服”,就会发疯般地转动、尖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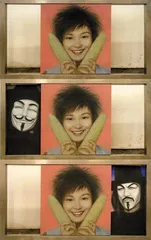
跑步机的尺寸是5米×2米,面对一张8米×4米的大银幕,参与者跑动的状态决定了影像的变化。如果跑得很快,就出现体育场的场景,如果脚步犹疑则出现幽暗的街道。电影的名字带着艺术家的情绪,叫《RMR》(Run Motherfucker Run),马尼克斯对记者说,他的作品反映了社会发展与生存速度的关系,总之是件挺让人焦虑的事儿。马尼克斯大概是在现场待的时间最长的艺术家,因为他总担心玩的人会摔下来,这个作品体现的控制与反控制,也是这个时代的隐喻。可惜他不能老在那儿看着他的大玩具,展览开幕后不久,《跑步机》就因为有观众受伤停掉了,但后来又有观众给上海的报社打电话投诉,报社向双年展反映了情况,跑步机才又开动起来。
在《涂绘约束》中,比约克和她的爱人变成一对鲸鱼,他们用后颈上的类似鲸鱼呼吸孔的小孔呼吸,让人不禁联想到一部参展动画作品《新山海经》中所表现的怪兽“廷独”——“北溟之中有巨兽焉,能潜行海底数千里,体黑皮坚,背有孔,常有小鱼跃出,高入云端。”这“廷独”八成是鲸鱼变的吧,来自日常的幻象,如梦一般的图像和叙事,是艺术家邱黯雄相信的预言和对世界真实的描述:“极端荒谬的事情往往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而我们却习惯编造一些怪谈让人大惊小怪。”
有人说,好的艺术就是过500年它还在那儿,对于某些作品来说是这样:比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比如特蕾西·艾敏写满和她睡过的男人女人名字的帐篷,相信也会如此,如果不是一场大火把它烧掉的话。却也有艺术家主动选择让自己的作品消失,王音的参展作品《肖像》,是他根据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传记中出现的照片创作的一幅苏联老知识分子的群像图。他在颜料中混入了特殊物质,画会随着时间转变慢慢褪色消失,加上所使用的已被逐渐淡忘的苏派画法,正好吻合了索尔仁尼琴的文化语境。
刘建华多年来一直用日常生活用品表现社会问题。他曾经用瓷器碎片组成一只巨大的航天飞机的形状,讲的是人类依赖高科技发展的同时,它易碎的一面仍具有不可修复性。这次他的参展作品叫《义乌调查方案》,刘建华说他在确定参加双年展之前,就一直想以义乌的商品生产模式作为解读对象,却正好符合了这次展览的主题。小城义乌作为小商品批发集散地和加工出口地,每天有1000多个集装箱从这里运往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双年展的展厅里,大量的小商品从集装箱内涌出,折射出复杂的全球地方化(glocal)经济关系,仿佛一个预言。虽然所有商品的“低设计”在实用性、流行性、低成本和廉价劳动力上找到很好的结合,但是,这种模式会为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关系带来什么?我们知道这些廉价商品使世界降低了通货膨胀率,抵消了油价大幅上浮可能带来的物价上涨,但还有些影响是无法预测的。
不是所有作品都如此严肃,令人愉悦的更多。奈良美智的超级大南瓜娃娃,朱里安·奥培舞动着女人性感线条的发光二极管灯箱,李小镜的简单、直接、粗暴地表现人类兽性的《夜生活》数码摄影作品;克里斯·容坎的《企鹅》——以企鹅出版社发行的一行禅师《正念的奇迹》书脊为主体的观念绘画,都是市民喜闻乐见的作品。本届双年展在选择作品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观众的接受程度,没有白辛苦,第一个双休日的观众流量达到7600多人,超过了前一阵火爆上海的印象派画展。
观众很可爱,观众能吃粗粮
“上海的观众很可爱。”张晴说,在双年展筹备的两年间,他跑遍全国上百个艺术家工作室寻找符合感觉的参展作品。他说这座城市市民海纳百川的特性,给了策展团队在选择作品上的信心。“上海市民喜欢新鲜时髦的东西,你要给他看一般的东西,他会看不起你,给他看怪的,看不懂的,他会觉得蛮好,这就是上海。”
尽管如此,上海双年展似乎并没打算在占领亚洲地区的艺术大展的制高点上多走出一步。上海从地缘上来讲是个很独特的城市,半殖民的历史,经济发展最热的地区,现在是最有活力和潜力的都市空间,也是照向国际的反映当代中国都市化生活的镜子。双年展避开了“地缘政治”的陷阱(比如过多地讨论身份认知问题),对艺术家的选择是开放的,芜杂多变的。本届双年展的精神是“把机会给大家”,但是,我们无法用“大声展”的标准来要求背负着一座城市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期望的上海双年展。看到了良莠不齐的艺术家作品,还有一些好像是手工艺者来参展,就觉得很刺眼。参展的中国艺术家还不如去“光州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腕儿大,有些人没请的原因是因为以前参加过了。如果说双年展不屑用西方那套评判体系,但外国艺术家又请了几个明星过来,中国这边的噱头是漫画师几米。
当代艺术的发展总在两个极端中徘徊。当一个时期,它过于理性化的时候,就会走向娱乐化的那一端,反之亦然。2006年上海双年展恰好走到了娱乐化的这一端,无论是上任一年多的馆长,还是参与了四届双年展策划的张晴,或是职业策展人,都很认同这一说法:“我们以前太忽视观众了!”双年展的一个策展动机是摆脱观众和作品之间的障碍,好看的,好玩的(互动)作品比比皆是。本来娱乐性和学术性也可以不那么矛盾,比如美国展览“让我们娱乐吧”就曾引发大讨论,而上海双年展在娱乐化上走得还不够极端。除了主题讨论之外,双年展想在学术上突破的另一块,却又引来争议。
艺术发展到现阶段,矛盾是全球化和民族性之间的进退。今年的双年展比较强调中国性,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是民族自信心上升的标志。也许本意是好,张晴说:“以前我们是设计大国,现在都是在抄袭,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很荒诞。”他说想从古代寻根,思考“超设计”问题,带动中国当代艺术史中的一种形态:“当代艺术的批判性和先锋性,不一定非是生猛海鲜,而可以像绵里藏针一样。”就是这棉花团太大,针藏得太深啦。两个展览中有些作品因为缺乏富有想象力的“转译”,或者需要文本来配合解释,而显得缺乏活力。“挪用”是艺术家最司空见惯的手段,也曾经让评论家津津乐道,但现在让人审美疲劳。
今年,上海双年展是和首届新加坡双年展、韩国光州双年展同期举办的。几个月前,三大展览的负责人在东京开发布会做宣传,吸引西方的艺术观察家和爱好者前来,做亚洲艺术大展三地游。两小龙国家的双年展都有大量资金投入,新加坡双年展的预算是上海双年展的20倍,光州双年展的预算是上海双年展的10倍。上海双年展尽管得到市政府持久的支持,经费仍然捉襟见肘,多数艺术家还得自己掏腰包做作品。李磊讲到他们布展时碰到的一个典型情况,如果想实现把地板提高15厘米的想法,就不够钱做艺术作品“斗拱”,如果做斗拱就不够钱做地板。“具体预算不方便透露。我国不是那么有钱的国家,我们一天到晚在筹钱,但也没有那么多赞助。我们给艺术家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贫穷的艺术家当然会给补贴,我们也尝试寻找别的途径,比如那个斗拱,大家很赞成,但钱还是用在了地板上。后来是由一个企业家出钱,展览结束后,作品就归他所有。”
一个大型展览难免会有争议,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来看展览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主席塞缪尔·凯勒就觉得双年展很好,他说:“我看到一些作品太有意思了。以为是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一看是外国人做的,而以为是外国人做的作品,却是中国人做的。”前者他大概指的是容坎以寺庙为主题的油画,以及查尔斯·桑迪逊用飞旋的方块字做的多媒体投影,表明中国艺术家淡化了民族情调和符号化的东西,而西方人开始关注中国文化。伦敦大学Goldsmith学院的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斯科特·拉什看着乌泱乌泱的参观人群,直说难以置信:“简直跟威尼斯一样!人的参与很重要,反映了一个城市公共文化的影响力。”在他看来,上海双年展已经获得了成功。■ 娱乐上海艺术双年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