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苗老汉聊天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苌苌)

黄苗子老人93岁了,最近他出了一套书,本来他想叫这个系列为“苗老汉聊天”,可除了他自己,周围人包括出版社都觉得这书名不太合适:和他同辈的人,称他为“苗子兄”,小一辈尊称他为“黄老”,“苗老汉”只能他自己拿来和自己打趣,别人都不好意思开口叫。
说聊天倒真像聊天,每篇长度不过几百字,大部分是80年代他旅居澳大利亚时给报纸写的专栏,无主题限定,每天500字,拉拉杂杂地谈天说地。整理出版期间,又找到一些70年代的笔记加进去,共分成8大类。三联书店今年8月先出版了其中的4类:《世说新篇》有点像《世说新语》,黄苗子书中讲的是他所熟悉的朋友和师长,活跃于五四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文化名人,如沈尹默、张伯驹、沈从文、钱钟书、老舍、侯宝林等人的小故事。《茶酒闲聊》讲茶事,讲钟表,讲广东老家的豆腐,老上海的酒肆。《人文琐屑》讲社会风俗,京城往事,民国野史。《雪泥爪印》是老人晚年游历欧、美、澳、非洲的游记。
文字读起来很轻松,宛若一条波光粼粼的历史长河在眼前缓缓流过。黄苗子是个有阅历的老人,他曾经和张大千、齐白石交往,和邵洵美同桌吃饭,和旧时代明星是好朋友,和大玩家王世襄做邻居,和启功称兄道弟。采访中他总结自己的一辈子,说自己比较幸运,一是受朋友的好处比较多,因为“他们都比我学问大,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二是自己活得长,且没有为疾病所累,有时间和精力把前尘往事记录下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文艺的兴趣是否与家庭有关?
黄苗子:小时候我和家人住在香港,我父亲是晚清秀才,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在一份和孙中山有关的报纸《大光报》任总编辑。他每天给8个报纸写小说社论专栏,放了学,我就去帮他送稿。我父亲喜欢看书,那时香港是文化沙漠,进步的杂志报刊都是从上海来的,我跟着父亲看了很多,中学还没毕业,就自己跑上海去了。那时上海在世界上经济算比较发达,物价便宜,一个亭子间的月租在10块左右,再加9块钱包一日三餐,生活比较简单,就有很多时间交朋友。我在大众出版社当编辑,加上父亲的关系,接触面广。当时的名作家丽尼是我的同事,叶灵凤、郁达夫、张大千他们待我都很好。那时徐悲鸿在南京,经常来上海,我们时而见面。还有邵洵美,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了,之前也是被埋没很多年。那时他在出版界,所以彼此熟识,经常一起吃饭,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文艺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你最早是画漫画的,后来怎么开始写作的?
黄苗子:刚到上海的时候,叶灵凤常带着我坐双层电车在上海滩兜风。有次我问他,你散文写得那么好,可不可以教我写散文。他说只要会说话就可以写散文,最好的锻炼方法就是记日记。那时我住在祖父的一个学生家,那位伯伯抽鸦片,晚上睡得很晚,我就坐在他的大烟榻上听他谈掌故,晚清的明朝的,拉拉杂杂的,就成了我最初的笔记。

三联生活周刊:你和郁风老人就是那个时期认识的吗,后来你们伉俪成了文艺界的美谈。
黄苗子:我们在上海认识,在重庆结婚,到现在60多年了。我们两个人对文艺有共同兴趣,有共同的文艺美术界朋友相互熏陶。有共同兴趣就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家庭生活也不觉得枯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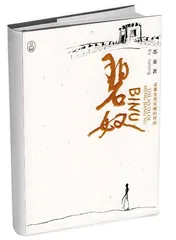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中提到,你们夫妇在反右后和王世襄、张光宇做过一段邻居,他好像很好奇这么不搭界的几个人怎么会住在一起?
黄苗子:不是有个“二流堂”么。在重庆时候,我们的一些好朋友,金山、张瑞芳、吴祖光他们没有房子住,唐瑜就盖了座房子,让大家住在一起。这些人平时都是吊儿郎当的,有一次郭沫若去看他们,早上10点钟,这帮人还没起来,就很失望。当时正好有个延安来的文工团在重庆表演《兄妹开荒》,里面管那种好吃懒做、晚睡晚起的人叫“二流子”,徐冰就和郭老开玩笑说:“你给他们写个‘二流堂’挂在门口。”当时没找到笔墨,但“二流堂”就传出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到了北京,我们这拨朋友都住在长安街旁的南观音寺胡同,二流堂在反右时候成了政治问题,说是自由主义。上面组织一个专案组对付二流堂,不准我们住在一起。王世襄那时在音乐研究所,老来找盛世伦串门,我们就认识了。他说他们家有空房子,邀我们过去住。当时王世襄有一批老朋友,是文物界的专家,他本来是世家子弟,文学修养很深,我这里是一批画家和文艺家,这些朋友常常来往。张光宇是我们的老朋友,正好也在找房子,就搬过来了。张光宇以前也是画漫画,建国初期,和兄弟张定宇一起,中央许多的大型活动,五一节、国庆节的所有大型集会会场布置,都是他们设计,用什么颜色,怎么排队,张先生应是节庆装饰艺术的鼻祖。
三联生活周刊:王世襄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黄苗子:一开始觉得王世襄这人很怪,他生活十分简单,老穿着一件旧式大褂,常常到处跑。当时明代家具都集中在一个叫鲁班馆的地方,最好的家具拆开做算盘卖掉,王世襄着急,天天去,淘了很多家具,经常看他一个人扛着件家具回来。王世襄非常用功,我们住邻居时候,每天早晨,我是5点一定起来工作的,可每次我起来时候,发现他家的灯已经亮了。还有一次给我印象很深,我回家已经很晚了,看见王世襄和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在路灯下聊得正欢,上前一听,他们正在聊怎么种好菊花和竹子。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自序中引聂绀弩的诗句:“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凡老始知。”对我们来说是个警钟,可放在你身上,是不是太自谦了?
黄苗子:回顾我的一生,这两句话确实是我的写照。年青时我在上海是画漫画的,后来没那个环境,就不画了。我也喜欢写诗,出过两本诗集,我什么都做,书法、绘画、旧体诗,但就是票友。我有自知之明,讲学问,我远不及我的那些朋友,羡慕他们这么用功,到老来有成就。这辈子我浪费了很多时间,运动来的时候,想做的事情不能做;再一个是自己不够用功。
三联生活周刊:不是一直在研究古代中国美术史么?
黄苗子:是的,我喜欢搜集一些中国美术史的材料,前年三联书店还给我出版过《艺林一枝》这本书。八大山人我一口气搞下来,几十年了,书快出版了,还是觉得不够成熟。这方面受朋友的好处很多,做学问应该有师友。一些朋友听说我研究八大山人,就给我寄来他们研究的材料。汪世清先生,本来搞科技的,但是对国学研究感兴趣,编写了一本《石涛诗录》。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第一个到,晚上图书馆关门时回家,人家叫他“北京第一读书人”。他去世前,帮我审阅稿子,我不知道他已经病得很重,20多万字,半个月帮我改出来,40张纸,写了100多条意见。
三联生活周刊:那些运动给人生带来怎样的意义?
黄苗子:反右时候,去了北大荒,第一次有个安静的时间思考。臭虫咬得要死,温度太低,南方人受不了,有的人上工一天,睡下就起不来了。我们到底还是所谓的中产阶级,我的一生中,第一次是抗日战争,第二次是文革,使我接触到以前没接触过的农村劳动生活,就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不然这个脑子一天到晚是另外一种想法,没看到整个国家是什么样的,整个社会是怎么样的,只有自己生活的圈子。知识分子总要有他们对时代的感觉和是非观念,每一个选择都是根据良心和知识,不一定能做到完全公开,但从那些“聊天”中,你应该能看出我对人生的一点看法。■ 读书文学艺术聊天文化黄苗子王世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