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和朱文的小说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苌苌)

韩东和朱文是两位在南京成名的作家。韩东是南京人,写作从未离开过土生土长的地方,朱文是福建人,在南京上大学的时候进入当地的文学圈,与韩东等成为好朋友。他俩的中短篇小说在文学圈享有盛名,但销量和畅销书没法比,所以印得很少,流传较广的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那套牛皮纸封面的版本,6年过去了,由楚尘文化策划、世纪文景出版公司重新整理出版了韩东和朱文的一些作品,韩东的中篇集叫《人民币硬过美元》,朱文的短篇集叫《达马的语气》。
《人民币硬过美元》收录了韩东1994~2000年创作的7个中篇。韩东的叙事语言朴素内敛,写的是日常琐碎的生活经验,鼓舞了90年代之后一批立志于写作的人——原来,这样就是写小说了!殊不知,这是一个平静的漩涡,叙述暗藏玄妙,层层递进,像一块做工细腻的波斯地毯,花纹看似随意,却有着缜密的逻辑。他可以将那些琐碎的经验,还原并提升到哲学思考的高度。韩东是写实作家,作者的“人”和小说中的“人”,在人生迷局里影子般统一成整体,作品就具备了某种真实可靠的说服力。在注定有限的个人经验中,他挖掘并书写着无穷的可能性,拾起平淡的材料,放置到矛盾冲突中炙烤,最终带领读者穿过烟雾缭绕的障碍,抵达事物的本原之地。
这不等于说韩东的小说晦涩难读,相反你很容易读进去,不由自主地跟随人物的内心一起焦虑,紧张,忧伤。这几篇小说中人物的语言、行为、思想都浑然一体,他从不借用现成的说法或别人的总结来轻易定义某一个事物,擅长梳理和打磨卑微与混乱的人际关系,人性的温暖、阴暗、爱恨纠缠,都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对人类精神面貌的描述。韩东凭《扎根》获得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时,授奖词中说他“成功地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领域”,只不过他的创新与突破都埋在那平实的叙述下,乍看起来不动声色。
韩东踏实,而朱文比较躁动,韩东自省,朱文则比较自信,韩东的小说细腻,朱文则是泥沙俱下。《达马的语气》这个有点怪的书名,是朱文这本小说集中收录的一个短篇的名字。朱文说他一直想拥有一本叫做《达马的语气》的书,因为小说就是语气。达马是个人名,是这篇小说中始终未现身,却贯穿始终的一个角色。他的气场很强,不仅影响了小说中生活在他周围的人,而且读完小说,那个没心没肺,活蹦乱跳的家伙老在你眼前晃。一些没有被“文学”洗过脑的青年,凭直觉喜爱上朱文的小说,喜欢其中那种奔腾的节奏,或者是感受到了作品背后的朱文,这个狡猾、精明而又力道十足,说着“我一直要求自己写出单纯的小说、纯粹的小说,而不是文学”的小说家。
朱文的小说是以别人的终点作为自己起点。荒诞感是当代生活无处不在,却又很容易被视而不见的一个脉门,朱文在这方面的刻画有独到的天赋,小说充满了垦荒般的热情和惊人的想象力。他把性欲、卑琐等具有强烈反叛色彩的价值观,扭合成了尖锐的劳动工具,在一片荒地上恣意挥舞。朱文小说迷人之处,是他总是在颠覆和破坏生活的常规。从平常的琐碎的生活展开,突然就有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也没匪夷所思到外星人从天而降的地步,但你能感觉这是个总想寻找点刺激的作者,大概走在路上总幻想前方有爆炸、抢劫发生。然而他又很擅长使作品从叙事的绝境中脱围而出,他的结尾不是戛然而止如同欧洲的电影,就是忽现惊奇。同样是描述丢掉幻想之后,人类生存的荒芜景象,收录在这个小说集中的《段丽在古城南京》是他入木三分的观察力和酣畅淋漓的叙事能力的最大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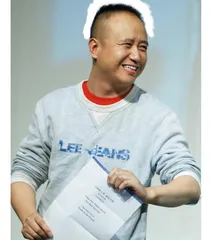
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写作者,朱文的小说成了他那个年代青春文学的代表作,透着强烈的荷尔蒙作用下的青春躁动。在男女关系上,在当代的语境中显得有些过时,缺乏暧昧的温暖,有些男性中心主义。而现在的青春作者好像没什么机会憋出那么大的性压抑了,女孩子在他们小说中是个相与相随的玩伴儿,飘过韩寒和郭敬明的小说的是一种淡淡的似是而非的情感。时代不同了,这是一个不在同一层面上的比较,就像朱文在小说中随处可见的那种幽默感,都有其为整个作品服务的严肃意味。■
韩东:小说的神秘在阅读中
三联生活周刊: 《三人行》是你第一个中篇小说,你在后记中提到,“它提示的各种可能的方向”是什么?
韩东:各种方向,你看完这本《美元硬过人民币》就知道了,这里面每一篇的写法和用心都不一样。我喜欢开玩笑,喜欢语言的精粹,喜欢荒谬以及缠绕,喜欢细节,喜欢分子水平的心理实况,喜欢琢磨事物间关系,喜欢叙述故事时的中国笔法……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世界中,写作与生活、虚构和现实的关系是怎样的?
韩东:写作和生活在我是一体的,或者我想尽量做到一体。虚构与现实是个伪问题,至少不那么牢靠。我的小说有的是以我的经历为模本,有的不是。但经验之类的东西对我的写作非常重要,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小说的神秘在阅读中,而不在于提前预知。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你“修改癖”严重,一个长篇写一年改一年,为什么不能相信自己第一直觉下写的东西?
韩东:我有修改癖,但也不过分。我很相信直觉的,但你能知道什么是直觉,什么是造作呢?加快速度并不是产生直觉的唯一办法,有时候或许更糟。恰当最好,适合自己最好。我一直在寻找恰当和适合,或许还有自信。
三联生活周刊:朱文说,“我很抵触‘职业作家’这个身份”,不是针对这种谋生方式,而是无法认同以一本接一本地写书打发生命。你怎么看自己一直坚持写作这件事?
韩东:朱文到底给我留了一个空子——“不是针对这种谋生方式”。实际上,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写作对我而言一是谋生,二是有一件事打发时光,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打发之中或许有些心得。所以我一再强调写作的这种根本性的虚无,唯有明知虚无还要去接受它,事情才开始变得有点意思了。写作和人生一样,是一场为了失败的战斗,只有如此它才可能是纯洁的。■
朱文:生活的动力就是虚构
三联生活周刊:你到北京的这6年来一个字都没写,生活没有给你带来创作的冲动么?
朱文:冲动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解决,比如拍电影。我很抵触“职业作家”这个身份,不是针对这种谋生方式,而是无法认同以一本接一本地写书打发生命。当写作成为一种习惯,让我难以忍受,所以青春期一过,就没法写了。之前我就不是那种写得很多的作家,我觉得一个好作家,不能写过80万字,后来我发现自己写得已经超过80万字,就不想轻易写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小说发生场景总是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你的世界中,虚构和现实的关系是怎样的?
朱文:写作的世界和我生活的世界就好像一个东西的阴阳两面,加在一起才完整。写作和生活互相投射,互相影响,但不是重复。写作的过程是一种生活,你和你的人物生活在一起;同时你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生活在特定背景中,两种生活之间的张力和关系,一直是我写作的一个严肃命题。写作是干预现实的手段,因为写作,而觉得自己在生活,这感觉在写作的那几年特别鲜明。只要对现实不满足,有白日梦的人都会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我的写作中要么都是“我”,要么都是“小丁”,他们代表我的某种生存。在现实中,我的生活可能是乏味的,但我的体验是深刻的,写作成为一种具有更深刻意义的体验行为。我只接受这样的写作,这样的写作才有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朱文:就是现实感。我过去的写作,和现实有一种很严肃的关系。你写到一个情节,可能明天就会发生,小说有预言性,我的写作是有明显的后果的,所以处理起来很困难,不是因为是虚构的就可以很随便。生活的动力就是虚构,在我是个小说家的时候,我就要求自己做个纯粹的小说家,就是说在生活中,我也信仰虚构。虚构是小说的灵魂,是个发动机。生活也一样,只是我们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待,很多繁荣的东西其实特别虚假。■ 小说韩东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