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天里的贝克特
作者:马戎戎(文 / 马戎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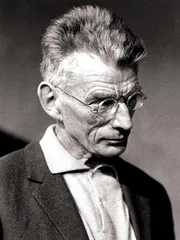
人到得不是很多,7点半开始的戏,7点钟时候,门口才排了几个观众。7点15分时候,人多起来,但也没有一直排到马路对面去,路边也没有票贩子。
安福路288号,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所在地。荒诞派戏剧大师贝克特的《莫洛伊》+《独白》就这样安静地上演。观众们走进一幢居民楼式建筑,坐电梯上去,拐一个弯就是剧场,座位不太多,全是年轻人,1/3是老外。然后一盏灯在呼吸和黑暗中亮了起来,一个身形高大的男演员走上来,穿着睡衣,站得像死人一样笔直僵硬,喃喃地背诵台词。整整20分钟,他不走动,也不坐下,就那么一直喃喃自语。观众都很乖很安静地听着,几乎没有人打瞌睡。
安静、淡漠、守规矩。总之,和北京很不一样。《莫洛伊》+《独白》的演出方是爱尔兰的“门”剧团。去年,他们在北京首都剧场演出《等待戈多》的时候,许多研究了一辈子贝克特的人都吃惊了,在这之前,大家熟悉的《等待戈多》,只是孟京辉和林兆华。2006年,是贝克特诞辰100周年,包括这个剧团的导演沃尔特·阿斯姆斯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执导的《终局》在内,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还请来了台湾当代传奇剧团的京剧版《等待果陀》,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飞那儿剧社的《等到戈多》。四台戏从4月15日上演到4月22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说法是,6天看懂贝克特。
6天能看懂贝克特么?没有人会故意较真这个问题,包括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没有谁会反复提这个说法,这个说法的诞生似乎只是为了在宣传前期给媒体提供方便,带点漫不经心。就像当你向这个戏的策划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市场部经理愉荣军问起,为什么不像北京的戏剧活动一样,宣传做得更大一点,场面铺排得更热闹一点?他会说:“我们已经比国外虚张声势很多了。现在全世界都在纪念贝克特,伦敦也在做,都柏林也在做,但其实都是在小范围里,都很安静。我会让观众因为喜欢,感兴趣才到现场。太商业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变质了。”
贝克特本人应该会喜欢这种方式。70岁之后,他发觉自己已经时日无多,绝望和对世界的厌倦越来越浓烈地抓住了他。1981年,他大发感慨,说为他举办的75岁生日庆典,不仅占用了他的时间,而且也侵犯了他的隐私。他在写给自己的朋友、英国舞台设计师乔斯林·赫伯特的信中称:“我担心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巴黎,人们小题大做,把我的生日庆典搞得像我的百年诞辰一样轰轰烈烈。我要在生日庆典隆重举行的那一天悄然离去。去哪里,我自己也不清楚。也许会去中国的长城吧!我要躲在长城背后,直到大浪淘尽为止。”
 (
《终局》剧照 )
(
《终局》剧照 )
像所有人知道的那样,贝克特天生敏感。他出生在1906年4月13日星期五,这一天是基督受难日。成年后,他一直认为,这个日子对他来说特别合适,因为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和生存的纯然不幸后来一直困扰着他的心灵。贝克特声称他记得他在母亲子宫里的日子,这种记忆带给他一种神经系统的疾患。他很难与人交流,只有酒精刺激才可能激发他的谈兴。他早年崇拜《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自愿担任他的助手。但根据阿尔瓦雷斯的《贝克特》一书中的描述,两人交往时大多数时间相对无言,神情黯然。乔伊斯是贝克特悲观主义世界观的直接来源,在那时写下的论文《论普鲁斯特》中,贝克特已经认为:“个人毫无内容,仅仅是盛放未来的液体从一个容器倾注到盛放过去时间的液体的容器中的过程而已。”他的早期小说《莫洛伊》和《独白》正是这一思想的产物。
这次贝克特百年纪念活动中,《莫洛伊》+《独白》是第一次在中国上演。导演沃尔特·阿斯姆斯年过六旬,是贝克特生前密友,担任他的导演助理达15年之久。戏剧分上下两部,上半部是20分钟的《独白》:“《独白》就像一个人在看着另一个人,在不断地描述他。只有35分钟长,是贝克特最短的戏剧。你听到一个人在高声说话,然后传来婴儿的哭声,然后你听见呼吸声,呼吸声止住,灯光关闭,这就是生命。”在沃尔特看来,《独白》是贝克特对人类个体问题的总结和陈述:“人们总在问生命的意义,每件事都在离去,离去,没有什么留下来,人们对黑暗望眼欲穿,想找到一些‘意义’,最终人们只能说‘我找到的唯一意义是万物留不住,生命归黄土’。”据说,当年贝克特排演《独白》的时候,演员到演出结束的时候,往往会进入一种精神崩溃,伏在地板上大哭。《莫洛伊》改编自贝克特的小说,讲述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寻找母亲和故乡的故事,但却终于陷入无聊和绝望之中。沃尔特对这部作品的阐述是:“我们在社会中接受的教育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但没有人告诉我们意义是什么。”这或许来自贝克特早年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时期的“边缘生活”。年轻时他沉迷在都柏林的小酒馆,尝试过相当长一段时间醒来时不知身边姑娘是谁的生活,甚至被男妓纠缠。事实上,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近40岁。1938年1月,他在巴黎街头被一个男妓捅了一刀,刀锋离心脏只差了那么一丁点儿。这次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
关于《莫洛伊》+《独白》,西方戏剧研究学者、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荣广润的评价是,“这部剧不但有着深刻的哲学内涵,而且语言也写得很美,并且也有戏剧性,在诗化和戏剧性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荣广润认为,这是原汁原味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这种原汁原味。台湾著名戏剧人金士杰和当代传奇剧场的创始人吴兴国带来的是京剧版的《等待果陀》。金士杰和吴兴国显然都不太喜欢在他们之前演出的《莫洛伊》+《独白》,在他们看来一个人站在舞台上念台词,显然不够好看。金士杰是《等待果陀》的艺术指导,他这样描述他心目中的《贝克特》:“我们在做剧场的时候,相声啊、小丑啊、喜剧的东西常常出现。这次我发现,这些因素在贝克特里面是经常具备的,我发现他其实很懂得剧场,我很想把《等待戈多》做成是很好玩的小丑戏。”
《等待果陀》进行的是一种很艰险的尝试。在内地,吴兴国被人所知,是因为他刚刚出演过电视剧《长恨歌》里的李主任,靠了“李主任”的余温,他成为这次戏剧活动中上海传媒追访的对象。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台湾最具实验性的京剧演员,早在1986年,就曾经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为京剧《欲望城国》。从《等待戈多》到《等待果陀》,对于吴兴国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京剧存在的基础和核心价值观是忠孝节义,而贝克特的戏剧讲的是存在的荒诞和虚无。”此外,正如荣广润对贝克特戏剧特点的分析,“贝克特的戏是难排的,难排在它是反戏剧的,和传统的方式对着做,要的是内在的逻辑性而不是表面的逻辑性”。但京剧这么多年,一直都在讲故事。最终呈现在舞台上的《等待果陀》其实并没有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但吴兴国和金士杰把它做得很好看:大量的唱念做打、亦中亦西的服装和脸谱营造出的视觉和听觉的冲击掩盖了戏剧核心的生硬。《等待果陀》的笑声非常多,在几场演出里,这是气氛最轻松的一次。
《等待果陀》其实并不是中国戏剧人第一次尝试将京剧元素引入贝克特。某种意义上,中国戏剧人第一次排演贝克特的戏就这么做了。荣广润认为,中国第一次排演贝克特的戏剧是在1987年,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让进修班的同学导演和演出了《等待戈多》。回忆起那次排演,曾经在国外看过这出戏的荣广润觉得,那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贝克特。而在同时期,台湾戏剧人对贝克特已经相当熟悉了。金士杰说,他从20岁起就是贝克特的“小粉丝”。1986年,赖声川在台湾搞过一次声势浩大的“贝克特之夜”:“一个大院弄里,做一个特别大的贝克特之夜,院子里是流水席,有七八站,每一站都是不同的贝克特的戏。不同的导游领着人去看。”
事实上,内地对贝克特作品的翻译并不晚,早在1979年,已故英美文学专家施咸荣先生就翻译了《等待戈多》和《美好的日子》。而《等待戈多》真正被内地的普罗大众所熟知,已经是1991年孟京辉以此开始自己先锋导演生涯的《等待戈多》,而1998年4月下旬在北京首都剧场上演的由著名导演林兆华排演的《等待戈多》,是国内演出场次最多的版本。对于中间十几年的“时间差”,荣广润的看法是:“80年代,中国根本没有相应的环境。《等待戈多》在西方的流行,是因为二战以后,整个西方社会的精神价值体系都崩溃了。所以在80年代,不是因为不允许排,而是因为排了,观众也理解不了。1987年以后,中国进入了现代化的进程,关于生存的意义,价值观的崩溃等等问题也同样在中国社会显现了出来,观众有了理解的基础。”
金士杰看过孟京辉的《等待戈多》,看过林兆华的《等待戈多》。在他看来,贝克特的戏,最大的魅力就是:“有着非常大的解释空间。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他觉得,贝克特之所以是大师,就是因为无论做戏的人怎样“戏耍”,最终发现都无法彻底逃离和颠覆他。在排戏的过程中,他总是觉得:“我们在玩耍中有时候要跑远了,但最后发现根本跑不远,在一个可怕的悬崖边上。”因为贝克特是如此洞见人生:“人生就像《等待戈多》里的台词:‘你也高兴,我也高兴,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既然高兴,那么干什么呢?我们拥抱吧,哈哈。’——我们拥抱别人,但拥抱之后又会发现对方有脚臭或者有口臭。马上需要了,又马上觉得很麻烦。”或许,这种能无限解释的魔力正来自于贝克特本人的矛盾性。晚年的贝克特是极其平易和幽默的人。他甚至对自己的前半生忏悔:“痛苦、孤独、冷漠和轻蔑都是我个人优越感的表现……直到这种生活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否定生活的生活方式,演变成为一些无以复加的可怕的生理症状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真的有病。简而言之,如果我的心灵中没有闪现过死亡的恐惧的话,那么时至今日,我一定还沉醉在灯红酒绿之中,一定还是目中无人,一定还是终日无所事事,因为我觉得自己太优秀了,优秀得别无选择了。”他一直在笔下毫不犹豫地、歇斯底里地戳穿命运的骗局,却在生活中主动和命运达成彻底的谅解。他的传记作家阿尔瓦雷斯认为这种和解来自于彻底的失望,就如在晚期作品《终局》中他对人生的形象描述:住在垃圾桶里的残疾人,却盲目地想掌握命运。
所以,最轻松的接近贝克特的方法,也许应该像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生们排演的《等到戈多》:等啊等啊,戈多真的来了,可是这下,很多人都失业了。 贝克特艺术戏剧爱情电影智利电影等待戈多吴兴国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