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拷贝,大牌生气了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李孟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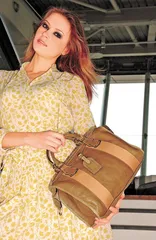
血拼智慧和五周生产计划
买一本最新出版的时尚杂志,《魅力》、《玛丽嘉儿》、《哈泼斯芭莎》什么的,翻到时装版,看到了今年春夏最新款的服装、鞋子、手袋——都是高端品牌。买不起?好,撕下这几页,带着它们奔向Zara、H&M、Topshop、Mango或者Tesco,不信找不到Chole风格的卡其布上装,夏奈尔风格的花格呢外套,Mulberry风格的手袋……它们价格低得多,甚至连零头都不到。没有顶级的收入,不能拥有顶级奢侈品,仍然能得到顶级感觉,这是目前流行、被人称道的血拼智慧。怕动脑子的人,连这点智慧都不必有,《玛丽嘉儿》有个“炫耀vs偷学”栏目,编辑在Celine连衣裙的旁边,摆出了Zara的拷贝版,只管找最近的一家Zara连锁店去买就行了,一点脑力体力都不费——类似的版面,几乎每本时尚类杂志都有。
当下最有“被拷贝缘”的是法国设计师罗兰·毛利特(Roland Mouret)的Galaxy裙装。这款20世纪50年代风格的长裙标价4位数,有非常华丽的腰带。腰带使胃部平坦,同时让胸脯高耸,塑造出完美的沙漏型身材。它有黑和深蓝两个系列,已经被诸多名人如西恩娜·米勒、卡梅隆·迪亚兹、黛米·摩尔、维多利亚·贝克汉姆穿过亮相,凯拉·奈特利在《傲慢与偏见》的首映式上穿的也是它。普通人只要掏出35英镑,就能穿上和这件2005/2006秋冬最美丽服装几乎一模一样的裙子。
今天的消费者前所未有地产生了对时尚消费品的贪欲,而且具有丰富的品牌知识,人人都关心大街上流行什么,什么穿戴最时髦,时尚分析专家安尼卡·索伦森称他们为“时尚知识分子”:“20年前,人们看的是月刊,报纸上不会刊登时尚文章,更没有时尚版面。也不会有时装秀一类的电视节目,当然更不存在网络和所谓的名人文化。今天,针对女性读者的时尚类杂志除了月刊,更有周刊,密集、疾速地散播时尚信息。”媒体上“必不可少的××件本月单品”,“本周热门推荐”等栏目极富煽动性,煽起了读者的占有欲和购买欲。然而90%的人是不可能负担奢侈品的。于是,大众品牌的拷贝产品被催生出来,又迎合了这种贪欲。
五周生产计划,是大众品牌进行拷贝时通行的规则。四大时装周上的某个设计,某影星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穿的礼服,一旦被认定有市场前途,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出拷贝版,穿在全球连锁店的木头模特儿身上。于是,这边模特儿刚走下天桥,那边仿制服装就上了货架;时装周才结束,新衣服就开始“低价”倾销。一些热门的拷贝服饰,哪怕售价才10英镑,居然还有了顾客等候名单,而等候名单是顶尖奢侈品牌限量版产品的专属。

西班牙大众服装品牌Zara最先证明五个星期是最佳的期限。Zara的创始人安曼西奥·奥特加就是“五星期”的受益者。当年,奥特加还是家乡制衣厂的工人,看到商店里漂亮的丝绸睡衣想送给未婚妻,无奈阮囊羞涩,只得望橱窗兴叹。他灵机一动,改动了一些细节,赶制出一件睡衣送给未婚妻,深得未婚妻欢心。他们大受启发,建立了一家服装公司,毫不讳言要将T台风尚带给大众。很快他们打进马德里,占领欧洲市场,发展成全球第二大服装公司。奥特加也上了《福布斯》富人榜。
暂时无法打败拷贝

虽说作品被抄袭、拷贝是一位设计师得到的最大恭维,但所谓血拼智慧还是让很多大牌和设计师恨得牙根痒痒,英国著名设计师马修·威廉姆斯就拍案而起,起诉某连锁超市剽窃他的数个设计。法国最高贵的时装品牌之一Chole告Tesco剽窃它一件绿色雪纺小礼服的设计,现正和Kookai在法庭上纠缠。2004年下半年来,英国著名的皮具品牌Mulberry一鼓作气和17家服饰连锁店交手,其中16家为了避免高昂的诉讼费用,选择庭外和解,予以赔偿,并收回、销毁未售出的仿制品。
设计师们要捍卫高端时尚消费品的“排他性”和“精英身份”。订制一个LV的旅行箱,商家会在箱子上为客户做烫金的姓名缩写;如果人人都提一个棕色底子褐色花纹的箱子,那个姓氏缩写还有什么意义?和新秀丽旅行包的标识又怎么区分?大众品牌大量拷贝顶尖品牌的产品,拉低了后者尊贵的身份。
诉讼行为后面,隐藏着设计师内心的不安全。迪奥老板的观点“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打败拷贝产品”,是业内老板们的共识。设计师不过是商业帝国的一个棋子,还面临一季推出一个系列新装的巨大压力,“不断创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相当困难。设计师更害怕面对消费者的质疑:奢侈品牌斥资数百万投放广告,宣传的商品在街头商店都能买到类似的,价钱却要低得多。所谓的奢侈品,不过是一种时尚阴谋,诱惑消费者花高价去买它们,而实际上它们根本不值那个价。
经济利益更是必须保护的。目前设计师和高端时尚品牌最关注的是皮具系列被拷贝,Chole起诉Kookai,就是因为后者抄袭了它一款蛇皮质地带银饰的手袋。这个手袋售价1086英镑,Kookai的拷贝包才35英镑。手袋不同于服装,一款好的手袋往往能成为经典,比如爱马仕的Kelly包、Birkin包,卖上几十年都不会被淘汰,是很好的时尚投资品。在奢侈品消费滑坡的欧美,手袋等配饰支撑了众多奢侈品牌利润的大半壁江山。
全球奢侈品行业已经开始联手对抗拷贝行为,捍卫自己的时装、手袋、鞋子。这方面欧洲做得比较好。1994年,圣罗兰在欧洲起诉拉尔夫·劳伦抄袭其一款燕尾服的设计,胜诉,获得30万美元的赔偿。2002年以后,欧盟采取更严厉的举措保护成员国设计师的作品。四大时装中心之一的美国,给予奢侈品牌的法律保护则少得多。
设计师不满现有法律没有给予时尚产品和书籍、音像制品等其他艺术产品相同的法律保护。现行的专利法保护科技发明,著作权法保护原创作品的作者如作家、作曲家的权益,保护年限为其有生之年再加死后70年。服装、手袋等至今被认定是实用产品,而不是艺术品或科技创造,因此时装设计师和其设计既不受版权法也不受专利法保护。复杂的是,时尚产品涉及到的商标、标识,如夏奈尔的双C,Tommy Hilfiger的小旗子,又受法律保护。最近,美国国会立法给予船体设计10年的保护期,让时装设计业看到了希望。戴安娜·冯·弗斯滕博格、Narciso Rodriguez等美国顶尖设计师分别前往华盛顿游说,呼吁立法保护设计师的知识产权。英国、法国、意大利的设计师做出声援,表示这也关系到他们在美国的利益。
一分钱一分货
零售巨头们对此嗤之以鼻。洛杉矶一家专门生产廉价时髦服装的公司A.B.S的老板说,大牌设计师的设计不过都是炒冷饭,在他看来,细条纹就是细条纹,鸡心领也不过是鸡心领,谈不上什么新创意。A.B.S在2003年奥斯卡典礼结束后90天拷贝出了妮可·基德曼穿的夏奈尔礼服。该老板说,我们对经典进行了便宜化的诠释。
Tesco强词反驳Chole时称:“说我们有一帮人坐在天桥下,认准一个设计师然后就扒人家的设计,此乃无稽之谈。我们自己有一支天才的设计队伍,他们会分析时尚潮流和我们顾客的需求。Tesco的设计师除了关心T台走势,更注重从寻常街头的潮流,以及电影、音乐等更宽泛的艺术领域中获取灵感。”
英国专栏作家马克·汤盖特写了一本书《时尚品牌:从阿玛尼到Zara,带烙印的风尚》。书中,他提到他在Zara总部看到设计师的电脑旁堆满了时尚类杂志,但Zara断然否认他们拷贝。Zara的观点是:“我们没有创造潮流,但我们通过杂志、时装秀、电影、街头紧跟潮流。我们更倚赖潮流预测公司和潮流侦探。”常常遭遇抄袭指控的H&M也持相同观点。《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时尚编辑克劳蒂亚·克洛夫为Topshop等廉价服装品牌辩护说,大众品牌制造出了自己风格的潮流。比如2005年风行了一个夏天的毛线钩针披肩,并非因为凯特·莫斯穿了它,或者来自T台,而是大众品牌连锁店的功劳。
马克·汤盖特认为,除了时尚工业的模式发生巨大变化,技术手段为廉价品牌抄袭、借鉴、拷贝大牌设计师的创意提供了便利。网络和数码相机的出现,时装周上的新装两三个小时内就上网传遍全世界。图片库里,有各大品牌全套的新装照片。各类时尚网站,不仅提供图片,还有服装的细节、世界各地的行业新闻、报道、潮流分析。最著名的是全球时尚联合网络,它已被奉为时尚界的电子圣经,Zara、GAP、H&M都是它的订户。这种网络服务远比传统的情报服务有效得多。
不过,还是有人认为高端时尚产品值4位数以上的价码。买拷贝版的确只需花极少的钱,一分钱一分货也绝对不是高端品牌为自己找的借口。比如Galaxy礼服,除了华贵的面料、熨帖的裁剪、欧洲本土工人精细的手工制作、刺绣(绝非出自第三世界国家血汗工厂的流水线),还有一个独特的网眼内衣。内衣采用高科技材料制成,对身体起着塑形作用。拷贝版的裙子当然没有这内衣,所以除非你学习玛丽莲·梦露敢于去掉两根肋骨,否则穿不出那沙漏的效果。■
设计师罗兰·毛利特(左)和思嘉丽·琼森(右)
凯拉·奈特利穿着Galaxy礼服亮相《傲慢与偏见》首映式
妮可·基德曼在2003年奥斯卡典礼上穿的夏奈尔礼服被迅速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