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津有味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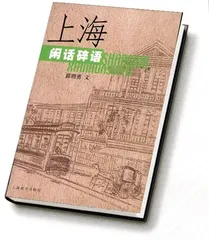
有关“上海闲话”,薛理勇写过好几本书。《上海的闲话碎语》(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是最新的一本。
薛理勇解释上海话,经常别出心裁,存心和一般的讲法过不去,未必十分有理,不妨聊备一格。
“大闸蟹”是上海的名物,如果评选中华第一美食,不少上海人会投“大闸蟹”一票。很多文章说,“大闸蟹”得名是拦闸捉蟹而来,薛理勇不以为然。他说“大闸蟹”应该沸水煮熟而食,隔水而蒸并非“大闸蟹”的正宗做法。吴方言中“煮”字为“”,发音同“闸”。“大闸蟹”其实就是“大蟹”。薛理勇还找到清代记录吴地风俗的《清嘉录》支援他的说法:“湖蟹……有‘九雌十雄’之目,谓九月团脐佳,十月尖脐佳也。汤而食,故曰‘蟹’”。这番考证很有道理。
但他的另外一些说法显得很没道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方言中流行的一个词叫“老克拉”,通常是指那些原来有点家底,有生活情调,讲究品位的男人。“老克拉”又称“老狄克”,没有人知道“老狄克”的出典,薛理勇自说自话地做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解释。他说:“文化圈中的一些人知道张春桥在30年代以‘狄克’的笔名攻击过鲁迅先生,于是当时上海出现这样的局面,追随张春桥的人千方百计隐瞒历史以保张春桥,而反对者希望通过张春桥即‘狄克’轰其下台,而大多数市民只知道中央或地方隐藏着一个老奸巨猾、名叫‘狄克’的人。于是‘老狄克’取代‘老克拉’而成为流行语。”
这真叫无稽之谈。“老狄克”是白相人,张春桥再怎么“老奸巨猾”,和白相人还是沾不了边。上世纪70年代,他想“找个伴”都难,哪里有一点“老狄克”的腔调。“大多数市民”都知道“狄克”,证据在哪里啊?上海“老狄克”,对政治一向避之唯恐不及,怎么可能会想出这样一条拐过一百多道弯的曲线来声讨“四人帮”。作者太看得起上海人,太看得起“老狄克”。

说薛理勇是上海话专家,不算过誉之词。不过专家也会错。他把俗语中的chatou(出租车)写成“叉头”就是一例。Chatou应该写作“差头”。老上海出租车被称为“出差汽车”,金雄白的回忆录里可以查到。
前几年上海出过陈存仁的两本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记录的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事与人,一时成为饭桌上的谈资。以后也有学者比对史料,发现陈存仁写书光顾自己高兴,怎么好玩怎么来,常常拿道听途说流言蜚语当真事讲。虽然娓娓道来,未必凿凿有据,只求别人能读得津津有味。

《津津有味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是陈存仁当年在报上开设的专栏名称,现在也已在大陆出书。这套书以食疗食补为题,分《素食卷》、《荤食卷》和《食疗卷》,照样写得妙趣横生,除了中医的食补的知识外,还有不少作者的见闻和八卦。
他也提到吃螃蟹讲究“九雌十雄”,因为“九月中雌蟹黄满脐凸,到十月间雄蟹内满盛脂膏”。但蟹黄蟹膏究竟是什么,我一直食而不知其然。读了陈先生的书,我才知道“雄蟹的蟹膏即精子,雌蟹的蟹黄即卵块”,难怪这么好吃。下次有机会陪老外去吃蟹,我一定等吃到极乐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们吃得最过瘾的是公蟹块状的精液,还有母蟹卵子的尸体。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下咽。陈存仁说,吃蟹还真吃死过名人。张大千的老师,清朝遗老李瑞清那时候在上海号称“李百蟹”,秋风起时日啖湖蟹一百只,到了晚年患上严重的胃寒症,“饮茶非沸水不饮,一切食品均需滚热,如果稍进半温半凉的汤水,立刻会胃痛如绞”,终告不治。
我曾听朋友说,燕窝的食补效用十分可疑。在《津津有味谭》里也能看出些许疑点。陈存仁说,过去的本草书一向不认为燕窝是补品,记载历来从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因为燕窝的功效并不是医疗上所必需的,故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禁止进口燕窝”。
说到燕窝的润咳补肺之功,陈存仁总是语带保留。他引宝钗对黛玉说的一段话:“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吊子熬出粥来,要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陈批:“话虽亲切,可是每日一两即使在今日又有几人负担得起呢。”这是老上海说NO的阴阳怪气。■ 张春桥津津有味陈存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