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普马克:我们生活在“失忆的年代”
作者:孙若茜 谢尔·埃斯普马克
谢尔·埃斯普马克
“昨天这里还是别的房子,/每走一步这个城市都在改变。/我能不能回到家/而这把钥匙还对得上门锁吗?”这是谢尔·埃斯普马克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首诗中的节选,他在描写“失忆”——从那时候起,他的文学创作中已经开始出现了“失忆”的主题。
1985年,埃斯普马克在布拉格之行后写下的《布拉格四重奏》中这样描述道:“墙壁被刮过,粗糙的牛皮纸/抵抗它新的文字。”以展现一种文化在消失的声音以及感官几乎无法抓住的毁灭,就像米兰·昆德拉曾写下的,俄罗斯占领者正在抹除掉他的祖国的历史。在他看来,这正是“失忆”在“冷战”时期留下的一种更危险的形态。
“上世纪80年代,瑞典对历史的麻木不仁也在增长,特别是在主管教育的政府部门。我曾经在瑞典学院做过一个让很多人不愉快的公开演讲,对我们历史记忆的丧失提出了警告。”埃斯普马克回忆,与此同时,他开始了题为“失忆的年代”的系列小说的创作。
创作从1987年起持续至1997年,《失忆的年代》共收录了7部长篇小说,包括《失忆》、《误解》、《蔑视》、《忠诚》、《仇恨》、《复仇》和《欢乐》。整个系列由翻译家万之执笔译作中文,经历两年半左右的时间。第一部《失忆》在2012年出版,其余几本相继发行,目前7部小说都已面世,出版方世纪文睿还为此系列发行了合订精装本。
这7部小说都以“失忆”作为主线,由7个不同身份的主人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切入,每位主人公都是以其独白的方式进行着讲述。他们分别是负责教育的官僚,报刊主编,为了两个儿子牺牲了一切的母亲,对工人运动进行着自我检讨的老工人,描述其政治家生存状况的被谋杀的首相,年轻的金融寡头以及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备受打击的妇女。他们展示着不同的社会截面,因此每一部小说又都可以独立成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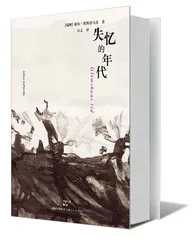 谢尔·埃斯普马克的著作《失忆的年代》
谢尔·埃斯普马克的著作《失忆的年代》
小说在细密地刻画着个人肖像,而所刻画的人恰在概括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埃斯普马克有着近似、但不同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野心。他没有企图复制社会现实,而称自己只是一种戏仿。他希望在写作中所达到的目标是给社会做一次X光透视,展示现代人内心生活的图片,其焦虑不安、热烈欲望以及茫然失措。在透视的过程中,他更喜欢用一种漫画式的、夸张且讽刺的手法。
比如《蔑视》中的老女人躺在医院病床上,看到自己周围堆积着垃圾:空纸箱、橘子皮、陈旧而酸臭的尿布、一个废弃的冰箱和被刺破了的床垫,垃圾的上方围绕着一群苍蝇。埃斯普马克说,这便是他所做的一个有关内心感受的夸张描写,它一反医院现实中的常态,垃圾是这个女人一生所感受的蔑视的具体化。再比如《仇恨》中被谋杀的首相,在现实中他被枪杀,而在小说中,他是被刀捅死的,腹背各有多处刀伤。这是埃斯普马克将仇恨物化的表现,用以说明仇恨之多以及来自不同的方向。
 翻译家万之
翻译家万之
一个政治家“在发表苍白无力的竞选演说时就消失了”,“当我的嘴唇上还有我爱人的嘴唇留下的温暖时,我就已经忘记了她”。写到失忆,埃斯普马克这样描述。他的笔下,记忆只有四个小时的长度,甚至更短。这意味着你会忘了昨天在哪里工作,没有人记得昨晚睡在哪里,当你按动门铃,会自然而然地生出疑问:开门的这个女人,会是我的太太吗?站在她身后的孩子,会是我的孩子吗?这个长篇系列里始终贯穿着找不到亲人或情人的苦恼。
他所讲述的“失忆”不是生理或心理上的疾病,而是与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把自己的国家叫作“失忆的合众国”,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把我们的时代称为“遗忘的年代”中所提到的“失忆”、“遗忘”是为同样的表达。
“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记忆,如果没有了我们行事的上下关联,孤立的事情就不可能去固定下来。那么每个解释都会变得随意武断,方向也不可确定。”埃斯普马克认为,失忆是很适合政治权力的一种理想状态,对和权力纠结的经济活动则同样。“因为有了失忆,就没有什么昨天的法律和承诺还能限制今天的权力活动的空间。你也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只要你成功地逃过舆论风暴的四个小时,你就得救了。”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说:“现代人越来越生活在当下,而过去就好像是一个黑洞,一切都可以在里面消失:英雄、罪犯、明星和无名的群众。甚至活着的人也在里面消失了,不像在过去的时代,活着的人是在自己生命结束后才消失。”埃斯普马克喜欢借用这段话描述他的主题。他同时想要表达的是,虽然这几部小说都是以瑞典人的眼光去看问题,但所呈现的图像在全世界都有效——“否则,它也没有被译成中文出版的必要了。”
埃斯普马克认为,失忆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它让人产生了一种自我查禁的功能:我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自己就会把它擦掉;不应该感觉的东西会悄悄地从我们的意识里溜走;我们参与其中的正式公开的谈话会把正确的词汇放到我们的嘴里,把正确的思想放到我们的头脑里,帮助我们忘记那些我们不应该记住的东西。
“我的雄心是把本来可以写成400页的小说压缩在100页之内。凡是没有绝对必要的段落和词都删除。”因此,这7部小说的篇幅都很短,每部都只有六七万字,但它们并不是轻松易读的。埃斯普马克说,要达到这样严格的简略,就要求精准和知性方面的含蓄。人物和事件的描写都需要精确和可靠,全都能清晰展露在读者眼前。所有这些特色,我们通常都习惯于在诗歌的语言中看到,而在他看来,好的小说、散文语言是诗歌的孪生兄弟。这也使得我们在这几部小说中很难看到清晰的故事主线、跌宕的情节,一切都呈现碎片化。埃斯普马克对此的解释是:“生活在失忆的年代本身就很难保持完整,只有电影里才有完整的情节和完整的结局。”
小说中贯穿始终的叙述模式可以追溯到但丁《神曲》中穿越地狱的旅行。“在我这个系列里,人们落入的是人类的地下室层。那些陷在这个地狱色彩的当代的人物确实都到了他们人生处境的最低点,还都带着他们被极端具体化了的烦恼、热望和内心的破碎。”但在《失忆的年代》中,埃斯普马克希望将读者设置为其中的旅行者,即真正的主角。每个主人公的独白都需要对手,他说:“只有读者也在场,这种独白才有可能进行下去,是读者的回应使得独白成了对话。这7部小说里真正的主人公其实是你。”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失忆的年代》这个系列之外,我还读过你的《巴托克:独自对抗第三帝国》,有报道称那是你自认最好的一部小说,是这样吗?
埃斯普马克:我的下一本书写的是有关作曲家霍夫曼的故事,特朗斯特罗姆说那是我最好的小说,所以,我最好的小说是下一本。
三联生活周刊:霍夫曼、巴托克都是作曲家,为什么你会选择让两本小说的主人公都是这一身份?
埃斯普马克:的确,这两本书都是在写知识分子面对强权的抗争,身份使得他们对社会问题更加关注。比如霍夫曼,他不仅是一个艺术家,还是一个法官,因此对无视法律的事更加注意。霍夫曼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和我们相近的年代,相近的意义在于那时候的人也都非常害怕恐怖主义。那时最活跃的是无政府主义,他们制造革命、炸弹,因此国王和所谓官僚主义都认为要加强强权、控制,甚至法律都已不再重要。在小说中,国王要求霍夫曼把所有涉嫌恐怖主义的人都关起来,但霍夫曼认为做这样的事情需要证据,应该坚持法律,因而拒绝了体制的要求,他本人则因此受到了酷刑的折磨——甚至用烧红的烙铁去烫他的背。
整个故事就是霍夫曼的辩护词,是在口述一个文件。就像《失忆》的形式,一个人一直在说,而在一旁记录的打字员其实就是作者,我们超越了时代会面。
三联生活周刊:《失忆的年代》在剖露人性的弱点,但是巴托克和霍夫曼都是独立对抗的形象,在讲述你曾经提到过的特别赞赏的“公民的勇气”,写作方向上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转变?
埃斯普马克:你说的对,《失忆的年代》里的人物都有弱点,写的都是强权的牺牲者。可以这么解释,现在写要勇于站起来做点儿什么的人,这就好像先做诊断,然后就需要开出药方。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作家有责任去解决问题、疗救社会?
埃斯普马克:作家的主要任务还是诊断,至于做什么,还是需要读者。能提出解决方案的作家往往应该去写报刊的文章而不是写小说。
三联生活周刊:那些写了很多解决社会问题的文章的作家是否能得诺贝尔奖?
埃斯普马克:诺贝尔奖应该给作家而不是宣传家。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他写的文章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还是可以得的吧,比如丘吉尔?
埃斯普马克:让我们忘掉丘吉尔吧,给他发奖是一个错误。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严格的规定说评委会成员不能获“诺奖”?
埃斯普马克:现在有严格规定,我们评委自己不能得奖。不光是不能得诺贝尔文学奖,还包括瑞典学院每年颁发的其他奖。我们每年颁发的大小奖项有60多个,我都不能得。不仅如此,我的太太莫妮卡,也至少因此错过了两个本应该属于她的奖项。
三联生活周刊:“诺奖”评委会主席的身份和你的作家身份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埃斯普马克:我可以用精神分裂症形容,我作为评委给人评奖和自己写作简直是两个人,但他们和平共存。
三联生活周刊:怎么解读你作品中存在的自传性质?
埃斯普马克:在创作一个文学作品的时候当然会有个人经历在里面,但是文学作品有自己的逻辑,不能把这个人不可能说的话放进这个人嘴里。在描写历史故事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转化,不能写不可能的事情。有一个瑞典女作家曾以一个芬兰籍的瑞典作家为主人公,在小说里讲述了一个凭空想象出的爱情故事,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可以的。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是小说为什么不可以?
埃斯普马克:写历史人物的小说还是要忠实的,小说的人物不能扭曲得不像样。人物被创造出来,就不能再滥用作家的权利,你要对他忠实,这就好像我们翻译一首诗歌,瑞典语中“翻译”那个词其实是“解释”,可以解释,但不能强暴。你所创造出的人物就是你的解释,但是你不能去强暴他。
我有时候也借人物的声音表达。在小说中有两个声音,既要让人物发声,也要借他的口说自己的话,两个声音都要存在。要有很客观的方式,作家会时不时地在作品里现身,尤其是要表达自己的态度的时候,而这种态度表现在作家怎么去选择事件、选择人物,是在作品的结构里表现出来。 作家阅读书与人埃斯普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