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威登
作者:黑麦 位于法国上塞纳省的路易威登工作室(摄于1989 年)
位于法国上塞纳省的路易威登工作室(摄于1989 年)
在进入圣托诺雷木箱行当三个月后,路易·威登凭借机敏和勤奋,成为优秀的“行李打包工”——这是19世纪冒出的时髦新名词之一,专指那些为大户人家运送物品特意装箱打包的人,他们的职责是用最少的箱子装进最多的物品,前提是不能有丝毫损坏。出身于木匠之家的路易·威登熟悉各种木材,也知道如何挤压空间,他的精打细算颇获好评。1840年12月15日,拿破仑的灵柩被运回巴黎的那一天,他被木箱行晋升为高级技师,负责制造旅行箱。
“在铁路出现前,法国人似乎从未对旅行有过奢望;当铁路成为最主要的出行交通工具时,路易威登的旅行箱也出现了,旅行箱成为一种让人走出去的动力。”这是皮埃尔·达利巴尔在《记忆中的行李箱》中的一段描述,法国的首条铁路在1837年贯通,“西留斯号”蒸汽机船横渡大西洋,欧洲人于是彻底感受到了机械化旅行时代的来临。
当欧仁妮(Eugenie de Montijo)皇后成为路易·威登的客户时,他似乎也意识到了旅行时代的到来。这位主顾是个唯美主义者,每到狩猎季都会迁至巴黎北部的贡比涅,他们搭乘火车前往目的地,用几个车厢放置装满皇后衣物的箱子。路易·威登发现,当时流行的圆顶箱子造成了很多不便,软式旅行包与狭长的火车空间,很容易使箱内衣物变得褶皱,为了保持衣物的平展,路易·威登制出白杨木平顶衣箱,把皇后精美的服装妥帖地捆绑在旅行箱中,用平整的服饰保持她的端庄和影响力。
路易·威登随即做了一个尝试,他用耐用又防水的帆布物料将其中一个旅行箱覆盖,推出一款方便运输的平盖白杨木行李箱,这个行李箱表面覆以优质灰色防水帆布,角位以金属包边,装上手挽及托架,表面的榉木条以铆钉钉牢,内部安置了一列隔底匣及间隔方便摆放各式衣物。史蒂芬妮·柏威琪妮在《路易威登传奇》一书中评价,它是今天我们所用的旅行箱雏形,很长一段时间,这款设计也成为人们心目中旅行箱的样子。平顶皮箱的发明像是一场变革,用轻便的帆布制成的箱子很快成为巴黎上流社会出行的必需品。
意大利导演卢契诺·维斯康提(Luchino Visconti)有一款专为长途旅行而设计的分格硬箱,它可以有效保护箱内物品,箱内设有三个隔层,包含一个帽格以及专门放置内衣和配饰的分格。这位导演常在旅行时携带着这个宛如“屉柜”的箱子,并夸耀道“有行李箱的地方就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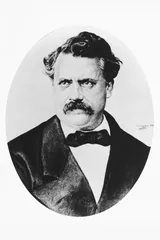 路易·威登
路易·威登
“探险家德·布拉柴、作家海明威、时装设计师珍妮·浪凡等,都曾与路易威登旅行皮箱形影不离。”《100个传奇箱包》一书的作者皮埃尔·雷昂福特(Pierre Leonforte)认为,在“奢侈品”出现前,旅行箱仅为人们的日常工具,当需求量逐渐升高时,“奢侈品”才开始浮现出其标准。“有些旅行箱被束之高阁,有些被陈列在博物馆,有些还在旅途中。”拆解任何一款路易威登的旅行箱都会获得一份完美的技术清单,它就像制箱工匠的圣经。
似乎每个行李箱,都藏着一段无法复制的故事。1920年,指挥家列奥波尔德·斯托科夫斯基曾希望路易威登为他定制一款内部安有分格的书桌旅行箱。在默片盛行的时代,对自己的仪表格外讲究的演员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也向路易威登定制过旅行皮箱,他曾经要求特别设计的皮质固定系带上,放置着一系列梳妆用的瓶子与刷子,用以保证梳妆的“随时性”。路易威登为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定制过一个可随身携带的梳妆用品箱,几十年后,好莱坞女演员莎朗·斯通也定制过一款类似箱子,它像一个迷你化妆台,内置12个珠宝柜以及种类繁多的间隔和旅行日志口袋。在莫里斯·勒布朗(Maurice Leblanc)1911年出版的小说里,著名珠宝商为了迷惑大盗,而向路易威登定制了一款能容纳两个人的巨大箱子。这个箱子也成为法国小说家大卫·芬基诺斯(David Foenkinos)的短篇故事《撬不开》的创作灵感。2013年,路易·威登出版了一本名为《行李箱》的法语短篇小说集,也将芬基诺斯的逃脱艺术家故事收入其中。

路易威登旅行箱的黄金岁月是1893至1936年,1893年,路易的儿子乔治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展示了路易威登的产品。身处“加速世纪”核心地带的美国人很快被这种结实、轻便的防水帆布箱所吸引。19世纪末,这款以凡尔赛小提亚农宫作为主色调的旅行箱被看作“法国入侵”的象征之一。乔治用简写的“L”及“V”配合花朵图案,设计出交织字母,并在帆布上印制了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商标印花图案。
从芝加哥世博会开始,“路易威登”仿佛成为象征高档皮具和箱包的代名词。设计师马克·雅可布(Marc Jacobs)在电影《穿越大吉岭》中,为演员复刻了一款当年的旅行箱,并在箱子上印上各式动物和树木的图案。雅可布说:“它是法国最古老的奢侈品之一,它的设计记录了旅行的黄金时代。” 路易威登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