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牛奔腾中的《22条军规》
作者:邢海洋 ( 邢海洋 )
( 邢海洋 )
写过很多封面,再也没有一个比《22条军规》写得容易的了。之所以容易,是因为我做过一段证券分析师,技术分析是老本行。与谢衡、谢九“二谢”合写这个封面,分配我的也正好是技术分析的部分。那个封面,我写的导读,开篇就是“射击之星”,一个专业的K线形态名词,用这个充满意向的词汇开门见山,正好勾起读者的好奇心。
其实即使再拗口些,读者也会对这个题目感兴趣。那是个疯牛奔腾的时代,牛市已经开始奔跑,从千点跃上两千点,到了我们决定写这个封面的时候正跨越三千点。社会上到处都是股市的赚钱神话,有的同事轻描淡写,说他爱人早就满仓买入,引来大家的一片羡慕,办公室里本不关心股票的同事们都开始向我们打听股票的事儿。可同事们多中文或新闻出身,先天对钱的事情不敏感。在讨论会上,主编还以编辑部同事们的“钱商”打比方,说既然我们已经写过宏观经济、写过社会变迁对股票的影响,又没有预测股票能涨到哪儿的本事,何不普及炒股票的知识?当时我还想,知识没有时效性,是固定了的内容,书本上都有,我们的读者会否愿从杂志上获得?选题会上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写知识,但应该通俗易懂并结合当时的股市动态。
也正是那种奇怪的牛市环境,赋予了这期封面价值。本来,中国股市在这轮牛市前是很少受到白领们,或有正当职业的人关心的。在净土胡同工作的时候,马路对面新开了一个证券营业部,营业部就是胡同口的几间大平房,外立面是巧克力色的墙砖,两个大玻璃窗能看到里面摩肩接踵的人群,门口是个自行车场。我没事常去那里看股票行情,看自行车是多了还是少了。股市火爆的时候,交易大厅外的门厅里烟雾缭绕,老股民们要么穿着邋遢,要么面有菜色,除了证券部的工作人员,很少有职业装束、面色红润的年轻人。当然,这样的环境和我们净土里的办公室很搭配,我们这儿人来人往,也都和胡同串子似的。但恰逢此次牛市,互联网普及了,白领们不必灰头土脸地挤在大妈们中间炒股了,这时就有了普及些股票知识的需求。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有关这个跨越三年的大牛市,我们曾在2005年6月写过一个《千点等一回:机会和陷阱》,是从宏观经济和社会变迁角度写股市。当时股市正好跌到千点,回头看是世纪大底。当时引用了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对上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结构的分析,以战后50年代为分界,此前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以自由农场主和小企业家为主,此后大企业兴起,“新中产阶级”则以职业白领为主。中国在21世纪前10年也正经历着同样的转型,靠知识与技术谋生的白领们开始领取稳定且较丰厚的薪水,他们的投资理财需求出现了。不过,那时候白领们挣的是真金白银,时过境迁,现在“白领”又成贬义词了。就拿编辑部举例,1999年底我去美国留学,两年后回来,单位已经搬到了北京安贞地区的写字楼,办公室多出了很多生气勃勃的年轻人,都颇职业了。及至搬到三元桥的多功能厅改造的办公室,装修已经是后工业化特征了。
写《22条军规》,我们面临的是这样一群在重理轻文、重工轻商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型理财者。恰逢一个大牛市,亿万投资者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形成一种群体效应,行为经济学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在投资知识普及中经常出现的理论。我引用过波浪理论掌门普雷彻的一段名言,他说:“投资人每天读相同的报纸,看相同的电视,这简直就像广场上的情形一样,一群人聚在那里,一位煽动革命的演说家站在阳台上,令群众的情绪随着每一项变动的内容、性质以及幅度,时而高涨,时而低落。因此,大众的情绪就可以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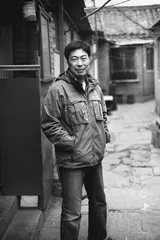 ( 邢海洋在北京南锣鼓巷(摄于2008年)
)
( 邢海洋在北京南锣鼓巷(摄于2008年)
)
我还用两军对垒来比喻股市走势的变动。在战场的僵持阶段,战事胶着一团,分不清方向,这个时候是最难以投机的。可一旦双方胜负有了些许迹象,投机者就会加入强者的一方,加入分食弱者的行列,这时候战局就会加速逆转。股市的走势,表现在价格变动上也是如此,胶着的时候最难判断,而一旦趋势成型,趋势就有了自我加强的能力。因为拔河更是所有人都有过的亲身体验,我还打了拔河的比方:拔河过程中最累最难受的时候是不分胜负的时候,一旦一边倒,那种感觉就是摧枯拉朽了。
写作这样一个封面,所谓厚积薄发,并不费力,甚至有酣畅淋漓之感。我翻出十几年前在北京图书馆复印的材料,里面有着“自学成才”时期自己一段有趣的经历。那还是1994年的事,我虽算不上“北漂”,却因为从机关辞职,把个人档案从学院路街道的人事科迁到一墙之隔的劳动科,成为一名待业人员。没事骑着自行车溜达,看到证券公司里熙来攘往,就有了靠炒股票当万元户的愿望。
学习股票知识,起初在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看些证券报之类的报刊,里面很多分析文章让人如坠雾中。后来在北图的港澳图书阅览室看到普雷彻的《波浪理论》,真是如获至宝。书中很多数字和图形,让我这个理科出身者颇有亲切感,而作者宣扬的波浪理论对资本市场走势的种种神奇预测,又与我们崇尚“天人合一”的神秘文化有着种种契合。对波浪理论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那些天,因为图书不能出借,我几乎就泡在图书馆里。全书看罢,还是不能割舍,又复印了一部分。北图保护版权,一本书是不能全印的,一次只能印一小部分。
20年前,全国上下理财知识之贫瘠,在我的求职经历中就能反映出来。怀揣着这本《波浪理论》,再到证券大厅里的时候,我也有胆指点江山了。有时在新街口的大厅里跟人探讨,还引来些争论,于是再读书再回家写写画画,不亦乐乎。那时每个证券营业部都会在入口显眼的地方开辟公告牌,每天一闭市,就贴上一种称为“股市动态分析”的传真,专门以专家的视点讲解技术分析,有些报告还专门开辟数浪的专栏。不过数浪这事,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有你的数法,我有我的数法,争论不休。现在的市场,看空和看多各搬各的论据,和当时的数浪没什么分别。
墙上的报告看多了,大多数都不能准确预测后市结果,我也从相信变得怀疑,于是给《证券报》投了一篇小稿子。没过几天,家里接到了报纸,我的投稿发表在了报纸的类似“街谈巷议”的栏目里,至于具体是什么栏目,已经全无印象。但就凭着一两百字的“豆腐块”,我在一家发布“股市动态分析”的新兰德证券咨询公司找到了工作,做起了分析师。从此以后,就是我写技术分析了。
在新兰德公司的1995年,沪深股市的投资观念还基本是技术分析的天下。股市有时候缓慢滑入深渊,再被一个从天而降的利好激活,拔地而起;有时候像自由落体一样落下,再在水面上颠几下,振幅越来越小,一切恢复平静。那时候的走势的确和力学规律合拍,就像一家中学的物理实验室,里面放上钟摆、放上滑轨再摆上个杠杆,一群中学生,新学了牛顿第二定律,即可来演示一番。推动股市上涨或下跌的力量,就是靠一群人的拔河或混战游戏。
每天面对386电脑绘出的K线图,我们似乎在监视着股市一干投资者在战场搏杀的战事演绎图。于是乎,经常想跳出波浪理论,自己琢磨出点大众心理,或者把投资者的心理与技术图形或技术指标结合起来,也升格出一点理论。最终,理论未成,我却对技术分析的兴趣渐渐失去了。正如那本宝贝的《波浪理论》,它躺在北图的书架上我读得如饥似渴,可一旦后来在书摊上几块钱就买到一本,就束之高阁了。
技术分析看似深奥,实则简单,在海外,数量投资者可以用电脑统计出股票的价格规律,用大数据炒股票。而在漫长的没有电脑介入的时代,投资者借助图形,试图总结出规律,预见未来,但这不过是个体力活,很多对高手的采访里,都是汗牛充栋的图表和被图表折磨得不食人间烟火的分析师形象。图形也的确反映出一群人的心理和实力博弈状态,在刚刚起步的A股市场和此后10年的大众理财普及中,理所当然地扮演了引路人的角色。但随后,更多深入的财会、各行业专业知识和宏观经济的判断才是判断上市公司价值所在的基本工具。而技术分析,也只有在一群没有“技术”,蜂拥而至的群众掀起的股市波澜中,可资参考。当然,这是那次大牛市后的后话。
转行到周刊,很大程度上是不能胜任技术分析这份“苦力”工作,到后来,面对电脑上闪动的红绿字符如坐针毡。做记者,对经济的解读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也不必囿于一地每日朝九晚五,心理上才真正安定下来。有时候骑着自行车到街面上转转,尾随尾气滚滚的大货车,都可能发现货车生产行业肮脏的秘密,更不用说面对生活成本的直线上涨,解释CPI背后的统计规则和上涨原因了。具体到股市,海外成熟市场,持有股票的投资收益从长期看能战胜存款、不动产甚至黄金等贵金属。而经过长年公开透明的操作,优秀的基金经理脱颖而出,自可帮助投资者获得稳定持续的收益。但这些在A股却行不通,股市就像一道闸门,闸门背后是权势者,明面上的投资者大多是被鱼肉的命运。在股市中浸淫越久,作为一名分析员,你就对它越失望。而作为一名记者,面对成千上万读者,有一个地方吐槽,也有了直抒胸臆的地方。
回过头再说2007年的股市,这场拔河比赛完全进入了摧枯拉朽的状态,股市天天涨,稍有风吹草动概念股便跟风涨。我有一个“投资理财”的专栏,偶尔也推荐一些行业或股票,写完后居然就涨停,还有读者打电话问有没有内幕。实际上,那个时候根本不必有内幕,投资者赚得红了眼,捕风捉影,有点消息就抢买,股票焉有不涨的道理。单位里的年轻人这时都进入市场,交流着赚钱的经验,大家谈得最多的是神股中国平安,每一次买入都赚,一直涨到140元。那些被股票“噬咬”过的老同事,这时也再次买入。2007年5月我们写过《12万亿财富膨胀:人人都是股神》的封面,还在2007年8月底写过《5000点的围城现象:恐慌型投资》。道琼斯理论说股市在绝望中迎来转机,在犹豫中上涨,在疯狂中结束,回想当时挑选的这些题目,正应和了投资人典型的情绪爆发。
那个时候股市里的人赚钱赚得酣畅,外围的人则看红了眼。银行和证券公司里排满了开户的人群。每天30余万的新开户基民和股民,为沪深股市的上涨输送来源源不断的后备军。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正赶上互联网泡沫的尾段,大家炒股票似乎都不过瘾了,还炒各种域名。可市场泡沫一破裂,狼藉之状惨不忍睹,几百美元的股价以几美元收场。新浪、搜狐和网易三大门户从几十美元的价格跌落到只有几十美分。手里有股票,即使坚信互联网全新的投资理念,即使以未来市场份额给公司估值的理念,眼看股价一天天缩水也是巨大的煎熬。纳斯达克能从5000点跌到1000点,台湾股市曾经的投机潮后,股价也跌过80%。那时我每周给周刊写专栏,第一篇就是《卖水的赚了大钱》,讲的就是加州淘金热中,那些后来加入的淘金者都没赚到钱,可能还赔掉了辛苦攒来的旅费和采矿资金,反而是在旅途上贩卖饮水的小贩、卖牛仔裤和铁锹等装备的杂货商赚了大钱。
亲身体验过大熊市的残酷,我对2007年股市熙攘嘈杂、人人言利的市井场面天然地抱有距离感。不得不说,在一个投机大牛市的疯狂阶段,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跟你谈股票,无论打开什么样的媒体都是“涨停板”,真有令人无处可逃之感。可我的工作又是写投资,股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所以尽管讨厌这个市场,也不得不奉命写。当时是4月底,做着自己厌烦的事,不觉喝醉,于是胡写,深一句浅一句,左支右绌也不能自圆其说,竟拿出看家本事,算起账来:先算中国有多少人有投资资格,再算多少能居住在有投资基础设施的东部地区,再算二八效应下还有多少有钱人能入市,最后看把这些人归并为家庭,有多少家庭愿意成为“最后的接棒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从庞氏骗局拉丁聚财的角度,市场已经在涸泽而渔了。
这样的苦口婆心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即使起到了警示作用,也可能构成了误导,毕竟牛市疯狂后还有几个月癫狂的获利期。不过我这个算法,却获得了颇为广泛的传播效应,几家电视台的新闻评论都予以摘录。
中国新生的白领阶层,或曰中产阶层,教育背景和职业素养本来决定了这是一群保守稳健型投资者。在中国特色的A股市场,他们却不得不被裹挟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投机中,面临着先富特权阶层在职场之外的一场绞杀。我们无力左右股市的游戏规则,也只能给股民一个方法论的引导,试图在这个财富沸腾的时代告诉大家如何去赚钱,给他们进行理财启蒙。正如巴菲特所说:“股市与上帝一样,会帮助那些自助者,但与上帝不同的是,他们不会原谅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我们的一片苦心,在上证指数13年后还是零增长的今天,在回忆中,比那时候更凸显出来了。 股票股市投资奔腾军规证券狂牛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