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墓即景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杨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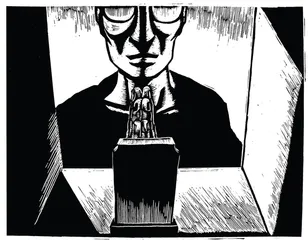
去的是八宝山革命公墓,老父亲已在那儿20年。
早年逢清明,斜穿城市,直眉瞪眼奔至墓碑前,有悲痛有回忆,完事即走,片刻不多留,没那份闲心。20年后的今日,清明扫墓如日上三竿吃午饭、月到中天睡大觉一般,细细密密织进了日常生活这块大幕布,而且几经洗晒,针脚都瞧不清了。所以不疾不徐去了,恭恭敬敬祭了,完毕正值午时,园中人少,沿山道拾级而上,饶有兴致地还参访了一些名流墓园。不少细节摄入意识的大硬盘。又因漫天杨絮飘舞正欢,使这些记忆更似梦幻泡影。
大多扫墓人群组合,是全家咸集,子孙毕至。骨灰堂的院子里不光有祭奠亲人的,还有顺道参观的。一位中年女性正压低嗓音向另两个中年妇女介绍:这儿是部级的,他们这叫“入室”,后边还有骨灰墙,局级干部,他们那叫“上墙”。那俩一边听了,踱至一间屋门前,扒着门框朝里打探,门口值班人员注视着。骨灰墙的院子里满墙鲜花,祭扫者比骨灰堂院多好几倍。刚祭扫完的一家五六口人,高声喧哗着向外走,途经另一户五六口的人家,正面对墙上一块墓碑肃穆。旁边有第三户人家迎面而来,看不惯吧,对喧哗一家人行了“侧目礼”。
北内、北外两面墙的夹道正中,停着一架铁梯。骨灰墙挺高的,最上面两排墓碑,一般人的身高想祭扫,必须借助梯子。一个老头扶着梯子,似在等待着什么。
梯子旁边有个水泥砌的水池,侧面一根自来水管,很像90年代每家每户的墩布清洗池。一个中年男人在水龙头下搓洗一块浅蓝色毛巾,搓好拧到半干,递到不远处一个老太太手中。老太太正泪眼婆娑,来回摩挲一块墓碑,轻声絮语:老头子,又来看你啦,你怎么样啊……毛巾递到,老太太开始一遍遍擦拭那块只有两本画册大小的墓碑。
老太太忙活的时候,中年男人回头,惶恐地问扶梯子的老头:您……老头指指老太太正擦拭的墓碑正上方。男人脸上迅速堆满歉意,又指指老太太的背影:抱歉啊,稍等啊……老头宽厚地微笑,摆摆手。
出骨灰墙院子向北,上山小道两边灌木丛里,是众多开国元勋、各行业出类拔萃者的一个个墓园。墓碑设计都花了心思,更有别致者,无墓无碑,只在一棵松树旁竖块牌子,标志某某骨灰撒放处。这片区域的祭拜者几乎看不到,都是参访的,不时听到惊呼:哎,这是那谁谁哎!哎,那不是那谁谁么?
快到尽头处,一小块墓园周围站着不少人,高一声低一声地热烈议论。片刻人群散开,才看清那是薄一波之墓。刚刚解散的那群人中,有一对母子正路过我身边,母亲对儿子说:看到没?连他的墓都没动,说明什么?搁这儿最放心了。别迁了,我回头也来这儿和你爸做伴儿。儿子说:可人家那儿好歹是块土地啊,入土为安,这老挂墙上算怎么回事儿啊…… 即景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