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也具有审美价值
作者:贾冬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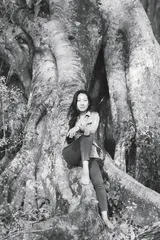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在大众眼里,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随便种点什么下去都是绿的。为什么十几年前你和马悠博士要将这里作为天籽的基地,进行生物多样性的干预?
李旻果:不知道你在飞机快要降落时注意没有,从上向下俯瞰,西双版纳遍地都是绿色“指纹”,一圈又一圈,这些都是橡胶树,已经成为一个植物行为艺术了,但这是大地悲剧。“西双版纳”这个名字意为12个坝子,每个坝子周围都是山丘,以前山丘上都是神林,现在都不复存在。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海拔1000米以下都陆续变成了橡胶林,为了割胶方便,就在山上一圈圈地环着种。现在我们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橡胶生产基地,但是代价是什么?这里一到冬天就是一片焦黄,全是枯枝和落叶。景洪1954年雾日为184天,但到了2005年仅有22天。纵向对比,你会发现,西双版纳的物候、气候,已经完全变异了。研究表明,天然热带雨林转化为人工橡胶林,每减少1万亩,就使一个物种消失,并对另一个物种的生存环境构成威胁。短短的30年过去,这片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带,就消失了70%多的雨林,这非常令人震惊。更严重的是,依附于水源林、寨神林、薪炭林等森林环境,千百年维系着各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生态传统,都在大规模单一种植的浪潮下分崩离析。曾经在西双版纳随处可见的傣族家庭园林的消失就是一个悲哀的例子。
说西双版纳种什么下去都是绿的,没错,但这是表面的绿色,或说是我们说的“林相”非常单一。就像面相代表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一样,林相单一就是被大量先锋植物入侵的结果,很疯狂,很容易引起火灾。这种懒惰地等待森林自我复原的方法,只能用在人迹罕至的原生态林子里,它可以像生态走廊一样,让物种传播,在这种环境下,才可以像以往老百姓做的轮歇地一样,砍了能再长。但现在人太多了,砍了永远不歇,一直作为草场放牛,栽种旱稻,或者把它烧了,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们要做的是一个良性循环,主动干预,积极有效地让物种回到山上,把热带山地林修复起来。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将橡胶等旗舰物种林还原为生物多样性热带雨林,还面临经济效益上的博弈。
李旻果:我们刚来到澜沧江边这片山的时候,周围没房子,也没有雨林,只有商业公司的橡胶林,我们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恢复成热带雨林。现在这片林子里有金兰,因为它独特的分子结构,对人体有特殊作用,专供娇兰的高端化妆品生产。它是从开始到第七年才成为一个产品,成为我们的自我造血机制。因为热带兰花这个物种是世界上最有奥秘的东西,它一定是长在这种生境里的,你想要这个物种必须保护这个生境。它是附生的,种子非常小,一克里面有几十万颗,就飘在树的最顶端。它不吸收树的营养,它吸收空气的营养,需要湿度、气度、风度。因此,先造雨林,才能造生产车间,金兰是第一步。
2002年初春我和先生去老班章的布朗山考察原生态植被,正赶上村民在计划烧除,其实这是一种不科学的农业管理办法,所谓为了防火,实际上想烧就可以烧,而且面积相当大。我们那一次看到正在烧荒的摇摇欲坠的树上的兰花,先生非常心疼,他说,倒下的不仅是一棵树,而是这棵树上的生态系统。所以他说,你问村里要一块地来,正在烧的地,我们来种树,把这些兰花救活。结果村里租给我们一大块地,他们最初意识到的是茶叶,但我们就想来种树,也种了10年。这两年逐渐开始在那里按照布朗族的传统,恢复古茶园林。
由此,我们探讨出一种热带雨林的再造农业,但一定是先有物种保存,然后才有再开发的可能性。我们造的是热带山地林,里面有上千个物种,我们可以从中选择十几个生物多样性的产品,古树茶、天籽金兰、地涌金莲、万代兰,一样样地开发使用价值。布朗山海拔1600至1800米,未来天籽中心还可能在其他海拔的山上各选一个点,做不同物种的恢复,做成一个活的种子银行。
三联生活周刊:天籽生物多样性发展中心作为非政府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与开发商和政府博弈的?
李旻果:只要在做事情,非政府组织和这些利益群体的关系势必要纠结,要有一种博弈。开发商拥有土地,在共同理念下合作,是我们最直接关联土地、影响土地的一种方式。我们也是政府的决策顾问,像普洱的生态茶园改造项目,普洱市生命景观系统的规划,天籽中心都作为智囊团参与了。
政府做景观恢复的驱动力,表现在含绿量、物种多样性、街道清洁度、噪音污染等多个方面,而实际效果也很显著。现在普洱市的景观强调了生物多样性,不再一条街只栽种一种三角梅,同时也强调了多层次、高绿色容积率。以前造园子叫作“花灌草”——花、灌木、草,大面积、地毯式的,寿命短,养护成本高,现在的做法则是多层次的,立体的,长乘以宽乘以高,持久性强。
生态茶园改造的初衷,是我发现欧洲人不认普洱茶,一检查里面各种指标超标,都是台地茶拼配出来的。你知道目前大规模推行的所谓“台地茶”,为了高产,首先把古茶山砍光了,整成平台,然后每米密植七八棵树,这是所谓的现代茶园改造,70年代后期在勐海大面积进行。所以现在古茶山的古树普洱完全不在欧洲人的视野内,因为一片山的古茶树挨着一大片台地茶树,山水相连,这个有毒这个没毒,跟谁说去?只有把这片台地茶换成生态茶,恢复古茶山的生态系统才行。这一代或许不能长成大树,但至少可以为后人造出一片古茶园,总有个开始。所以从2010年,普洱市开始了再造古茶园的行动,停止施用化肥、农药,降低栽植密度,补植生物多样性树种,我称之为“普洱茶的排毒养颜”。事实证明,茶农最终从中受益了,采茶工作量减少了一半,而茶叶价格翻了不止一番。
目前我们正在和德国科学家做另外一个项目——生态胶园。新一届政府也想像生态茶园一样,在胶园里栽树。
三联生活周刊:生物多样性注重的是生态修复,怎么去适应景观需求?
李旻果:我思考了很久雨林美学。你看日本,那么有限的自然资源里,造出了以小见大的枯山水;在泰国,一个西方人过去造了汤普森园林,用的是泰国当地的物种——钝叶鸡蛋花,造了一个当地人都看不懂的园子,现在成了全世界喜欢园艺的人都要去看的园林。还有很多这样的园子,随便栽栽,任它生长,就是比影响现代景观学的法式园林、英式园林要好。其实法式、英式是从药草园开始的,是为了留下一些物种,或者用作疗浴,所以在城堡或城市周围造了一些园子,按照庄园式的造园法则。而我们这里有极大的生物多样性,营造雨林植被景观是得天时地利的易举。如果换上移植来的园艺物种,最好是稀缺的,造一个别样景观,或者按法国人的欧式造园法,把它们切割了,则完全是本末倒置。你去切割一下望天树试试?七八十米高,怎么去切呢?要做的就是尊重它,把本地物种做成可以审美的东西,这个转换过程是我一直想做的。这里面还有很多科学知识和管理方法在里面。比如很多人去看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看藤蔓把树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从天上到地上,震撼不已。但我们称之为已经退化的林相,因为疯狂生长的藤蔓把最高的树冠已经灭掉了。最健康的林相是什么?要依靠很多观察、了解、研究。我在西双版纳做热带雨林恢复13年,其中跟着先生10年,我都还没有出师。在概念上我可以了,但是和自然的朝夕相处,对自然的了解,这种从心到手指的距离依然在。
三联生活周刊:用本地物种造景观,有没有成功案例?
李旻果:每一块土地,最有价值的景观,就是由当地的物种构成,具有独一无二的审美价值。我们要推的就是生物多样性的美学,我们希望形成这样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一个最好的模板就是清迈的四季酒店,用当地稻田做出了标志性景观。我以前就跟西双版纳州政府说起过,在泼水广场这个仪式性空间建一片稻田,还原稻作文化。但政府担心,游客们一进稻田,不就踩一脚泥?还是做成了一个水泥广场。之后没多久就听说清迈四季酒店,还有曼谷机场,都建了稻田景观。所以其实大家也在慢慢意识到每一种本地物种特有的美感,稻田的美感。而且原生态的稻田、生物多样性的稻田和现在单一物种的高产稻田有本质的不同,这里面有很多眼睛看不见的价值。(文 / 贾冬婷) 多样性景观生态具有物种入侵西双版纳审美价值生物生物多样性热带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