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中部城市寻找出口
作者:吴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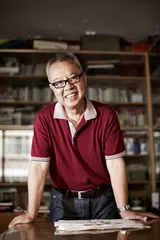
犹豫不决的改革
“武汉是中国最大的县城”,直到七八年前,外地人还经常用这句话揶揄武汉人。这句话既承认了武汉的地域面积大,又直言武汉的城市建设落后,不像一个大都市应有的面貌。了解城市开发史的武汉民用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郑国庆说,武汉的发展代表了一个中部城市的尴尬。当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市场开始兴起时,武汉的政府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那时候全国好多地方学深圳,深圳的开发很红火。可是很多城市去考察之后,又发现自己没法学深圳,那是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新城,想怎么建都有空间。可这种办法没法嫁接到武汉。”
此时的武汉仍是一个老的工业基地,在全国工业实力仅次于上海,略高于沈阳,只是没有了往日的辉煌。新中国成立前的武汉商业发达,与之相连的轻工业也发达。根据《武汉市志》的记载,1949年武汉的轻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92.5%,重工业的比例仅为7.5%。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五”、“二五”期间,国家确定武汉为重点工业建设城市,在改造扩建原有轻纺工业的同时,对重工业进行了大量投资。于是一批著名的“五字号”的重工业企业发展了起来,比如武汉钢铁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重型机床厂等。在改革开放初期,武汉的经济水平居于全国前五。
但是武汉与改革开放的时机有些擦肩而过了。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王磊向本刊提到,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是在1984年,武汉成为计划单列市,表面上好像是个机遇,武汉享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而不是省一级行政级别。但计划单列市的收支直接与中央挂钩,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两分,无需上缴省级财政。这样一来,武汉的税收不再交给湖北省,很多重要的项目湖北省就不愿意放在武汉了。而由于上期上缴中央的财政比例高,武汉市自身的城市发展慢慢落后于经济发达地区了。
与传统工业城市一样,上世纪80年代,武汉工业布局的重心聚集于江岸、江汉、硚口、汉阳等7个中心城区,其中又有易家墩(古田)、唐家墩、西马等11个工业密集区,工业区人口密度为城区工人密度的13~27倍。
老城区本应该为新产业的发展“腾笼换鸟”,可是涉及如此多国家级重工业的改制与升级,武汉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有学者向本刊分析说,我国大的经济改革,都是源于国家层面上的政策推动,武汉一直想等政策。很长时期内,武汉地方政府认为湖北“朝中无人”,万一闯了改革的禁区,承担不了后果,对于武汉的发展有些束手束脚。这导致了武汉的民营经济一直不活跃,政府管得多,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在很多领域里难以进入。而大汉口在历史上的发展,正是印证了市场的发展,不需要政府过多管制。根据美国学者罗威廉的研究,1796年乾隆皇帝退位这一年,为了镇压白莲教起义,中央和起义多发地湖北的地方财政几乎破产。然而与此形成矛盾的是,这一时期是汉口商业繁荣的“黄金时代”,它在这场叛乱的进攻中免遭冲击。清末的大汉口“政府力量已经山穷水尽,而地方经济却充满活力”。
何祚欢提到,上世纪80年代,广东一度缺粮,希望能向湖北购买,可以高于市场价。湖北为此召开省委常委会研究,三次开会讨论,认为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的,不能单独卖给广东。直到过了一年,湖北的领导才意识到,自己粮食有余量,卖给广东能赚钱,何乐而不为呢?但是那时候广东已经不缺粮了。“改革开放之后的20年,湖北落后在了观念上。”
在城市建设方面,武汉也长期以国企为主,民营经济相对较弱。郑国庆说,房地产行业早期拿地、报批、项目定位等方面,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严格完善的规章制度。“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市场总是先于法规的完善的。如果地方决策者不敢承担发展的风险,没理解透小平说的‘发展是硬道理’,就很难驾驭房地产这样资金需要大进大出的行业。”而武汉这样历史厚重的城市,既面临着老城区庞大的拆迁压力,也面临着怎么对待租界等历史街区的问题,是将租界保护起来还是利用其土地价值做大幅度的改造,各方看法并不一致。
于是上世纪末武汉的城市发展,经历了一些弯路。2000年前后当全国各地城市之间互相追赶GDP的时候,武汉也在城市外围上了好几个开发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回避老城区棘手痼疾的情况下尽快达成经济增长的目标,自然而然地这些开发区内也建了一些住宅项目。郑国庆说,但是因为城市的基础设施没有同步跟上,政府又没有能力约束开发商做好商业、教育等配套,这些远离中心区的住宅小区虽然大部分卖出,却始终难以提高入住率。这样看上去建成了大量的新住宅,老城区的再生问题却一拖再拖、变得越来越沉重。
其间曾有香港新世界、九龙仓、源兴等一批港资房企提出希望对武汉老城区进行改造的计划,但随后的亚洲金融风暴让这些计划甚至开建项目无疾而终。郑国庆认为2002年万科在东西湖开发的楼盘、2003年浙江一家房企在东湖开发的楼盘,彻底改变了武汉人对房地产的概念,“原来房子可以做得这么好,房子可以和周边的自然环境结合得这么好”。
新的经济开发区的配套短期内解决不了,到了2008年,武汉周边新城出现了居民返回老城区的高潮,孩子上学、老人看病的事情还是靠老城区来解决,新区的人们“出来了不想回家,回家了不想出来”。 而这时武汉中心城区的新建住宅项目一个接一个开盘,价格也逐步拉升,仍然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
于是政府部门明确意识到,由于土地供应量逐渐萎缩,老城区的问题已经无法回避,必须面对,这就引出在全国同类城市中相对较晚的大规模“城中村”改造。武汉计划在5年内消灭80%~90%的“城中村”,与此同时,似乎是一种巧合,大规模的交通市政设施的建设也与此同步进行,这样亦能适当降低城市改造的成本。而最近的这两年,正是城市建设的“攻坚阶段”。
期待唤醒活力
这几年武汉城市建设的力度,在全国城市中十分突出,武汉同时开工的工地可以达到5000多个。根据规划,2017年武汉将建成7条轨道交通覆盖三镇,居民公共交通出行的时间可望由2010年的51分钟减少至38分钟。
目前武汉城市建设的土地,主要由对“城中村”的改造供出。郑国庆说,武汉市政交通累积的压力大,老城区的改造和市政交通同步进行。对于“城中村”的改造,政府是呈主导地位的,可以使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成本相对较低。比如武汉目前正在修建四环线,将建成以货车为主的专线,这样三环线将不再主要是城市的过境公路,而是恢复承担起城市内部交通中快速干道的作用。交通的布局一旦建立好,“过去散落在武汉周边的几个新城,就全部活了起来”。
现在城市仍然不断向郊区扩张,但已经不同于早期,被称之为“郊区化的3.0版本”。郊区的“独立成市”,配备了交通、教育、商业等配套资源完备,具备一个完整单独的城市的功能。这种多中心的战略引导了市场资源的配置,使其更加合理。
谈到武汉即将发挥的特点,研究者认为武汉的区位位置、工业传统和人才储备仍将在新一轮发展中,发挥出优势。王磊说,武汉之前的交通设施没有建设得很好,其中一个担心是自身的工业实力不够,交通畅通以后,资源反而就会流失到外地去。现在城建发展快,很重要的一点是城市建设必须和工业实力相符。“我们讲‘中部崛起’,相比东部有地缘优势,西部有政策优势,怎么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很重要。”
但是现在武汉改变了思维,准备建第三航站楼,开通更多的国际航线,武汉还有“祖国立交桥”计划,利用武汉的区位优势,发展交通运输。在水运方面,武汉会争取五年内成为最大的内陆港口。
“现代大工业的货物运输需要大进大出,水路是最廉价的,武汉仍然可以发挥通江达海的水运优势。”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的副教授黄永明告诉本刊,武汉会发展“大临港”,利用阳逻港的优势建立化工工业园,吸引大的工业项目,“武汉提出了工业倍增计划,希望2020年工业整体发展水平跨入全国先进城市行业”。
于是与很多城市不同的是,武汉将自己定义为“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仍旧准备利用自己工业体系完备的优势,对工业进行升级。事实上,武汉对于到底以发展工业为主,还是服务业为主,有过犹豫。政府最终意识到,工业基础良好的武汉,应该依托传统特点发展产业。黄永明说,如果第二产业不发展到一定程度,第三产业是起不来的。有些城市一味强调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是这些“软性”的实力是需要产业基础的。武汉经济开发区的汽车产业已经体现出集群优势,光谷作为高科技研发企业集中的地方,产业布局先进。黄永明说,“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产品,服装业是传统产业,但是高端服装业市场前景仍然非常好。我们过去搞汉货精品,现在一样需要建立武汉自己的品牌。武汉有着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同时武汉高校数量全国第一,武汉今后将更大程度发挥出产业自主创新的能力。”
王磊说,目前武汉市的第二、第三产业,都面临“高度化”不足的问题,技术含量和创新不够。比如第三产业中,房地产业这两年发展很快,但是金融、法律咨询等行业就发展很慢。要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仍然需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激发它们的活力”。(文 / 吴琪 周翔) 武汉发展中部武汉城市武汉市寻找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