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的理论与中国需求
作者:吴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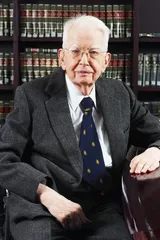 ( 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 )
( 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 )
企业与市场的边界
“在人生的长河中,我结识了一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从未视己为其一员,或与之为伍。”1991年,科斯在诺贝尔奖的获奖致辞中,自谦地说自己发现的经济学特征“如此明显,恰如G.K.切斯特顿笔下布朗神父系列故事之一《隐形人》中的那个邮递员,反而易被忽视。然而它们一旦被纳入分析,我相信会带来经济理论结构至少是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的彻底变革”。科斯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证明生产的制度结构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重要性”。
这是一次对科斯理论充满趣味的嘉奖,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对经济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其观点的全部要义在1932年就提出来了。“那时我21岁,人生刚刚起步,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些观点在大约60年后竟能成为摘取诺贝尔奖的主要依据。年届八旬,因20多岁时能做的工作获奖,对我来说实在是奇特的经历。”
虽然21岁在讲授课程时就提出了有开创性的理论,但科斯之前的经历并没有多少早慧的宣告。他1910年12月出生在伦敦的近郊威尔斯登,父母是邮局的职员,文化程度不高,但修养良好。年幼的科斯一度因为腿疾而上了残疾学校,他说自己在那儿学会的唯一东西可能只是编篮子。后来科斯进入基尔本中学,受到良好教育。他爱好历史和化学,但由于不懂拉丁文放弃了历史,因为数学基础不好又放弃了化学,当时商业学成了科斯的唯一选择。科斯后来说,他很庆幸当时的选择,否则他可能只会成为一个平庸的历史学家或化学家。
1928年,18岁的科斯进入了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商业学,科斯深受普兰特教授的影响,学习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了解到整个经济体系是透过价格体系的运作来协调。科斯在诺贝尔奖致辞中说,亚当·斯密写出《国富论》发表后的两个世纪,经济学家的主要活动似乎是填补亚当·斯密体系的空白,大家几乎只围绕着定价体系,而忽略其他主题。他们“只关注市场中发生的事情,诸如生产要素的购买以及这些要素的产成品的销售。至于在购买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则被完全忽略了”。
科斯心里有一个看似简单的疑问:如果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为什么还会有企业呢?假如定价体系提供了协调所需要的全部功能,为何还需要管理呢?
科斯的这个疑问,其实正踩中了主流经济学的“黑箱”。他特别强调经济学家对真实世界的关注,说“经济学家研究的只是自己心目中而不是现实世界的经济体系,我称这种研究的成果是‘黑板经济学’,其中的企业和市场有名无实。主流经济理论常将企业描述为一个‘黑箱’,企业也确实是未打开的黑箱”。
大学第三年,科斯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卡塞尔旅行奖学金,他决定去美国一年,研究美国产业的纵向和横向一体化。此时的科斯是个社会主义者,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战争和经济衰退,让他转而关注到社会主义理论。他学习列宁的著作,1932年去美国拜访的人里边包括社会主义党的总统候选人托马斯。“列宁说过俄国经济系统将像一个大工厂那样经营。然而,许多西方的经济学家坚持说这不可能。但西方确实有工厂,其中一些还相当大。我们该如何将经济学家关于定价体系的作用和成功的中央经济计划的不可能性,与管理的存在及明显的计划社会、在我们自身经济体系内运营的企业的存在协调起来呢?”
幸运的是,科斯在1932年夏天就找到了答案——他意识到存在使用价格体系的成本,即交易成本。正是对进行市场交易成本的回避,可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在分析企业的起源、性质和生产纵向一体化的过程中,科斯首次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经济分析,奠定了现代西方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的基础。接下来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德姆塞茨、张五常对这个主题做了重要的研究,科斯和他们一起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
这时的科斯仅仅是个20岁出头的本科生,他没有去追逐当时流行的经济学问题,比如“如何规划投入产出”和“如何达到充分就业”等,科斯关心的问题显得很生僻。他终生都没有拿过经济学博士学位,甚至不算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但他坦言这恰恰是其优势——他可以不受成见的约束,按照自以为然的方式去锁定问题、思考问题和回答问题。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向本刊提到,他和经济学者刘伟是比较早接触到科斯理论的,那是在1985年。“科斯研究为什么要有企业,这样的问题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科斯看到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市场上价格机制起作用,企业内管理协商机制起作用。交易成本的大小可以界定市场和企业的边界。同时,企业内部管理的成本应该低于市场交易成本,这意味着企业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他意识到当时西方兴盛的汽车托拉斯、钢铁托拉斯会潜藏着内部交易成本过高的危险。”
而当时中国经济学者知道的西方经济学家是凯恩斯、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几人,对于其他正活跃在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知之甚少。科斯的理论对中国人非常有实用价值,正进行改革探索的中国人,解读到科斯理论中关于市场和企业的边界问题,这对于中国公有制之下行政权力过大,有着警示作用。平新乔说:“如果市场延伸到企业内部,企业会消失;但是如果企业扩展到整个市场,那就成为失去活力的计划经济,用指令代替了市场交易。”
科斯这篇重要的文章《企业的性质》,在当时并未获得太大反响。可是它的影响却在持续发酵,并且重要性日渐彰显,后来通过威廉姆森、德姆塞茨、张五常对生产的制度结构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重要性进行了进一步阐述,使得新制度经济学渐成体系。
产权研究与中国需求
带给中国经济改革更大启发的,是科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科斯的好友张五常说:“科斯是个个性很强、观点顽固的人,对当时盛行的好些理论漠不关心。他不断地鼓励我走自己的研究路向……他构思《企业的性质》时只21岁,我没有听到过另一位学者能在一门学问上的执著持续那么久。”
科斯非常注重对现实世界的研究,1935年科斯到母校伦敦经济学院任教,讲授公用事业课程。他发现经济学家对这个领域知之甚少。科斯于是对自来水、瓦斯、电力、邮政与广播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深入了解其运营和定价机制。这些在当时都是经济学的冷门。
1951年移居美国后,科斯调查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因为他见到该会控制着整个美国的所有传播行业,是一家垄断权力非常庞大的机构,他要问这权力从何而起。科斯找到的答案是,该委员会的前身是一个收音委员会组织,起于美国的东北部——波士顿一带。20世纪初期,东北部的渔民出海捕鱼,靠收音机与家人联络,问天气、报平安。收音机的音波有频率,这频率应该每艘渔船各自不同。但在没有管制的情况下,不同渔船用同一音波频率,在空中互相干扰,弄得一团糟。有些好事之徒乱用频率,传达假讯息。科斯提出疑问:音波频率究竟是谁拥有的呢?为什么不界定为私产然后让市场决定谁有使用权呢?
1959年科斯发表的《联邦传播委员会》,提出了“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必要的先决条件”。而且科斯认为物品的交易不要从物品本身看,而是要从物品有什么使用权利及权利谁属的角度看。
在此之后,科斯进一步研究提出《社会成本的问题》,成为他继《企业的性质》之后,受到瑞典科学院嘉奖的另一篇文章。科斯确定了产权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界定。
平新乔解释说,在科斯提出《社会成本的问题》之前,经济学家将凡是不能定价的纠纷都叫作外部性,比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社会治安,他们认为这些是市场经济失灵的地方,需要政府干预。而科斯根本不信这个,他认为市场能搞定一切,如果市场解决不了,是因为产权不明晰。所以如果公共产品的产权能够明晰,比如明确空气的产权,污染是可以治好的。污染者可以出钱买污染权,被污染者可以要求得到补偿权。这为后来的碳交易打下了思想基础,促成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碳交易市场的出现。
而科斯的思想,对于创立法律和经济的交叉学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科斯认为,在市场中交易的东西,并不像经济学家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进行某些行动的权利和个人拥有的、由法律体系确定的权利。那么法律体系将会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前者控制后者。它使得“法律和经济学”的研究在美国法学院兴盛起来。
科斯坚持以“双向”的角度来看待污染和侵权行为。牛吃了小麦,牛的主人就应该对小麦的主人进行赔偿;糖果作坊发出了噪音,糖果商就应该对隔壁的牙医做出赔偿。但是反过来,如果不让牛吃小麦,牛的利益就受到损害,不让糖果作坊工作,糖果商的利益就受到损害。科斯以中立的角度看待污染和侵权,让市场行为来解决很多过去被视为“外部性”的问题。
平新乔说,科斯抓住了“产权”这一核心概念,打破了原来大家认为的,社会主义必定是公有制、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制这样的简单概念。无论是公有产权还是私有产权,都可以使得产权明晰。“中国人从来没有想过产权可以交易,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在明晰产权。”80年代科斯的思想进入中国后,经济学者大声传播,给决策者也带来了影响。“科斯的著作只用语言去分析,没有用大量的数学模型,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理解。而且他看到的是日常生活的经济规律,让人听了豁然开朗,都能明白。”之前中国经济找不到出口,不知道如何盘活资产,公有制主体是人民,可是大家不知道人民该如何有效享用资产。科斯让大家明白了,产权明确之后可以交易。
张五常也提到,科斯的观点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是重要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已对北京的朋友提出一些改革建议,但私产他们怎样也不接受。他们可以接受市场,但不接受私产。没有私产怎可以有市场呢?我因而推出权利要有界定之说,他们容易地接受了”。
科斯也让中国人意识到产权可以有很多层次。平新乔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出现的承包权的改革,只是撬动了最浅层次的产权。中国后来放开一点土地市场,发现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如果在本村内流动,能够对资源做好的配置。再后来中国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一开始怕引起私有化,要求必须设定法人股,保持公有制的企业性质。到了1995年之后,政府开始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由过去考虑数量上公有制占主体,到变为关键领域公有制为主,小的国有企业可以彻底私有化。“科斯的思想破了中国改革的难题,放开国有企业产权后,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把制造业里边上百万家企业给盘活了。”这就是对科斯思想的运用,“清晰产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2000年之后,中国的土地市场开始产权交易。在开放土地的产权方面,一开始国家设置的障碍比较多,比如破产的乡镇企业的土地可以卖,但只能卖给集体企业。土地的买卖都是国家征用后,再卖给开发商。“现在我们开放的是70年的土地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2012年这个制度已经走到尽头了。如果国家不承认农民对产权的合理权利,改革会出现极大的问题。特别是2003年之后,中国产权改革几乎停滞不前,土地的产权、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产权、环境污染问题的产权都需要改革。”平新乔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主要是开放了国有企业的产权和一部分土地的产权,这些产权交易使得资产增值,盘活了经济。“国家开放这么一点产权,就给经济带来了如此大的繁荣,接下来如果我们开放采矿权、资源权、污染权,开放金融,经济还会释放非常的大的活力。如果不开放其他领域,经济的活力和资源仍会像过去那样,都挤到了房价里。所以我觉得科斯的思想在中国还能实用50年。”
面对中国经济学者的热情,科斯保持着一贯的冷静,他说并不清楚为什么自己的理论对中国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他早已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非常关注中国的改革。科斯说:“中国学者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口众多,所以学者的影响范围大;二是中国的经济学尚未完全定型,有更大的灵活性,更可能走上更可取的道路。”科斯希望中国在改革实践中能出现“中国经济学派”,他把推广“真实世界经济学”的希望寄托在中国。
科斯的中国助手王宁教授告诉本刊,科斯一直强调活的理论只有来自对具体经济实践的研究和反思,没有一成不变的经济学理论。他逝世前认为,中国目前最迫切的挑战是开放思想市场。(文 / 吴琪 周翔) 科斯产权理论平新乔产权经济学需求理论经济学理论中国企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