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特·芬格斯坦的藏书票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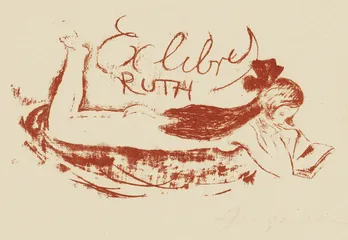 ( 鲁斯·芬格斯坦藏书票,芬格斯坦绘,石版(1916年) )
( 鲁斯·芬格斯坦藏书票,芬格斯坦绘,石版(1916年) )
1987年9月11日的《纽约时报》讣告版刊登了一则题为《皮特·芬格斯坦——艺术家兼教授逝世》的消息。这位纽约佩斯大学艺术系的创始人在本周三因胰腺癌医治无效病逝于斯耐山丘医院,享年71岁。皮特·芬格斯坦(Peter Fingesten 1916~1987)是米歇尔·芬格斯坦的独子,他的离去注定是芬格斯坦家族的终结。这位早年便与家人诀别的波西米亚后裔承载着父辈的寄托,沿着父亲的足迹继续着那条未走完的艺术之旅。1939年的一个夏日,在意大利的某个港口,皮特被父亲送上了开往美国的客船。
1914年芬格斯坦与妻子比昂卡(Bianca Schick 1889~1941)结婚,膝下有一儿、一女,儿子皮特出生于1915年,女儿鲁斯(Ruth)比哥哥晚一年降生。在那个时期,芬格斯坦尽情享受着天伦之乐,女人、孩童等融会亲情元素的主题占据了他作品的大部分空间。根据已故德国藏家恩斯特·迪肯(Ernest Deeken)在2000年编著的《芬格斯坦藏书票清单》记录,芬格斯坦曾为妻子比昂卡制作过一张藏书票,为纪念女儿鲁斯出生制作过两张,为皮特则制作了八张书票。1929年芬格斯坦与比昂卡离婚,女儿鲁斯跟随母亲去了南非,皮特则一直陪伴在父亲身旁,成了他唯一的亲人。在芬格斯坦的眼里,皮特时而是他在南欧街市上见到的朝气小伙,时而是他绘画作品中的英气模特。皮特生于柏林,从小在父亲的版画工作室长大,16岁时即在德国举办了个人雕塑作品展。在柏林艺术学院主攻了几年雕塑,皮特已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在移民美国前,他已拥有了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23次作品展。这枚书票算是芬格斯坦为了勉励儿子在雕塑方面能学有成就而精心制作的,画中矗立的撩人的胴体雕像恰似皮特即将完成的作品,只见他兴奋地弹起吉他,手舞足蹈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芬格斯坦在艺术方面有意与儿子合作使得皮特经常会参与父亲在藏书票圈内的活动,这个“二人家庭”在意大利与当地结识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意大利现代藏书票画家社团”。在父亲的熏陶下,皮特也开始制作藏书票,即使之后去了美国他也没有放弃创作这门父亲毕生经营的小众艺术。
徐志摩说:“哪一个不朽的艺术家不是在苦痛中实现艺术,实现宗教,实现一切的奥义?”1939年5月,为了安全起见,芬格斯坦把皮特送到了美国费城生活。美国书商、藏书票藏家伊丽莎白·戴伊蒙德和丈夫杰克·戴伊蒙德接纳了这个即将失去自己唯一亲人的青年。芬格斯坦曾为伊丽莎白制作过书票,二人仅凭通信往来,素未谋面,在患难时出手相助,再次验证了微薄的书票孕育着人间的真挚情感。在费城,皮特幸运地遇见了他的资助者,一位百万富翁的遗孀——瓦瑟曼夫人(Joseph Wasserman)。瓦瑟曼按月接济皮特一笔小额的支票。这位年轻雕塑家的“工作室”是一间从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借用的车棚,下雨时棚内便是一片“床头屋漏无干处”的狼藉。到了晚上,他只能租间地窖将就过夜,即便是地窖的房租对于一个“孤儿”来说也是奢侈的。为了讨好那位爱尔兰裔房东太太,皮特会教老人如何做马赛鱼汤、匈牙利炖牛肉、意面肉酱。三种菜肴想必均是他母亲当年的拿手菜。“我当时已经7天没交房租了。”皮特在日后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但她待我就像亲母,居然帮我打理生活。当我生病时,她会照料我。现在,她竟然想让我教她画画。”1940年《时代》周刊3月首刊的艺术栏以题为《幸运的芬格斯坦》的撰文:皮特·芬格斯坦,一个从欧陆逃难来的青年雕塑家,留着一撮小胡子,胸前戴黑色大领结,20多岁的小伙儿显得桀骜不驯!此时的芬格斯坦已被逮捕。尽管父子二人身各一方,皮特与集中营中的芬格斯坦仍保持通信。他日后回忆:“父亲在信中提到对意大利南部的风景赞不绝口,那里比北部要安静许多,他已经决定等战争结束后会在那里定居。”
当我们还在为藏书票是否应该贴于书中而喋喋不休时,皮特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率先总结了这一似乎永不会终止的争论。1943~1944年美国藏书票协会年刊里,皮特发表了《论当代藏书票》一文。他将藏书票比作是其作者和票主合作的终极见证。在长达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藏书票经历的几次变化不仅受到了社会变革的助推,而大时代发展趋势对其产生的连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现代藏书票俨然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不仅是早期以实用为主,证明书的所属权的象征标签。从某种角度上说藏书票变得更加“民主”,藏书票的交换,版画技法的不断推陈出新,资助者、票主个性要求的不断私密,文化、国家界限的模糊,艺术家自我矜持的创作个性等等元素构成了当代藏书票的大背景。皮特认为一张适应潮流的藏书票必须具有三个元素:“内在功能性”、“作者的艺术个性”、“票主的个性”。首先,票主要明确制作藏书票的目的。如果排除其固有的实用性,那么书票当亦被视为一门私人收藏品,既可用来与票友交换,也可作为装饰性版画。然而,票主有时过于放纵“任性”的作者,尊重并充分利用作者在版画创作上的优势才能得到双赢的结果。当然,票主在整个书票制作过程中毫无疑问是占主导的。
上世纪50年代,皮特开始在佩斯大学任教。佩斯大学在美国以经济、工商专业闻名。为了增加学院的艺术气息,皮特说服了学校的决策者,白手起家建立了佩斯大学的艺术系。1956年,他在佩斯大学纽约市校区开办了第一家校办画廊,不久纽约上州维切斯特分校区的画廊也正式开放。皮特任艺术系主任直至1986年退休。在他病逝后,佩斯大学为了缅怀这位艺术家和教育家,将皮特一手创办起来的画廊命名为“皮特·芬格斯坦画廊”。严格地说,皮特并非是一名职业艺术家,他更像是专为传播艺术而生的学者,甚至是年轻人崇拜的偶像。他一生所著不多,仅有三本,每本著作却涉及艺术、宗教、审美三个不同的领域。他的学生在多年后仍坚持认为他是一位“被忽视的大师”。在一次佩斯大学校友聚会上弗雷德回忆道:“我在60年代中期选修过皮特的‘艺术史’。他上课时总是十分动情!他的口头禅是用意大利语说‘该死’。当时,我和几位对经商毫无兴趣的朋友‘误入歧途’进了佩斯。在皮特的课上,那些只懂赚钱的呆子们对他讲的东西摸不到头绪,我们几个好像才是皮特的忠实听众。自那时起,我开始对艺术着迷并取得艺术史学士学位。”有的学生至今还对这位个性强烈的教授仰慕不已。皮特嘴里含着的烟斗是他如影随形的标志。他与妻子卡洛尔(Carole Cacace)穿的花呢格西服情侣装曾是校园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 鲁斯·芬格斯坦藏书票,芬格斯坦绘,石版(1920年) )
皮特是幸运的,至少比他父亲幸运得多。乱世淹没了世间过多的真情,但摧毁不了人的信仰和理想。芬格斯坦在恶斗的漩涡里挣扎着,他使尽自己最后的力气单臂将儿子托出了泥潭。一张旧照上,人过中年的皮特,眼眶深陷,苍迈的面庞下郁郁寡欢的眼神在试图向苍天倾诉:他,一个波西米亚人,倦了,老了,他注定是波德莱尔笔下《旅行的波西米亚人》,他惋惜自己的苦涩旅程。
 ( 皮特·芬格斯坦 )(文 / 子安) 藏书票父亲格斯艺术美术皮特格斯坦
( 皮特·芬格斯坦 )(文 / 子安) 藏书票父亲格斯艺术美术皮特格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