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黑:我眼里的中华民族青少年时代
作者:李东然
“放在眼下的市场环境里,《大秦帝国之纵横》看上去不够娱乐,不够颓废,不够物质,不够消遣,甚至过于崇高,大概会使一些人心生排斥。但我心中的大秦恰恰不是虚妄浮夸的,或是说意识形态化、概念化的崇高,反而它就是一股子有关生命本身的力量,这也是我选择拍这段历史的缘由。自始至终,我希望自己也保持这样一种精神面貌,全情地投入。”《大秦帝国之纵横》的总导演丁黑告诉本刊。
丁黑祖籍陕西,出生在西安,成长在西安,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后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电视剧导演职业生涯起步于根据作家何申的六部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大人物李德林》,初出茅庐便因对文学原著精髓的准确把握脱颖而出,从此扎实的文学功底成了他的职业招牌。而真正使他声名鹊起的是在2003年拍摄海岩编剧的《玉观音》,此后他又将《平淡生活》、《长恨歌》等当代文学作品搬上荧屏,一次次掀起收视狂潮。
电视剧拍了快20年,丁黑觉得《大秦帝国》算是在走过求生存求成功的大段路之后,再回首找寻自己追求的、向往的、认同的所在,“所以反而有点豁出去,把自己当回事一次,这个东西能够共鸣就共鸣,没有共鸣也没办法,‘雷剧’已经铺天盖地,不如我就想拍个正剧试试”。
当然,能“正”在这样一部投资上亿元、全剧有名有姓的人物角色近200个、剧组常规工作人员400余,最多的时候达到1000余人,从南到北转场了7个地方、仅装道具的巨型集装箱车皮就有16辆之多的《大秦帝国之纵横》上,丁黑说自己心中全是感恩。“更满足的是这段经历本身,20年职业生涯里的头一回,一部戏真的把一群满是热爱和热情的创作者聚集到一起,大家齐心协力去做些逆潮流而上的事儿,此番经历足以永生难忘。”
“投资人焦阳算得上是半个秦史专家,又是西安人,对于历史本身是有执念的。”丁黑告诉本刊,“虽然前期我们就请了历史专家座谈,也将演员们集中起来上课,但其实焦阳自己就教了我许多。比如,青铜器本身的颜色是怎样的,器物上究竟有怎样程度的锈迹是可以在这样一部写实年代戏中出现的,那个时代人的坐卧行走穿衣戴帽,甚至是衣服的花纹样式是什么样的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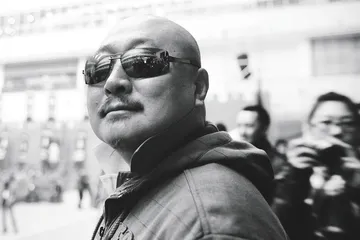 ( 导演丁黑 )
( 导演丁黑 )
丁黑说,他最早听说焦阳真的要动这个大部头历史戏时,他从第一部时便跃跃欲试,至于如何宏观看待这段秦史,事实上许多观点两人之间已早有默契。但也就是因为做朋友在先,丁黑说自己也须毫无保留地把职业经验分享给老板。“我们商量好拍历史正剧,拍好看的历史正剧,但我同时也与他明确,今时今日正剧再好看,对收视率也是一个考验。至今我仍清楚记得焦阳回话时的斩钉截铁,他说:‘这个你不用考虑,这个压力在我身上,不在你身上。’”
为了这个正剧的理想,又有了编剧李梦的加入,丁黑导演最感慨的是他和焦阳、李梦三个男人因为这一段秦史情结联系起来,再无彼此之分,全是无条件地鼎力相帮,至今那些惊心动魄的时间点还清楚地记在他的脑子里——春节后建组开始前期,李梦是刚刚开始重写剧本;9月底开拍,李梦能给的也只有十几集台词。“但是那时候我已经等不了必须开机了。大秦筹备了快一年,而在国内的影视剧生产模式里,电视剧前期准备通常只有一个月,这已经拖得太不正常了,怕散了人心,所以必须得开机。但拿着十几集的剧本拍40多集的戏,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在走钢丝,睡着觉都能惊醒。但看看李梦给的这十几集,又心知肚明唯有他能写下去,并且能安稳扎实地写下去,戏才能成。”
 ( “秦武王举鼎”这场戏完全依据史实拍摄 )
( “秦武王举鼎”这场戏完全依据史实拍摄 )
剧本没有落定,却已经开始“烧钱”,丁黑告诉本刊,说到底,他担心的还是如此大体量投资的风险,只不过这一切焦阳全看在眼里,却没有一个“不字”,没有一个问号。“李梦写剧本慢,但这也是客观实际的时间需要,他是字斟句酌的一个人,为了一个人名一个地名能翻上一整天的书,写到最后已经完全和周围人的世界脱离,每天都是写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七八点睡觉,到下午四五点钟起来吃个早饭,然后又是一夜。所以,打电话永远找不到他,见面是一次比一次消瘦,最多时瘦了得有将近20斤。但我们就相安无事似的这么过了半年,仨人也不怎么见面,偶尔见了也是煮酒烹茶谈天说地,聊我们心中的大秦梦,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似的,但心里全是彼此间的体谅甚至疼惜。”
所以,丁黑说,他常觉得,有时候想到《大秦帝国》,想到是自己导演的,觉得很骄傲,转念之间,又觉得好像自己什么都没做似的。在《大秦帝国》面前,好似本来就有那么一股精神力量,焕发了每个人的精气神,并使之凝聚在一起。“剧组里的每一天,我都赞叹怎么一次就碰上了这样多特别棒、特别有热情的好演员,富大龙、喻恩泰、宁静、姚橹、周波、杨志刚等等,这些人无论腕大腕小,没人提条件,顶多是单人间、带一个助理,再没有任何要求。为了打造出年代质感,我们的戏服很重,尤其冷兵器时代的那种力道,每一副盔甲都在六七十斤左右,男演员们常常就这么穿一整天还要不断走位。李梦的台词还是偏文学化的,半文半白的对白很多,不是一般的难背,但连我自己都惊讶,我从头到尾没有因为演员的台词发过一次火,每个人都背的滚瓜烂熟上来就演。”
丁黑尤其难忘的是一个编号202的房间,剧组转场到涿州后,演员们就熟悉起来,扮演嬴驷弟弟的演员荆浩,是个人高马大又爽朗热情的人,他每天拍戏结束后,就在自己房间里备些花生小酒,招呼其他演员来聊天,演员们于是渐渐都聚在一起。“后来我也给拉去,大伙就一起聊天、唱歌,热热闹闹。也不知怎的,每个人到了那间屋子之后就都感性起来,有一回姚橹放了一首草原歌曲,一群大老爷们竟哭成了一团。大家也常常聊到天擦亮,从戏聊到了人生,又从人生聊回到戏里,畅所欲言。但当说起业务,每个人都很较真,围绕着各自的人物、彼此间的配合常会争个面红耳赤,好在一碰杯又都是好哥们儿。常常吃完饭聊完就差不多得各自回去背词开工了。”
转眼离开《大秦帝国》已经两年有余,戏也在一部紧接一部地拍下去,有时候丁黑觉得,得刻意去忘了那一段“大秦”时光,为了更切实际地做好眼前的事。而拉远了距离冷静了热情之后,又常常琢磨种种不舍,尤其想找出个答案,如此大动干戈究竟意义在哪里。“从小我们读史,被教育成非得带着虔诚仰着脑袋,当它是遥远神圣所在,再就敬而远之了。但我觉得,所谓历史,不过就是今天的现实,今天的现实大体也就是历史的再一次投射,认识历史和了解现在其实是紧密相连,无论对于家国民族还是个体人生,历史其实都是无比珍贵的。我不知道《大秦帝国》究竟把那个遥远的时代说清楚几分,但我想不管怎么说,重提了一段值得提起的事儿,而且还把那段事儿往和我同时代的人身边拉了一拉,这是使我感到满足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部《大秦帝国》中,你和编剧李梦之间的密切合作在如今的中国电视剧创作现状中并不多见。
丁黑:当初我介入这部连续剧的时候,原编剧张建伟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剧本了,因为《大秦帝国之纵横》中的“纵横”,说白了就是外交。可是,讲外交的话,战国七雄,等于是秦要跟六国打交道,这对电视剧是一件特别不经济的事。张建伟的版本基本上解决了如何处理秦与六国关系的问题,给出了一个电视剧样式下可行的故事架构。而且张建伟是职业编剧,在他的概念里,电视剧就得按电视剧的路子走,创作上得偏向娱乐化。他刚完成殷桃主演的《杨贵妃秘史》,也是稍微偏娱乐化的。但当时这个剧本的定位和焦阳对《大秦帝国》的定位有一些出入。焦阳是陕西人,本身是先秦历史的专家,他自己对于那段历史是很执著的还原态度。
我接手以后,首先得把自己的功课给补足,思考所谓历史精神和电视剧到底应该怎么结合,焦阳的历史正剧定位如何实现。李梦就是在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加入进来的。找到李梦让我们觉得特别庆幸,现在能写历史剧的编剧本来就不多,能写这个时代历史剧的编剧就更少了,何况这个时代本身的历史资料非常有限,所以得在翻阅大量史料的前提下,才能完成剧本。而当时找到李梦的时间点已经是剧组开始前期准备工作的时候了,时间非常紧迫,如此短的时间内要读大量资料,然后再写成剧本,是挺困难的。巧的是李梦刚好写过一个有关秦史的电影叫《铸剑》,对那段历史有所储备,他马上就能接,就能写。其次,他对这段历史也有特别强烈的情感积累,这使得在贯穿整个剧的色彩也就是我们崇尚的精气神上,有了相当的默契。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电视剧导演,你素来擅长文学作品的改编。而实际上,《大秦帝国之裂变》是由导演黄健中和小说作者孙皓晖两人共同完成的。为什么你觉得《大秦帝国之纵横》中编剧的参与十分重要呢?
丁黑:我也考虑过按照小说的架构去安排整部电视剧,事实上,在整个改编和拍摄的过程中,原著在精神气质和大历史观方面的呈现,始终是我们追寻和效仿的,我们只不过是试图用电视剧的方式来再现。
但是从小说到电视剧的直接跳跃在我看来到了《大秦帝国之纵横》是无法完成的,这不在于小说的质量和可看性,而是文字和电视剧影像叙事方式的差异。简单说,小说的对立关系是建立在苏秦和张仪分别主导的合纵和连横两股力量之间的拼斗。但是这两个人本身一个在秦国,一个领军六国,基本是不照面的。张仪是给嬴氏出主意,苏秦是给六国国君出主意,战场上有交锋,但这两个人的故事却是平行发展的,这就是直接拍摄的困难。电视剧毕竟是直白通俗的表达方式,起码老百姓需要看到主人公见面,发生故事,才能看得下去。此外,小说情节也都是大段大段的,比如先用七八章讲秦国,再用四五章讲魏国,如果直接沿用这样的叙事方式,很可能变成拍四五集秦国的故事,搁下之后再讲四五集魏国、楚国、赵国、燕国的故事,观众就无所适从,到底是看一个戏,还是几个戏?所以拿小说直接改编实在是难度太大。
三联生活周刊:能不能具体说说怎样的秦的精神气质将你和焦阳还有李梦联结到了一起?
丁黑:秦王国时期在我眼里就是中华民族的青少年时代,充满朝气、热情和生命力。没有经过后世文明的腐蚀,不只是秦国,当时人的精神面貌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就像兵马俑,每一个的身高都在1.9米以上,都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极具生命力的。《大秦帝国之纵横》讲的是所谓春秋战国的交接时期,偏春秋末期,那时候的人带着朝气,是凛然站在历史舞台上的。比如连当时的军事上都更崇尚阳谋,不齿暗处的权谋阴计,虽然战事频繁,却也因此酝酿了侠客、剑客精神。秦之所以能胜,或者秦在那个时候能崛起,得益于变法,变法就是解放人的精神,运用实际的物质方式——征战或是种田,大家都是平等的,全都凭本事丰衣足食。尤其放在秦国当时是如此积弱积贫的蛮夷小国背景下,更能体现这种平等和协力。《大秦帝国之纵横》里秦惠文王继位,开始放眼天下,着眼于山东六国,开始有一统天下的意图,所谓纵横实际上也包含着崛起。这时候的秦国,政治制度上也不像秦始皇时期所谓暴政,就像秦惠文王和魏国人张仪之间的厚重情意,那时候的人内心是开阔的,重情守信,是梦想家也是耕耘者,活得灿烂美好。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李梦的台词有很高的评价。
丁黑:李梦的台词确实很凝练,很概括,有文字的美。李梦特别注重选词的音调,他的谈吐也很有说服力。一般南方人说话是不容易抓住重点的,因为南方人说话口音普遍偏重,但李梦不知怎的很懂得言语本身的节奏、味道。而且很多都是四六句,比如张仪的“敬这大争之世,敬这小酌之时”,这样的排比,再加上音调,就特别有味道。李梦他确实给这部戏添彩不少。跟今天的所谓古装戏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的古装戏也是半文半白,但一味枯燥而已,而且是听不懂的。李梦确实既让你能听明白,同时又非常古雅,有古趣。(文 / 李东然) 眼里文学丁黑焦阳内地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中华民族李梦古装剧青少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