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台计算机
作者:袁越(文 / 袁越)
 ( 埃尔温·薛定谔 )
( 埃尔温·薛定谔 )
薛定谔的演讲
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于1887年8月12日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从小就喜欢数学,后来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并于1926年提出了用波动方程描述微观粒子运动状态的理论,后称“薛定谔方程”,他因此获得了193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薛定谔留给世人的最著名遗产还不是这个方程式,而是那只“薛定谔的猫”。这是他设计的一个关于量子力学的“思维实验”,即把微观粒子想象成一只猫,把量子力学的一些原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从而颠覆了人们在宏观世界中培养的常识。
这只猫的诞生和薛定谔的生活环境有点关系。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维也纳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很多行业都涌现出一批革命性的人物,比如音乐界的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把古典音乐的后期浪漫主义推到了巅峰,建筑界的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创立了包豪斯学派,美术界的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创办了“维也纳分离派”,在绘画中大量使用性爱主题等等。这些新思潮培养了薛定谔的叛逆精神。
这其中,尤以画家克里姆特对薛定谔影响最大。正是在克里姆特的启发下,薛定谔开始尝试各种形式的性爱,后来甚至同时娶了两位妻子,组成了一个三人家庭,这在那个年代是件大逆不道的事,因此当薛定谔为了躲避纳粹而逃到牛津大学后,当地人不接受他,他只好又搬回了奥地利。
 ( 爱尔兰总理埃蒙· 德· 瓦莱拉 )
( 爱尔兰总理埃蒙· 德· 瓦莱拉 )
正在薛定谔走投无路时,爱尔兰总理埃蒙·德·瓦莱拉(Eamon de Valera)向他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在刚刚成立的都柏林高等学术研究所内组建一个理论物理系,并担任系主任。薛定谔接受了这个邀请,于1939年带着他的两名妻子搬到了都柏林。他在这里一直住到了1955年,甚至还加入了爱尔兰国籍。
瓦莱拉总理之所以这么做是有原因的。爱尔兰1922年刚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很多方面都落后于欧洲大陆的平均水平。瓦莱拉坚信,振兴爱尔兰,一定要优先发展科学,于是他拨出巨款资助爱尔兰的科研机构,薛定谔是他的科学救国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枚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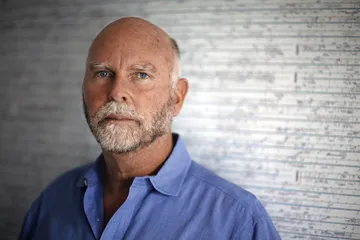 ( 克雷格·温特 )
( 克雷格·温特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薛定谔于1943年2月5日在都柏林著名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大讲堂举办了“生命是什么?”专题演讲。因为场地限制,只有400名听众到现场聆听,瓦莱拉不但亲自出席,还命令全体内阁成员都要参加。因为观众需求太过强烈,薛定谔不得不于2月12日和19日加了两场,同样场场爆满。第二年,他将讲稿编成同名小册子,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名叫《生命是什么?》的书迄今为止已经重印了20余次,简体中文版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被归为“第一推动丛书”系列。这个名字起得很恰当,因为这本书试图回答的就是生命的“第一推动力”问题。
在上世纪40年代,物理学和化学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们相信这个世界已经可以用简单的物理和化学定律来解释了,但只有生命是个例外,它似乎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很难用已知的物理化学定律来解释。于是不少人把希望寄托在了上帝身上,相信上帝赋予了生命“第一推动力”,这才把普通的无机物变成了神秘的生命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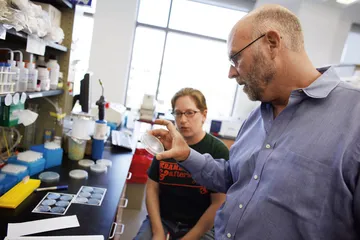 ( “塞莱拉基因组学”公司实验室 )
( “塞莱拉基因组学”公司实验室 )
薛定谔虽然出生在一个宗教家庭,但他是个无神论者,相信生命不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完全可以用物理化学定律来解释。他在该书第七章中举了一个工程师的例子解释了人们的困惑:
一位只熟悉热引擎的工程师在检查了一台电动机的构造以后,会发现它是按照他还没有掌握的原理在工作的。他会发现,过去很熟悉的制锅用的铜在这里却成了很长的铜丝绕成的线圈……他深信这是同样的铜和同样的铁……可是,构造的不同却让这些装置运用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做功方式。他是不会怀疑电动机是由幽灵驱动的,尽管它不用蒸汽只要按一下开关就运转起来。
因为专业的缘故,薛定谔在小册子中花了很多笔墨对生命的热力学性质做出了解释。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任何封闭系统的熵(Entropy,衡量体系混乱程度的物理概念)一定是在不断增加的,直到最后达到熵平衡态,成为一片死寂。但生命却很不一样,自诞生之日起,有机体的熵就一直在减小,看上去似乎违反了热力学定律。薛定谔则认为,生命体不是封闭系统,它通过从外界获得能量的方式维持自己的“负熵”状态,所以并不违反热力学定律。
值得一提的是,“负熵”这个概念在现代物理学中是和“信息”这个概念等价的,换句话说,薛定谔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通过消耗能量的方式维持信息的传递。
但是,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对遗传学的前瞻性描述。遗传学一直是生命科学最迷人的领域,一个细胞竟然携带着整个生命的全部遗传信息,看上去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薛定谔的时代,遗传学家们已经掌握了基本的遗传规律,有了基因的概念,而且知道染色体是基因的所在地,但对于遗传的发生机理仍然没有头绪,也没有意识到DNA才是遗传信息的载体。
1935年,有人用X射线照射果蝇,研究果蝇的突变率,算出基因大约有1000个原子那么大。这件事促使薛定谔考虑基因的物理化学性质,他得出的结论是,基因很可能是一种“非周期性晶体”。说它是晶体,因为基因携带的信息能够传递很多代不被损坏,说明基因分子一定是像晶体一般稳定;说它是非周期性的,是因为周期性物体太过简单了,只有非周期性的物体才能携带足够多的信息。
现在看来,薛定谔在这本书中提出的部分观点是不正确的,但这个“非周期性晶体”则是极富前瞻性的伟大预言,DNA正是这样一种非周期性晶体,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也正是得益于对DNA晶体的X光射线分析。而做出这个伟大发现的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都读过《生命是什么?》,两人都承认正是这本书让他们对分子生物学产生了兴趣,在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过程中也都受到这本书的很大启发。克里克甚至还亲自给薛定谔写了一封感谢信,并附上了论文原文,告诉他“非周期性晶体”的假说被证实了。
克里克已于2004年去世,沃森则不顾自己84岁的高龄,亲自到场旁听了克雷格·温特(Craig Venter)所作的演讲,题目就叫做“生命是什么?——二十一世纪的新观点”。
温特的演讲
薛定谔1943年的演讲3年后,也就是1946年,温特出生于美国犹他州首府盐湖城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他从小就非常贪玩,考试成绩大都是C和D,被诊断为患上了“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有趣的是,后来他用自己发明的方法测出了自己的基因组序列,发现了那个导致ADHD的基因缺陷。
虽然温特反对“越战”,可他还是被征兵去了越南,并被分配到了战地医院工作,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生命的脆弱。战争结束后他进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主修生物化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84年又转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担任研究员,主攻DNA测序技术。
到此时为止,温特和薛定谔的人生轨迹几乎毫无交集。但是两人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都有旺盛的好奇心和敢于冒险的精神。温特坚信生命的秘密就蕴藏在基因中,在NIH工作期间,他一直致力于完善一种俗称“鸟枪测序法”(Shotgun Sequencing)的DNA快速测序法,并打算申请一笔经费,用这个方法测出人类基因组全序列。但是当时主流生物界认为这个方法误差太大,无法满足科学家对测量结果精确度的要求,温特的申请被拒绝了。他一气之下干脆离开了NIH,于2008年自筹资金组建了“塞莱拉基因组学”(Celera Genomics)公司,试图凭借一己之力向政府研究机构发起挑战。
原来,美国能源部和卫生部于1990年共同投资30亿美元,揭开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序幕。但他们用的是传统测序方法,精度虽然高,但速度慢,价格高。温特和塞莱拉公司的技术人员改进了“鸟枪测序法”,大大提高了精确度,自信满满的温特于是决定独立进行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2011年,世界最著名的科学类期刊《自然》和《科学》几乎同时刊登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的消息,前者刊登的是“正规军”写的论文,后者则刊登了温特的结果,双方貌似打了个平手,但内行们都知道,这场看似实力悬殊的较量最后却以“弱者”获胜而收场。首先,双方的投资规模相差好几个数量级。其次,温特的“鸟枪法”如今已成为基因组测序的常规方法,“正规军”们使用的方法则被淘汰了。
首战告捷后,温特却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离开了塞莱拉公司,开始执行另一项“海洋微生物基因组普查”的宏大计划。温特认为,海洋微生物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远胜动植物,它们才是地球生物圈真正的主宰者,只有全面了解这些微生物的生活环境和生物特性,才能更好地保卫人类的家园。他和他的团队成员们乘坐自己的私人游艇环绕地球一周,搜集各地的海水标本,并将其中的微生物分离出来做基因组测序。该计划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地球生命基因库,为将来条件成熟后对这些未知生命进行功能性研究奠定基础。
以上这些事迹都是听众们耳熟能详的,温特只花了十几分钟一笔带过,将重点放到了“人造生命”的故事上。
海洋微生物基因组计划让温特对单细胞微生物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用生物化学的方法制造出一个全新的单细胞微生物。要想完成这个目标,最大的困难就是人工合成一条完整的DNA长链,并将其激活。为了证明这个思路是可行的,温特先在实验室里人工合成了一条噬菌体DNA链,再将其混入大肠杆菌培养液中。噬菌体就是专吃细菌的病毒,它们不能单独生活,而是依靠细菌宿主的细胞器复制自己,然后再杀死宿主,继续转播。温特的这个噬菌体实验很容易获得了成功,进入细菌身体后的人工合成噬菌体DNA就像一个活病毒,成功地绑架了该细菌,将其变成了自己的繁殖工具,组装出成千上万的新噬菌体。
但是,噬菌体毕竟是一种不能独立生活的病毒,除了DNA外就是一点蛋白质外壳而已,合成起来不难。真正的困难在于人工制造一个能够独立生活的细菌,有两个巨大的障碍横在温特的面前,第一是如何能在实验室里人工合成出细菌的全套染色体DNA,第二就是如何“激活”这条DNA长链,使之完成从“死的”有机大分子到“活的”生命之间的转换。
为了攻克第一关,温特决定从一种支原体开始做起。这种支原体的基因组是已知单细胞生命中最小的,只有58万个碱基。即使如此,仅凭目前的DNA合成技术要想合成出整条DNA长链也是非常困难的。科学家们采用了一种变通方法,先合成一段段大约6000个碱基长的DNA片段,然后将其导入酵母菌,利用酵母菌自带的基因重组功能将这些片段分步连接起来。经过4次组装,终于得到了一条完整的DNA长链。
第二关更难一些,攻关过程中遇到过两次大的麻烦。第一次的原因较为简单,合成的DNA片段少了一个碱基,于是后面的阅读顺序就都错了一位,肯定乱套了。但是,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新的DNA长链还是没能被“激活”,经过两年的不断试验后,科学家们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支原体DNA上带有特殊的甲基化标记物,它们就像识别装置,可以防止外来DNA前来捣乱。解决了这个问题后,合成DNA终于顺利地被激活了。而被转入了新DNA的支原体细胞顺利地接受了新的指令,变成了另一个全新的物种。
接下来,温特做了一件大概只有他才会做的事情:他设计了一套密码,将从事这项研究的主要工作人员的名字转换成相应的碱基顺序,装进了这个人造生命的基因组内。这就相当于给这个新生命加上了水印,从此这个新物种便永久性地带上了温特的烙印。这个做法有点嚣张,不少人怀疑温特想扮演上帝的角色,还有人担心人造生命会带来伦理问题。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温特用另一个水印圆满地为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解释。他把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的一句名言加进了新生命的基因组当中:
对于我不能制造的东西,我就无法去了解。
原来,温特的真正目的就是想通过制造生命来了解生命的奥秘。
2009年8月20日出版的《科学》杂志首先报道了这一成果,西方媒体称其为“人造生命”,其实仅就这篇论文看,这个支原体还远没有达到人造生命的水平。首先,温特必须借助酵母菌来完成人造DNA最后的组装,严格说这还不能完全算是人造生命。其次,温特必须借助现有细胞内的细胞器来给新的基因注入活力,这就相当于给一台电脑换了软件,使之成为一台新电脑,但电脑硬件毕竟不能算是人造的。针对部分媒体的质疑,温特解释说,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他手下的科学家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实验,争取尽快解决这两个难题,彻底摆脱酵母菌的帮助,制造出真正的人造生命。
但是,这个实验最大的意义在于,温特彻底回答了薛定谔当年提出的问题,那就是生命只不过是一个被DNA控制的机械装置而已,不需要特别的“灵魂”就能运转起来。在温特看来,生命就是一个精巧的图灵机,每个生命体都自带一套完整的,能够用来复制自己的图纸。这台机器的部件是由蛋白质和RNA制成的,它们的任务就是按照DNA图纸提供的信息,组装成一个个新的机器,并在此过程中把DNA携带的信息传递下去。
当然了,温特这么做也不光是为了解开生命的秘密,他还有一些更为实际的想法。2005年,他和别人合伙成立了“合成基因组学”公司(Synthetic Genomics),致力于开发人造微生物,用于生产清洁能源。后来他又将目标扩展到利用人造微生物为人类提供廉价食品和新材料,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大幅度提高效率而又不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伤害。
在演讲的最后,温特向大家预告了一项新成果的诞生。几天后,这篇论文果然出现在7月20日出版的《细胞》(Cell)杂志封面上。美国斯坦福大学马库斯·柯沃特(Markus Covert)博士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用一组计算机完全模拟了生殖支原体(Mycoplasma genitalium)的生命!这是一种人体寄生虫,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基因数量最小的单细胞生命。它只有525个基因,相比之下,生物研究最常用的大肠杆菌有4288个基因,算是庞然大物了。
柯沃特教授把这525个基因以及相应的细胞器的功能完全数字化,让计算机对这些基因的功能及其相互作用进行模拟,这就等于在计算机里给这个细胞做了一个备份,真实世界里的细胞行为完全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重复出来。事实上,关于生殖支原体的性质已经有过很多研究,柯沃特在计算机上模拟了这些研究,得出的结果和真实的实验结果完全吻合。
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再次证明,生命的本质就是信息。薛定谔的预言终于得到了证实——生命的本质就是信息,它通过消耗能量的方式来维持信息的传递。
这项研究不光具有哲学意义,还有很强的实用性。比如,今后关于生殖支原体的研究可以不用在实验室里做了,直接在计算机上模拟就可以了。温特预言,数字化生物学将为医学带来新的革命。比如,某地发现一种新的流感,科学家可以在当地测出流感病毒的基因顺序并传给远方的计算机,然后计算机对该顺序进行模拟,就可以计算出疫苗的结构。然后计算机再将新疫苗的信息传回当地,这样当地医院就可以迅速制造出新疫苗,将流感病毒杀死在摇篮里。
“生命就是一台计算机,未来的生物学,将以光的速度前进。”温特总结道。
(感谢德国罗伯特博士基金会对本文的帮助) 计算机科学科普基因合成薛定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