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我们的体外大脑
作者:曹玲 ( 尼古拉斯·卡尔 )
( 尼古拉斯·卡尔 )
有问题找谷歌
3年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作家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的一篇文章《Google让我们愈变愈笨?》。
卡尔生于1959年,是位专注于技术、商业和文化领域的作家,对互联网持一种批判甚至悲观的态度。他的书《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The Shallows: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曾入围2011年普利策非小说奖决赛,不过最后败给了医学作品《疾病之王:癌症传》。
卡尔认为,网络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媒体,就像是运送绝大多数信息的一个管道,这些信息经由我的眼睛和耳朵,进入我的大脑。网络提供思想内容,但同时也塑造思维模式,网络正在削弱我们的专注力和思维能力。
他在《Google让我们愈变愈笨?》一文中写道:“现在,我的大脑在获取信息时,正在按照网络传播信息的方式来进行:快速移动,像粒子流一样。过去我像个潜水者一样,在文字的海洋里潜游,而现在我就像一个骑着摩托艇的家伙,在海面上呼啸着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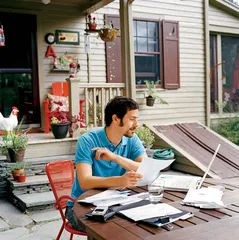
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互联网对记忆和认知的影响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今年7月14日,一篇发表在《科学》杂志在线版上的文章说,便利的搜索引擎真的能改变我们的记忆和回忆方式,但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文章的第一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系的助理教授贝特西·斯帕罗(Betsy Sparrow)。起因是有天晚上,她和丈夫一起看一部老电影,有个女演员明明见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在哪儿。于是她登录互联网电影资料库(IMDB),输入电影名称,查找女演员,查出她还演了哪些电影。之后,斯帕罗开始和丈夫讨论,在那些没有智能手机和电脑互联网的年代,人们想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怎么办。他们回忆起以往如何找人请教,如何查询书籍,回忆越多,斯帕罗萌生出越多问题。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斯帕罗找她的导师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瓦格纳(Daniel M.Wegner)讨论起来。
瓦格纳教授有一个在心理学上非常有名的“白熊实验”,参加实验的人在观看白熊影片后,你越是不让他想白熊,一年后他对白熊影片的记忆就越深。这个实验凸显了“想要抑制想法,反而会让人更执著于这个想法”的观点。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关于“交互记忆”的理论。“我们都有外部记忆装置,放在别人脑子里。我们大概知道别人知道什么,如果我们想知道确切的事情就去问他们。比如,我丈夫知道关于棒球的一切,如果我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就去问他。正是因为我知道他知道这些,所以我自己就不会再去记这些事。”斯帕罗解释道。
她和瓦格纳讨论出两个需要证实的问题:“第一,当我们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时,是否立刻会想到互联网?这是不是一件不假思索的事?第二,我们是会记住检索出来的答案,还是让它继续留在网上?如果我们查找问题却不会刻意记住它们,是否因为我们知道总能获取它们?”
为了证实这些问题,斯帕罗做了几个实验。其中一个实验她和同事们要求一组哈佛大学学生回答一些琐碎的难题,例如“鸵鸟的眼睛是否比它们的大脑大?”答案为“是”或“否”。在此过程中,不允许学生使用互联网。之后,他们利用心理学家推崇的“斯特鲁普效应”对学生进行分析。所谓斯特鲁普效应,举个例子来说,把“红色”两个字涂上黄色,“黄色”两个字涂上绿色,“绿色”两个字涂上红色,然后读这几个字,读字的速度会立刻变慢,这就是斯特鲁普效应,由美国心理学家斯特鲁普(John Ridley Stroop)于1935年发现。
在这个实验中,人们接受了两种刺激——词义和书写它的颜色,大脑对这两种信息的加工有所不同。当两种信息同时输入时,只对一个信息加工而对另外一个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由于对文字的加工比较容易,所以大脑首先会对文字做出反应,但是文字的颜色与大脑贮存的文字资料并不相符,这时大脑就必须用一段时间来思考才行。在斯帕罗的实验中,如果参与者最近曾使用过某个单词或者对他们比较重要,就会妨碍他们判断单词的颜色,用时也更长一些。
在斯特鲁普测试中,研究人员使用的单词“Yahoo”和“Google”,与消费品牌“Target”(美国塔吉特百货公司)和“Nike”相比,学生们处理前者用时更长。斯帕罗说,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这些学生的大脑中会蹦出“谷歌一下”的想法。“当你不知道答案的时候,你立刻会出现‘我的电脑呢?我能搜索一下答案吗?’的想法。”
是居安思危还是杞人忧天?
另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让参与者在电脑上录入40份声明,同时要求一半参与者在完成之后保存这些信息,另一半参与者则被要求删除。录入结束后,所有参与者均被要求尽可能回忆并写下这些声明。研究人员发现,要求删除的参与者回想起的声明数量远远超过要求保存的人。斯帕罗说:“如果参与者认为能够查询已经保存的声明,他们就没有必要自己记住它。”
“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的交互记忆,成为我们记忆的外部储存方式。”她说,“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伟大的朋友。比如你的Word文档打不开了,怎么办?以往你只能等懂行的人来帮你,现在你可以上网搜索你遇到的问题,总会有人回答过类似的问题,然后你自己就能解决问题。交互记忆存储的地方,无论是人还是电脑,我们都知道去哪里找它,所以,更重要的事情已经不是我们自己记住事情,而是知道去哪里找它。比如我就不记得很多电话号码,我不觉得记住它们有什么价值。我也不认为我们丧失了某些技能——我们大脑的某个部位并没有萎缩,只是我们不需要这样做了。”
一些人持有同样的看法。《连线》杂志观察家克莱夫·汤普森(Clive Thompson)把互联网称为“体外大脑”,说它正在接替以前由体内记忆扮演的角色。“把数据任务交给硅晶体,我们可以解放自己的大脑,让其执行急中生智、奇思妙想之类更加‘人性化’的任务。”《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写道:“我过去认为信息时代的魅力就是允许我们知道得更多,可是后来我认识到,信息时代的魅力是允许我们知道得更少。它为我们提供了‘外部认知奴仆’——半导体存储系统、网上协作过滤功能、消费者偏好分析算法、联网知识系统。我们可以让这些‘奴仆’挑起重担,而把自己解放出来。”
但有一些人不赞同如此观点。美国神经学家加里·斯摩(Gary Small)认为:“在每天与高科技发明打交道的过程中,会改变大脑细胞并且释放神经传递素,由此一来,人脑中新的神经线路会日益加强,而旧的则逐渐衰退。”他将其称为一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的“进化过程”。
持此观点的著名人物还有英国神经科学家苏珊·格林菲尔德(Susan Greenfield),她是英国皇家学会首位女理事。她称“Twitter”、“脸谱”(Facebook)和“虚拟人生”(Second Life)之类的社交网站“改变了人类思维方式”,花大量时间与屏幕互动的人情感会变得冷漠,他们视生命为一系列需要立即反应的逻辑任务,语言能力、想象力和分析力都被削弱,注意力缩短,对儿童大脑造成永久损伤。这些观点虽然大胆,但却缺乏研究数据的支持,有人认为格林菲尔德应该通过撰写和发表具有严谨科学数据的研究论文来表达她的观点,而不应利用媒体作为平台来渲染她关于“技术邪恶性”的假设。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间内,记忆都是神圣的。对古希腊人而言,记忆是一位女神:摩涅莫辛涅,她是缪斯的母亲。在奥古斯丁看来,记忆是“宏大而无尽的奥秘”,是上帝之力在人身上的反映。如今,记忆丧失了神性,记忆女神变成了一台机器,一些人难免悲观。
“在某方面人们会担心它,但是我觉得互联网和我们一直以来的情况没什么不同——它所做的事情就是以往其他人承担的工作。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互联网更适合成为交互记忆的载体,我们不用担心它会和我们分离,它会没用了或者换工作了,这是以往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没必要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斯帕罗说。
当年,苏格拉底对“写作会让记忆衰退”忧心忡忡,这是一种永恒的担忧,用意大利学者和小说家翁贝托·艾柯的说法就是:“新的技术成就总是会废除或毁坏一些我们认为珍贵、有益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价值,而且它们还具有深层的精神价值。”事实证明,对记忆丧失的担忧完全是杞人忧天,书籍“挑战并改进了记忆,它们并没有弱化记忆”。
“如果有一天互联网没有了,我们又会像以往一样记事。”斯帕罗说,“我觉得人类很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进化出一个不同的大脑。我在学校里教一个很大的班级,如今的互联网一代仍有很好的记忆习惯和能力。”■
(文 / 曹玲) 互联网体外大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