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好生活
作者:薛巍
幸福能否量化?
英国国家统计局问卷调查中的4个问题是:你昨天觉得有多快乐,你昨天觉得有多焦虑,你现在对你的生活是否满足,你觉得你做的事情有多值得?华威大学的幸福经济学专家安德鲁·奥斯瓦尔德说,应该补充两个问题:你的睡眠好不好,你觉得你的时间是否紧张?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杰·科恩说:“试着计算社会的幸福程度而不是增长率和生产率已经变得很急迫。当西方工业化社会开始测算国民生产总值时,很多人还面临生存问题。现在大部分人都丰衣足食了,但不知他们的感觉如何……美国宪法中说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注意这里的差别,这显示了美国立国者们的智慧。独立宣言保障自由,但说到幸福,只说对幸福的追求是权利。也许,现在该看看这种追求实现得如何了。”
英国作家娜塔莉·海恩斯则认为幸福指数调查毫无必要:“政府如果真的想知道什么使人们感到更幸福或更焦虑,他们不需要做调查。他们只需要同情心。当我们看到一家银行宣布一年亏损了10亿元,但同时给它的员工发了10亿元奖金,这会降低我们的幸福。有报道说我们地方的医院、图书馆或学校的经费将会被削减,我们也会感到幸福减少了。”
英国政府要统计国民的幸福程度,但幸福无法计算,这并非因为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一种心理状态。1974年,美国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写道:“假定有一个体验机器可以给你任何你想得到的体验。神经心理学家可以刺激你的大脑,让你觉得自己在写一部伟大的小说,或者在交朋友、读一本有趣的书。其间你浮在水箱里,头上插着电线。你会一辈子跟这台机器接在一起吗?在水箱中时,你不会知道你是在那里,你会以为那都是在真实发生的。你愿意吗?”这个思想实验说明,幸福不是一种精神状态。很多人都会拒绝接上那台机器,因为我们相信那不是真的幸福;写一部伟大的小说跟拥有写一部伟大小说的体验是不同的,“如果只是要得到幸福感,往自来水里加药就行了”。
 ( 《什么是好生活》 )
( 《什么是好生活》 )
按照功利主义理论,任何行为的道德价值要按照它带来的幸福的数量来计算。但即使对这些思想家来说,幸福问题也不只是幸福的多少的问题。密尔明确地认识到了幸福质的差别:他认为听歌剧或读弥尔顿的快感比享受美食更高级。他有一句名言:“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作一头满足的猪更好。”人生的道德价值在于能被更多、更深刻的经历打动的能力。这包括遭受痛苦的能力。
英国哲学家边沁和密尔的批评者们经常谈起计算幸福的实际困难。早在功利主义兴起之前,一些困难就已经被指出来了。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人的人生目标是幸福。我们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我们的心灵,最快乐的人就应该是以最出色的方式施展心灵的人。幸福源自好的习惯,深刻的幸福概念是长期的自我实现,而不是转瞬即逝的快乐,前者很难甚至无法通过“你昨天觉得有多快乐”来加以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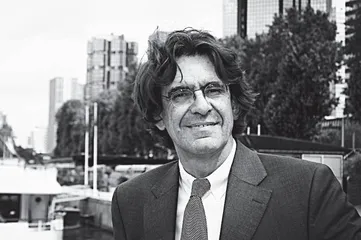 ( 吕克·费希 )
( 吕克·费希 )
亚里士多德还认识到,伦理学跟哲学的其他分支不同,它不是一门准确的科学。在18世纪,康德强调了这一点:我们当然都希望得到幸福,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也不知道如何得到它。追求过某种东西并希望它让自己快乐的人最后都感到失望,那甚至成了压力和焦虑之源。
在英国哲学家朱利安·巴吉尼看来,英国政府真正关心的并非国民是否幸福,仍然是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英国政府之所以转而关心国民的心理健康状况,是由于受到了心理学家理查德·莱亚德的积极心理学的推动。该学派强调心理健康跟身体健康一样重要。西方社会已经产生了心理治疗文化,过去不满会让人谋求改变,现在不满被认为需要接受心理治疗。“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工人跟他们的劳动之间产生了异化,因为他们不能得到产品带来的利润,声称自己很快乐的工人遭受到了虚假意识的困扰。积极心理学让工人无视他们自己不幸的状态,有理由担心政府是想用心理治疗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心理学家说,估计精神疾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770亿英镑左右,心理学干预的结果会是公民们把问题看做个人对环境做出了不当反应,而不是环境本身不公正。”
什么是好生活?
在西方古代哲学传统中,对最美好的生活的思考几乎都承认我们都追求幸福。哲学家们经常把人类的幸福当做判断善与对的重要标准。道德标准告诉我们该如何对待他人,伦理标准告诉我们该如何生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努力证明,荣誉、责任、公正等美德跟幸福的伦理理想是相关的,遵守道德会让我们感到幸福。但如法国哲学家吕克·费希在《什么是好生活》一书中所说:“你赞成还是反对幸福?这个问题看上去很荒谬,但是两年多来现代哲学饱受其折磨。从康德到尼采和弗洛伊德一脉相承,都认为幸福是一个模糊和天真的概念,这些哲学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对幸福的概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批评。”在尼采看来,好生活是一种最强烈的生活,因为它最和谐;它是最优雅的生活(说它优雅是因为这种生活中没有无用的弯路,不会浪费能量)。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生活中,这些重要的力量之间不是相互矛盾、分裂和竞争,从而相互妨碍或消耗,而是开始合作,把优先权交给积极的力量。
尼采说:“唯一可能的生活在于艺术,否则人们就远离生活了。”美国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在新著《刺猬的正义》一书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人们经常把生活和艺术做类比,这种做法经常受到嘲笑。浪漫主义者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生活过成一件艺术品,我们现在怀疑这种类比,因为它听起来太唯美了,就好像我们应该在生活中追求一幅画的价值——良好的感受性或者复杂的组织形式。但因此指责这种类比并不恰当,它类比的是作品的价值和创造行为的价值。”
我们推崇伟大的艺术品主要不是因为艺术品能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而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表现,迎接艺术上的挑战。我们推崇美满的生活,因为它们也体现了一种表现:迎接一个人生要过这一挑战。“我们的人生的最终价值是副词,不是形容词——是一个我们怎样活过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用于最终结果的标签。人生的价值在于表现,而不是抽走表现后剩下的东西。人生的价值是记忆变淡、涟漪消失后仍在心头的杰出的舞蹈或俯冲。”
某物的产品价值是它作为物品的价值,独立于它被创造的过程。一幅画也许拥有产品价值,这可能是主观的或客观的。它形式上的安排也许很漂亮,赋予了它客观价值;它也许让观看者感到愉悦,受到藏家的青睐,就赋予了它主观价值。这幅画完美的机械复制品有着同样的美。它是否具有同样的主观价值取决于别人是否知道它是复制品。对于那些以为它是原作的人来说,它跟原作有着相同的主观价值。但原作有着复制品所没有的客观价值,它是具有表现价值的创造行为制作出来的,它是一位有意要创作艺术品的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之所以美是因为它是杰出表现的结果,复制品就没有这么杰出。
过去流行嘲笑抽象艺术,说黑猩猩也能画出来,人们曾经猜想,10亿只类人猿随机打字能不能打出一部《李尔王》来。如果一头黑猩猩碰巧能画出《蓝枝》或打出《李尔王》,这两部作品无疑会有很大的主观价值。很多人都会想拥有或看到它们。但它们没有一点表现价值。表现价值也许独立于任何物体而存在。一幅名画被毁坏后没有余下任何产品价值,但它被创造出来这一事实仍在,它的表现价值也还在。
德沃金说:“如果想让人生有意义、说得通,我们就必须采纳浪漫主义者的类比。”我们觉得,说一位艺术家赋予了他的原材料意义、一位钢琴家给了他演奏的曲子新的意义很自然。我们可以把完美的人生理解为赋予人生伦理意义,这是唯一能够承受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的人生意义。“当你做一些小事时做得很好——弹一首曲子、扮演一个角色、玩一手牌、投一只球、说两句好听的,做一把椅子、写一首诗,你的满意自身很完整。这些是人生中的成就。为什么整个人生不能完整的是一种成就,活着时表现出了自己的价值?”■
(文 / 薛巍)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