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斯塔科维奇:别把我忘了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 (法新社供图)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 (法新社供图)
文/lafuenty
友谊的和声
肖斯塔科维奇在口述自传《见证》中几乎从未对访谈者伏尔科夫提起过伊萨克·格利克曼。当他谈论自己的创作与生活时,多是在谈论同时代的音乐家、评论家,以及那些钳制他生活的当权者。
这也许是伏尔科夫的谈话方式造成的。由于肖斯塔科维奇谨慎内敛的个性,伏尔科夫不得不旁敲侧击地从谈论其他音乐家同行开始,以此不经意地引出对其自身的返照。如伏尔科夫所说,《见证》的表达方式像彼得堡这座城市一样,由水中倒映的影像构成。
与此相对,与肖斯塔科维奇保持了40余年友谊的格利克曼保存的书信,因其坚实的真实性更显得稀有而珍贵。如果说透过自传看肖斯塔科维奇像是看“转播”,其中不免夹杂对个人历史的重构、修正和补充,那么信件则可理解为一种相对无意识的“直播”。
与肖斯塔科维奇在《见证》中提起的那些同时代人相比,格利克曼在列宁格勒文化圈中的确不算个特别出众的人物。
1931年秋天,经肖斯塔科维奇的密友索列尔金斯基介绍,崭露头角的戏剧和音乐评论家格利克曼与作曲家在列宁格勒爱乐乐团正式结识。他们的友谊升华于一次肖斯塔科维奇的专场音乐会后,参与了筹备工作的格利克曼受邀在演出后去肖斯塔科维奇家参加午宴。聚会散场时,肖斯塔科维奇对格利克曼说,“别把我忘了”。这成为后来两人通信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
此后格利克曼担任乐团大众文化部主任,进而成为肖斯塔科维奇的秘书。1941年战争席卷列宁格勒后,格利克曼被疏散到塔什干,肖斯塔科维奇则被疏散到古比雪夫(今俄罗斯萨马拉),这也是这本书信集的时间起点。
格利克曼的书信集收集了两人从1941年到1974年作家去世前一年为止的近300封信件。遗憾的是,30年代两人间的信件全部遗失,且由于肖斯塔科维奇没有保存信件的习惯,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单向的独白过程,辅以格利克曼的注释,形成一种独特的跨时空和声体。
肖斯塔科维奇对格利克曼的看重也许令人意外,但书信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段友谊不是格利克曼的一厢情愿。“不要忘记我”——肖斯塔科维奇的信件中反复透露出这样的讯息,“只要我手边有信封和信纸,我随时可以给你写信。”“我非常想念你,为什么最近一直没有给我来信?”“期待着你的来信,快给我回信吧!”
如果想要获得肖斯塔科维奇那对始终抿紧的、薄薄的嘴唇后面的真实话语,他在那些伟大作品之外的挂念与忧思,阅读这些书信是一条宝贵的途径。
“面包、黄油、半公斤、伏特加……”
在这些书信之外,我们可能很难再见到肖斯塔科维奇本人对于自身困窘生活的详细描述。
肖斯塔科维奇的性格决定了他将大多数精力放在艺术创作上,另一部分精力则用于应对当权者带来的恐惧和压力(如口述自传《见证》)。物质方面他鲜少开口求助,而面对自己过去的得力助手、最为信任的同事格利克曼,肖斯塔科维奇难得地常常写到自己勉强支撑的生活,还时不时向好友求助。
因此阅读这本《书信集》时可能产生一些矛盾的感觉。格利克曼在前言、日记和注释中始终要将肖斯塔科维奇捧上伟人的神坛,随时称赞其高尚光辉的品质;而肖斯塔科维奇在信件中反而时常流露的是真实而脆弱的一面。
据格利克曼所写,肖斯塔科维奇从不参与家人关于日常生活的谈话,“他与这种谈话无关”,但他又无法不为生活担忧,以至于他在信件中打趣地写,“每当我听他们谈话时,总会忘记其中的很多内容,但是有这么几个词我却记得十分清楚:面包、黄油、半公斤、伏特加、200克、通行证、点心等等”。
1942年2月,刚刚到达古比雪夫的肖斯塔科维奇直接写道:“我现在的生活很糟糕。”肖斯塔科维奇为远在列宁格勒的母亲和姐姐忧心,古比雪夫的冬天漫长而残酷,气温达到零下45摄氏度,房间里冷得要命,孩子不断生病。几位作曲家相继去世的消息传来,让他心情低落,而最严重的问题是“保证让刚刚到达的亲戚们吃饱、穿暖,并为他们治病”。
肖斯塔科维奇非常依赖与格利克曼的沟通,他常在信件末尾写“请经常来信,我过些日子再给你打电话”,也常常设身处地地为这位老友的生活担忧,给他寄去钱和咖啡,帮他探听亲人的消息。
这种羁绊根植于他们在列宁格勒共有的友人和共同度过的时光中。在战争的几年里,两人都不断失去共同的朋友,逝者简化成了信件中的一个个名字,一笔带过。即使悲伤,肖斯塔科维奇也是极其克制的。
介绍他们相识的索列尔金斯基于1944年2月11日去世,这个消息给已经习惯了失去亲人朋友的肖斯塔科维奇仍造成极大的撼动。他给格利克曼写信,约定在3月11日在塔什干和莫斯科分别遥干一杯伏特加,纪念老友去世一个月。格利克曼在注释里写,他遵守了约定,好不容易地搞到了一大杯当时十分紧缺的伏特加。
但在苦难之外,肖斯塔科维奇也在信中展露出富有情趣的一面。1942年,他甚至随信给格利克曼寄去一张喀山足球赛的节目单,通报了比赛结果。两人在列宁格勒总是一起看球赛。他在信中花了老大的篇幅回忆起一次他打电话给格利克曼转述球赛的经历,甚至能记得具体的球赛日期、球队名字、比分和进球的实况——那是对旧日列宁格勒生活的深深眷恋。但肖斯塔科维奇至死也没能回到列宁格勒,葬在了莫斯科。
也正是在这些琐碎的困苦包围下,肖斯塔科维奇作为艺术家的伟大之处才被反衬得更为清晰。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日,他也持续汇报着自己的创作进展和新构思,想尽办法要把刚创作出来的曲目弹给格利克曼听。如他在给格利克曼的信中所写的:“如果有一天,我的双手被砍断,我还可以用牙齿咬住笔继续谱写音乐。”
言外之意
格利克曼的注释事无巨细,篇幅常常超过信件本身。我们已经无从知晓这些注脚的准确性,但它们毫无疑问构成了这部《书信集》特殊生命力的一部分。
一些极度微小但富有深意的生活痕迹留在了信件中,被格利克曼仔细挑拣出来。肖斯塔科维奇提到自己去检查血象,说女大夫季莫舒克长得像契诃夫小说《正剧》中描写的戏剧家穆拉什金娜。格利克曼特别指出,这位女大夫在斯大林时代挑起过“克里姆林宫医生事件”。
一些罕见的情绪也只有在信件中流露。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创作的肖斯塔科维奇,在信中袒露自己的创作困境,“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好像再也不能谱曲了,似乎一个音符也写不出来了”。格利克曼在注解中解释了作曲家的这种性格——创作上哪怕很短暂的停顿都会引起他的惊恐,尽管在写这封信之前他刚刚创作出了《钢琴三重奏》。
最重要的是,为了躲避审查(在这些信封和明信片上,常盖有“通过军事检察”的邮戳),肖斯塔科维奇常用难以被察觉的反语和黑色幽默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些潜台词只有通过格利克曼的注释才能完全理解。
“‘直接违背’的描写方法在我俩之间的谈话和书信中也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特殊的经过句往往使我从直接对立的语言中体味出真理。”比如肖斯塔科维奇写一句“美丽的列宁格勒,我们将要在这座象征着苏联体制和斯大林战略的城市里生活”,格利克曼立马就能体味出这是与其真实思想绝对对立的广为流传的套话,背后是冷嘲热讽的潜台词。
一种有趣的阅读方式,是将这部《书信集》与伏努科夫写的肖斯塔科维奇口述自传《见证》对比阅读。《见证》是一本可靠性受争议的传记,而《书信集》则是实打实的一手材料。二者结合,往往能拼凑出一个更接近真实的答案。
比如《第七交响曲》的主题问题。《见证》中的肖斯塔科维奇极其反感当局出于宣传目的将这部作品与战争联系起来,声明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侵略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但在格利克曼的笔记中,肖斯塔科维奇却明确表示《第七交响曲》与当时的战争相关,“我所看到的战争就是这样”。我同意译者在后记中的推测,作品的构思初衷在战争之前,但战争到来时作品还未写完,肖斯塔科维奇最终将战争背景融入了交响曲的主题。
肖斯塔科维奇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74年8月。他对格利克曼兴奋地列举了近日的创作计划,说读了一些米开朗琪罗的十四行诗,想运用在自己的套曲创作中,并标注出诗歌的页码和标号,请格利克曼去图书馆翻阅。
此后他们还有过几次通话和会面,但1975年6月以后肖斯塔科维奇再也没来过电话;8月9日,肖斯塔科维奇去世,格利克曼感觉自己“一下子变成了永久的孤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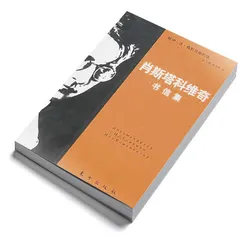 《肖斯塔科维奇书信集》
《肖斯塔科维奇书信集》
作者:[俄]格利克曼 编
译者:焦东建、董茉莉
东方出版社2005
| 推荐阅读
《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 [俄]肖斯塔科维奇口述、 [美]所罗门·伏尔科夫整理,叶琼芳译,作家出版社2015 列宁格勒阅读肖斯塔科维奇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