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撤军路
作者:卜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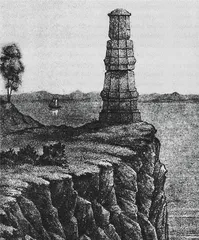 穆拉维约夫曾亲自率领第一、第二次航行黑龙江,主要是为了运送部队,前往下江地区、鞑靼海峡甚至堪察加半岛,去与英法联军作战。现在签订了《巴黎和约》,交战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他就下令撤回在那里的一些部队。1856年3月21日,撤军命令从彼得堡发往伊尔库次克:“鉴于合约已经签订,须将驻守阿穆尔河口和正调往该地的步兵,除出第十五边防营外,全部撤到阿穆尔上游。”穆督办事精细,遥令撤回部队分作三批,指定各批次带队军官,叮嘱他们多带食物,尽早登程。他把第三次航行黑龙江与撤军相衔接,要求船队一到马林斯克哨所,第一批撤离的部队立刻返回。他还希望刚刚在美国购买的“亚美利加”号轻巡航战船发挥机动作用,能将大部分官兵运至俄境,至少送到瑷珲一带。
穆拉维约夫曾亲自率领第一、第二次航行黑龙江,主要是为了运送部队,前往下江地区、鞑靼海峡甚至堪察加半岛,去与英法联军作战。现在签订了《巴黎和约》,交战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他就下令撤回在那里的一些部队。1856年3月21日,撤军命令从彼得堡发往伊尔库次克:“鉴于合约已经签订,须将驻守阿穆尔河口和正调往该地的步兵,除出第十五边防营外,全部撤到阿穆尔上游。”穆督办事精细,遥令撤回部队分作三批,指定各批次带队军官,叮嘱他们多带食物,尽早登程。他把第三次航行黑龙江与撤军相衔接,要求船队一到马林斯克哨所,第一批撤离的部队立刻返回。他还希望刚刚在美国购买的“亚美利加”号轻巡航战船发挥机动作用,能将大部分官兵运至俄境,至少送到瑷珲一带。
上溯黑龙江的旅程是凶险的。从马林斯克到乌斯特哨所大约4600里,两岸多数地方荒无人烟,没有住房,也很难找到食物。前面已写过普提雅廷在瑷珲被流冰阻住,吃尽苦头才得以返回俄境,乃至于回到彼得堡后,到处散布黑龙江是一条无用之河。同样的例子,还有一个考察队长马克,也是在去年沿江返回时遇到流冰,得到清朝官兵救助,安排他们在瑷珲住下,尽管有严密监看,还是偷画了一张详细的城区图。
撤回部队也抓得很紧。第一批部队在谢斯拉文中校率领下,6月中旬即从马林斯克起行。穆督所期待的“亚美利加”汽轮尚未抵达,他们从费雅喀人那里买了大小船只,尽量多装粮食,顺风时张帆,逆风时拉纤或划桨,开始阶段行进颇速。待到黑龙江中游,河水大涨,江面加宽,根本无法拉纤,逆水顶风而划,战士累得精疲力竭,也走不了多远。更要命的是会偏离主航道,沿着支流艰辛走出数十里,发现后再折返,沮丧至极。行至上游江段,热病开始在军中蔓延,按天配发的粮食由于时间拉长远不够吃,个别军官和士兵死去,总算在9月底前后进入俄罗斯境内。
第二批是由亚兹科夫率领的八百多人,在两个周之后动身,也是利用费雅喀人所造小船作为交通工具,一路遭遇了更多艰难,接近俄国边境时闹起饥荒,不少人死于途中,但仍在冰期之前抵达俄境。关于这一批的死亡人数,《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五十三章说是“死于各种疾病的共五十二人”,很忌讳提起饿死;而《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则说因饥饿引发疾病和死亡,“损失了九十六人”。
最惨的是第三批,由当年押运物资到马林斯克的第十三边防营营长奥别列乌霍夫中校带队,7月底才启程,至上游已是隆冬。《外贝加尔的哥萨克》描写了那次死亡行军:“他们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行军,一直在野地里,在篝火旁边扒开雪露宿,衣服都穿坏了……疲惫不堪的士兵,拒绝前进,躺下来等死……在阿穆尔河的一个岛上,找到了七个精疲力尽的和三个饿死的士兵。部队在继续前进途中,于11月13日遇上了第一梯队二十六个掉队的人,其中八个人已饿死了。11月14日再一次遇上了六人,11月15日又遇上了六人,其中一人已经死了……”让他们略感庆幸的是,春天顺江而下的时候,曾有一只满载面粉的船在雅克萨附近搁浅,士兵们找到了这艘船,得以饱餐一顿。而一个亲历者却说了这样的话:
在阿尔巴津下头靠近面粉驳船搁浅的地方有一些尸体,据普列舍彭科说,饥饿的士兵是由于拼命吃面粉而死去的。在驳船下游我们看到惊心动魄的情景:饥饿的士兵只穿戴大衣和帽子。在严寒中(零下35摄氏度或零下47华氏度)走过,半死不活,被烟熏黑和动画的形象,使人辨认不出他们。
此人叫罗曼·博格丹诺夫,当时是驻扎边境哨所的士兵,受命前往接应和救援,一路遇到的都是此类惨象,而最惨的还在后面:
在今天瓦甘诺夫斯基邮站下面的一个岛上,有很多尸体,其位置各有不同,人们一定会设想到,他们多半是饿死的。有的尸体的臀部被割掉。在这个岛上,我们发现二十个或者二十五个活下来的士兵,他们因为没有靴子或其他原因不能继续前进,并在等死。
第三批撤回俄军总共379人,死亡102人,若非从俄境内派来救援人员,这个数字还会大大增加。
对于俄国人在黑龙江航行,大清朝廷与边镇似乎达成一种默契,那就是不允许、不阻拦。体现主权在我的,是几处江卡的登船查验制度,详细记录士兵、移民、妇女小孩的数量,也记录军械物资甚至牛马之数。当然不让上船也不硬上,就简单记一下大船若干、小船几只。1856年的黑龙江一派繁忙,既有由西向东的沙俄船队,又有自下而上的回撤哥萨克,吉林将军景淳、黑龙江将军奕山奏报了经过所辖江卡的情景:
八月初四日,有俄夷二十人,分驾小船出黑河口,顺流下往;初五日,又有三百八十余人,分驾中船二十六只,自下游驶入黑河口,向上回行;又霍尔托库地方占居夷人,于八月十二日,自行焚拆房四所,仅留数人,外有二十六人,分驾威弧(即独木舟)三面,驶入黑河口;同日又有二百九十余人,分驾中船二十五只,自下游驶抵卡所,少停即行,均无滋扰。
约两个月后,二将军再次将乌鲁苏木丹卡伦的纪录奏报朝廷,登记沙俄回撤部队人船批次与数量甚详。有意思的是,也就在这一年开始,相距遥远的黑、吉两地将军常联名上奏,真不知是如何操作的。
罗曼的回忆录说道:他们返回之初由于天气炎热,带的食品大都坏了,到瑷珲后想要买些粮食,见居民不卖去找长官,结果被清兵抓起来,关了一天一夜。后来遇到一个熟人,又送了一些金币,长官下令提供必要的粮食和猪肉,还派人带了一段路。实际上遇到季节较晚时上行的俄国人,瑷珲官员总会告诫路途危险,赠送食物,必要时派人引路,也会在江边安排住处让他们过冬。悲剧的发生,往往在于俄国人执意前行。
这次死亡撤军,也使痛恨穆拉维约夫的人找到新的借口,各种议论和指责甚嚣尘上。但也有不少人为之辩护,包括一些亲历者,一位少尉写道:“我是此事的参加者,我所遇到的困难,所吃的苦处未必比别人少,可是我至今羞于提及这些。因为我觉得,这些艰难困苦在任何一次长途行军、任何一次战争之中,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占领仅仅长度达三千俄里荒凉地带的过程中,两年期间总共牺牲了二三百人,人们为此竟然不肯原谅穆拉维约夫,他何以如此不幸?”(待续) 黑龙江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