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撤回的论文,留美博士之死
作者:王海燕当地时间2019年6月13日,留美博士陈慧祥论文被顶级学术会议接收,毕业在即,却在会议召开前夕,自缢身亡。通过留下的遗书和大量聊天记录,陈慧祥指称,其在佛罗里达大学的华裔导师李涛,通过关系发表他的论文,有严重学术问题,其自杀的直接原因是,导师不愿撤回论文。
据当地媒体2021年3月1日报道,佛罗里达大学已暂停李涛的工作,不得踏足校园,未经许可不得与本校任何学生、教职员工联系和交流。报道称,李涛目前仍能收到学校发给他的15.3万美元的年薪,其在大学的主页已经无法访问。本刊从陈慧祥生前一好友处也确认了这一消息。
在佛罗里达大学做出上述处理前,美国计算机协会(ACM)已发布公告,称2019年陈慧祥的投稿涉及严重违规,其中情节最严重者,禁止未来15年内在ACM的任何场所发表文章,或担任任何审查、编辑或项目委员会的职务。ACM并未公布这位情节最严重者的姓名,陈慧祥的一些朋友认为,这人指的应当正是李涛。
此外,李涛曾担任Fellow的另一个组织学术组织IEE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也在进一步审核专项调查小组JIC关于此事的报告。
ACM和IEEE是全世界与计算机相关的最大非营利性专业技术学会,计算机领域学者被这两个组织严厉处罚,通常可视为在学术界被“封杀”。
两年前,本刊曾详细报道此事。当时在采访了陈慧祥众多的朋友、同学和导师后,我们发现,“问题”论文只是压垮陈慧祥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此之前,漫长的海外求学生涯里,他曾长期处于复杂困境当中,而用陈慧祥一位朋友的话来说,“我们应该有更好的解决途径,不至于让任何一个人处于如此的困境”。
在此,我们重发两年前的旧文,以纪念一个年轻的生命。同时,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一事件的进展。
记者/王海燕 实习生/张宇琦、张隽晔 本刊微博持续更新信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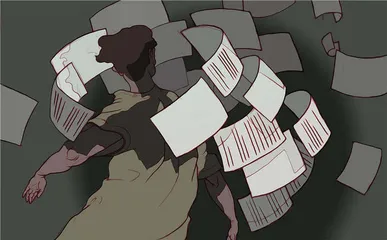
(插图 老牛)
自杀与遗言
当地时间7月11日下午2点,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爱丽丝湖边,平时不大开放的鲍曼中心(The Baughman Center),一座只能容纳96人的中世纪教堂风格建筑里,聚集了超过150人。有美国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其中一些人没有座位,只能拥挤地站在空地上,阳光和佛乐一起弥漫在挑高的建筑空间里,显得静谧安详。当天,中国籍学生陈慧祥的悼念仪式在这里举行。当地时间6月13日早上,他被发现死于佛罗里达大学的计算机实验室里,根据警方调查,陈慧祥死于自缢。
姗姗来迟的悼念仪式很简短,两位校方人员分别代表佛罗里达大学和电子工程系表示了慰问,随后,陈慧祥的表妹代表家人向在场参会人员讲述了他们眼中的陈慧祥。大约25分钟后,所有发言结束。陈慧祥的父母、哥哥和表妹是在他出事后赶到美国的,悼念仪式上,他们希望学校能尽快查明陈慧祥在遗书中指明的导致其自杀的事实。但一名参加悼念仪式的中国籍学生告诉本刊,校方发言人中,没有任何人提到调查进展,而这正是所有关注此事的人最核心的关注点。
陈慧祥去世后,这封遗书通过定时邮件的方式被发送给了其家人、导师和实验室同僚。陈慧祥在邮件里说:“我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很短的时间内写了一篇ISCA,投出去,恰好中了……靠的是Dr.Li的关系,这六个reviewer(审稿人)中四个是老板的朋友。但其实这个论文当时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随后,他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论文从题目、特性化到实验设计各个环节出现的问题,并称“跟Dr.Li沟通后,还是硬着头皮麻痹自己把这篇文章说圆,但是今天发现还是所有的问题都无法fix(修正)……考虑到对以后career(事业)的影响,如果这样发表的话,在体系结构圈内,包括reputation(声誉),我以后的生活会生不如死,完全进退两难。所以我希望通过自杀的方法来弥补我的过失。”
遗书中的Dr.Li指的是陈慧祥在佛罗里达大学的导师李涛;而ISCA,全称计算机体系结构国际研讨会,是陈慧祥研究领域内的四大顶级学术会议之一。在相关领域的顶级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文,正是学术界衡量科研水平最主要的方式。按照惯例,这类顶级会议上,一篇论文是否被接受,通常需要多名审稿人共同评审决定,并且应该严格遵循审稿人和作者互不知晓身份的双盲评审机制。
遗言截图很快在留学生圈子传播开来,不少针对此事发表过看法的留学生在此后都收到了李涛的邮件,邮件称:“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一不幸的事件和受害者家属的心理,在网上散布断章取义和未经充分了解事实真相的不实言论……我在此严正要求你们立即撤销,停止散布,和澄清网络不实信息。否则,有关责任人将面临法律起诉和司法责任。”网上流传的邮件版本,最早出现在6月15日,也就是陈慧祥被发现去世两天后的晚上。
在接受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时,李涛称,事件发生时,他并不在美国。对于遗书中提到的对论文的质疑,他没有正面回应。本刊通过邮件向李涛发出了采访请求,得到的回复是:“对于这一不幸事件,我及实验室所有成员都感到十分悲痛、震惊和惋惜。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届时将有官方结论,感谢您的理解和耐心。”
陈慧祥去世后第10天,ISCA2019如期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召开,陈慧祥的论文依然在会议上公布,李涛代替他上台做了演讲。PPT上的照片里,陈慧祥扬着下巴,笑得明亮,他依然是第一作者,只是被特意加上了生卒年份,“Huixiang Chen(1989?2019)”。李涛并未在会议上对陈慧祥自杀及其引发的质疑做更多说明,这个举动或许是引发陈慧祥亲朋愤怒的原因,6月29日,一些陈慧祥生前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公布,在这些聊天记录中,陈慧祥曾说起,发现论文有问题后,他希望撤回论文,但多次被李涛强硬拒绝,这让陈慧祥感到李涛“没有学术道德”,“逼我造假”。
网络曝光一开始并没有为事情带来进展,直到7月1日,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生工会组织公开呼吁后,7月3日佛罗里达大学校方才对校内学生和工作人员回应称,已安排一名独立调查员调查陈慧祥自杀一事。同样是在7月3日,主办ISCA大会的ACM SIGARCH(计算机系统结构特别兴趣组) 和 IEEE TCCA(计算机架构技术委员会)主席在官网上发布声明称,将协助佛罗里达大学的调查。此时,距离陈慧祥去世,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天。
直到如今,陈慧祥的妈妈依然每天在微信上给陈慧祥发送消息。陈慧祥的多位朋友都告诉本刊,自从来到美国读博后,陈慧祥已经5年没有回过中国了,在这期间,他的家人一直没有见过他。
毕业无期
陈慧祥是2013年来到佛罗里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就读于电子工程系,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计算机体系结构,这是一个偏向计算机基本工作原理和理论的研究方向,与人工智能等热门方向相比,学术界对计算机体系结构的研究更难直接转化为商业应用。他的导师李涛是一名华裔教授,根据公开资料,李涛1993年从中国西北工业大学本科毕业,1996年获得中国航天部计算所硕士学位,2004年获得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博士学位,目前在佛罗里达大学电子工程系任终身教授。
陈慧祥和李涛的求学轨迹有相似之处。沿着中国的高等教育标准历程,陈慧祥在研究生毕业时才开始申请国外的学校。老家山东临沂的他毕业于吉林大学,后保送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研。他本科时的朋友胡瀚告诉我,陈慧祥本科时学习很好,基本上是班上前三名。胡瀚记得,当时出国是学校里很多人的梦想,他们两人从大三就开始一起准备,沿着中国的高等教育标准历程,陈慧祥研究生毕业时才开始申请留学。在陈慧祥的博客里,如今还保留着他201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之际去香港大学面试时的记录,那篇文章里,他写到自己跟一同面试的同学比起来,还是“太菜了”,但随后又兴致勃勃地分享了自己的解题思路。胡瀚则记得,当时除了佛罗里达大学,陈慧祥还收到了一所加拿大学校的邀请,但他最终选择了佛罗里达大学,成为李涛的学生。
比陈慧祥早两年进入佛罗里达大学,如今已博士毕业的陈龙告诉我,他最早在学校社团组织的迎新活动上认识了陈慧祥,两人虽然没有深交,但他记得陈慧祥当时问了很多在美国生活、学习和未来发展的问题。陈龙的印象是,陈慧祥对自己的过往研究和兴趣都有很清晰的规划和认知,对未来的学习也很乐观和坚定。
佛罗里达大学在美国并不是顶尖高校,但在各类榜单上,也能排到30名左右。选择李涛,对陈慧祥来说,当时看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从公开资料可以看到,李涛是IEEE(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的最高等级会员,目前担任着IEEE旗下两份重要刊物的副主编,而IEEE则是全世界电气和电子工程领域规模最大、目前最受认可的非营利性专业技术学会。除此之外,李涛还曾于2015?2017年期间在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担任项目主任,可以审核项目基金发放。这些身份意味着荣誉、权威,也意味着权力。
但在李涛门下读博并非易事,胡瀚早就听陈慧祥说过,李涛实验室的毕业要求是以第一作者发表两篇顶级会议论文。普通人很难确切体会这一难度,在陈慧祥的研究领域,HPCA、ISCA、MICRO通常被认为是三大顶级会议,也有人会加上ASPLOS,算成四大顶会,这些每年召开一次的会议文章录用率通常只有20%左右,而竞争者则是全世界同领域的学者。
这一要求在同类高校中算比较高的,在2017年的一次采访中,李涛谈到,因为研究领域窄、研究难度大,这一领域的博士生如果有3篇项会,就可以在美国的名校谋到教职了。李涛在采访中同样提到:“一个学生什么时候能毕业呢,并不在乎他发了多少论文,从来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如果他能够独立完成整个的研究,他就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研究者。”结合起来看,这意味着,美国导师对博士的毕业问题,有着接近100%的决定权,又是完全弹性的。
李潇潇是2017年认识陈慧祥的,她记得有一次聚会时听陈慧祥提起毕业的问题,感到他有些焦虑,自嘲说“前几年不该太放松了”。直到出事后,李潇潇重新回溯,才更加体会到当时陈慧祥的处境。一名佛罗达里达大学的毕业生告诉我,在该校的理工科专业,博士生大部分都是5年半到6年毕业。
2017年正是陈慧祥在美读博的第5年,当年暑假,他申请了Facebook的3个月实习,这可能是他已经在为毕业做准备了。当时有另外一名和他同年进入佛罗里达的中国籍学生也去了Facebook实习,在实习后拿到了return offer,并于当年年底顺利毕业,开始工作。但陈慧祥当时并没有拿到return offer,同时,他当时只有一篇第一作者的论文,被一个叫ISPASS的会议收录。如果按照中国计算机协会对国际学术会议的分类,ISPASS属于C类会议,与李涛要求的顶会相距甚远。
中国导师与中国学生
也是2017年10月份,从国内到佛罗里达大学交流的博士生陈俊鹏和陈慧祥成为室友。陈俊鹏说,平时聊天时,陈慧祥偶尔会抱怨,说刚读博时帮李涛做了大量的工程类项目,其实跟学术没什么关系,这些工程类项目通常是高校老师与商业公司合作的项目,还说李涛虽然一直要求发高质量论文,但具体懂得不多,又经常让陈慧祥换方向,有点瞎指挥。
除了导师,陈俊鹏记得,当时陈慧祥偶尔也会说自己没有学术天分,很沮丧。当时陈俊鹏还安慰他,说美国的博士学位含金量比国内高,熬到头就好了,除此之外他也不知道说什么。陈慧祥体会到的巨大沮丧和绝望,他和其他的博士也体会过。同在美国读博的胡瀚向我形容,博士绝不是本科和硕士毕业生的校园生活续篇,甚至要求的能力和天分也不同。真正的博士要求在科技的最前沿有所创新,胡瀚把这个过程比作在茫茫沙漠里摸索,常常不知道方向是否正确,又是否在做无用功,不知道需要5年、6年还是7年才能到达一个地方,还是永远达不到。
事实上,多项数据都表明,很多国家的博士中途辍学率都极高。根据美国国家基金会2005年针对43354名受访对象得出的报告,当时美国博士平均取得学位的年限是8.2年,50%的学生会中途退学。胡瀚在身边就见过不少美国学生在读博几年后退出,转而取得硕士学位开始工作。但这个选择对中国留学生来说艰难得多,一是这些远渡重洋的留学生大多从小就是学霸,对他们自己和身边人来说,“辍学”都是难以接受的;二是一旦退学,学生签证就失效了,如果还要留在美国,取得新的身份将成为很大的难题。曾经作为学长迎接过陈慧祥的陈龙说,他也曾和陈慧祥一样,经历过在美求学的至暗时刻,只是他幸运,挺过来了。他说,绝大多数在美国读博的中国留学生都或多或少曾经历过类似的时刻。
除了学术上与导师的嫌隙,陈慧祥的朋友还多次听到他说导师让他做私人事务。在李潇潇向我出示的一份聊天记录中,陈慧祥说:“我都成他(李涛)的专职司机了。”李潇潇让他找机会拒绝,陈慧祥说:“我都习惯了,我老板的原话就是,我最讨厌学生跟我说不。”陈慧祥还提到,因为导师经常找他,他放假都不太敢离开佛罗里达大学所在的盖恩斯维尔。陈俊鹏就记得,偶尔凌晨一两点甚至三四点,陈慧祥还需要出门去机场接送李涛,一些国内学者到佛罗里达大学交流,陈慧祥也负责接送。
博士生和导师私人事务上的关联,在胡瀚看来,是部分华人导师和学生之间的特殊现象。胡瀚甚至见过身边有华人导师对美国学生和中国留学生区别对待,“对美国学生来说,接送导师去机场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有很强的权利意识,但中国学生就比较逆来顺受,学术上也同样如此”。实际上,很多华人导师的确更加倾向于招收中国留学生,比如李涛,其门下目前在读的博士生均来自中国。某种程度上,李涛属于1999年中国高考扩招以前那一批走出国门,最终在美国学术界站稳脚跟并获得了话语权的精英学者之一。如今,当留学美国的学生们提到“华人导师”时,绝大多数时候,指的正是这一批学者。
关于华人导师与中国留学生,李潇潇有另一个观察,她说,上一代在美国站稳脚跟的华人导师通常有两个极端,一种是因为自己曾走过不少弯路,所以更加尊重这一代留学生的权利,希望他们自由发展;而另一种则希望将自己的上升之路复制到学生身上。李潇潇说自己很幸运,遇到的是前一种。
李潇潇早就发现,陈慧祥的留学生涯相对比较苦闷。在Facebook实习过之后,他曾对一名同事说起,李涛非常反对他实习,“老板觉得我没搞研究相关方向,把我的实习骂成狗,说我这是disaster(灾难)”。作为室友,陈俊鹏则是在陈慧祥出事后,才在和其他人交流中知道,陈慧祥经常被导师骂能力不足,自信心很受打击。
2018年里,陈慧祥依然没有顶会文章,但毕业可能出现过短暂的曙光。他发表了两篇第一作者的文章,如果按照中国计算机学会的标准,分别是B类和C类会议。大约就在2017年到2018年之间,他也完成了中期答辩。中期答辩指的是博士已经提交了毕业论文研究计划书,并取得答辩委员会批准进行研究。此后,他从博士学生变成了博士候选人,相当于离毕业只有临门一脚了。从那时起,李潇潇听陈慧祥频繁提起,自己要毕业了。2018年暑假,他还难得地外出游玩了一圈,李潇潇当时还以为他在毕业旅行。但后来,陈慧祥毕业的时间一再拖延,从2017年年底,到2018年暑假,又到2019年春,似乎始终没个准信。李潇潇记得,当时大家一起聚会,陈慧祥还会偶尔自嘲,说在佛罗里达大学再也找不出比他更老的博士了。
在此期间,陈俊鹏则听陈慧祥说起过,李涛将毕业要求降低到一篇项会文章。因此,2019年3月,陈慧祥查询到自己那篇文章被ISCA收录时,高兴得大叫起来,满屋子都能听见。但很快,陈俊鹏又听陈慧祥说,导师要求他再发一篇项会论文才毕业。陈俊鹏和胡瀚都记得,毕业时间再次延期让陈慧祥很沮丧,但陈慧祥还是表现出比较精神的样子,积极开始下一篇论文,并打算在2019年8月份投出去。
那时候,他还跟陈俊鹏谈起,说毕业了想先在美国找工作,安顿下来,还说起自己那辆二手车,虽然看起来破破烂烂的,但很多零配件都是新换的,很好开,他还要继续开着它去新的公司上班。
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篇项会还没开始,陈慧祥就发现了不对劲。ISCA上那篇文章是在2018年12月初投稿的,根据陈俊鹏和陈慧祥的聊天,当时这篇文章陈慧祥只做了一个多月,还在李涛的指导下换了好几次大方向,因此实际操作的时间非常短。那篇论文最终的题目是《3D-based video recognition acceleration by leveraging temporal locality》,试图用体系结构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的方式提高视频识别性能。2019年3月,经过前期第一轮评审结果和作者答疑,陈慧祥最终被通知论文中选。按照一般流程,此时论文已经定型,只等着会议召开,上台演讲了。
但从4月开始,陈俊鹏开始频繁听到陈慧祥抱怨,说实验结果与预期差距越来越大,也就是说,直到那时,陈慧祥还在不断验证自己的论文。有时候陈俊鹏在楼下吃饭,陈慧祥会过去问他,如果他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陈俊鹏安慰他说,科研上的创新不是100%,有时候能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改善,也是可以的,就算没有改善,能提出新的框架也是贡献。但陈慧祥并没有被安抚到,他反复跟陈俊鹏说,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对错的问题,并且在业内人看来,这篇文章就像1+1=3一样错得显而易见且荒谬。
陈俊鹏记得,那段时间陈慧祥每天都是工作到夜里两三点。以前的陈慧祥非常热情好客,隔一段时间就会邀请朋友到家里做客,他自己很喜欢做菜,中餐西餐都做得很好。但自从发现论文有问题后,他再也没有组织过聚会。也是从那时候开始,陈俊鹏频频听到陈慧祥提起想放弃读博。但放弃也并不容易,按照陈慧祥的想法,即使放弃读博,也是以撤回论文为前提。虽然许多人跟我谈起,如果选择去工业领域,在学术界的失误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且有多名和陈慧祥研究领域有交叉的博士生告诉我,因为研究领域窄、研究难度大、数据体量大,体系研究领域的很多文章复现起来都很耗费精力,也很少有人去复现。但陈俊鹏记得,那时候陈慧祥跟他聊起来的感觉是,文章如果不撤回,迟早会穿帮,并将严重影响他未来的职业生涯,即使他去工业领域,甚至回国,都逃脱不了。
陈俊鹏觉得,这可能也和陈慧祥强烈的责任感有关。他说,平时陈慧祥出门,如果开车剐蹭到其他车辆,即使车辆主人不在,陈慧祥也一定会留下带有自己联系方式的小纸条。还有一次,陈慧祥的车坏了,陈俊鹏开车带他,因为跟陈慧祥说话分了心,陈俊鹏倒车的时候撞到障碍物,车碰坏了一点,陈慧祥坚持认为自己也有责任,要赔偿。
根据陈慧祥和朋友的聊天记录,出事前,陈慧祥唯一想做的是撤回论文,并因此和李涛产生过多轮拉锯。5月22日,他抱怨“不发对老板影响很大,他让我必须搞完……真是生不如死啊”,还提到“在严肃地考虑离开实验室,因为这算是我做了恶,即便顶会又如何”。他没有具体指明不发对李涛的影响是什么,但通常来说,导师一般可以用论文去申请项目或基金。5月27日,他提到“我好难受……真的好难啊”,接下来又提到“他死活不让我撤,还跟我说8月份,不吃饭不睡觉也得把paper给投出去……这一篇论文,让我好好做PPT,丢人也得上去讲解”。这里提到的“8月份论文”指的是陈慧祥原先准备做的第二篇项会。
6月1日,他提到“我宁可不要学位,不仅仅是违背道德,而是局面不属于我控制范围之内”。就在那几天,有一次陈俊鹏坐在沙发上,陈慧祥走过来找他聊天,眼睛都睁不开的样子,双手撑着膝盖,说自己没有休息好,很头疼,真的想放弃读博了。后来在和陈慧祥朋友的聊天中,陈俊鹏才知道,当时陈慧祥已经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了,身心状态都非常糟糕。但他可能依然在竭力向外界传达自己积极的一面。李潇潇记得,在他出事前10天,想配一副眼镜,在微信上跟陈慧祥请教,陈慧祥还非常热心地发去了许多链接,教她怎么比价。直到事后,李潇潇才回想起来,按照陈慧祥以往的习惯,说完眼镜的话题,他还会热心地问问李潇潇的生活近况啊之类的,但那天他什么都没说,李潇潇以为他太累了。
李潇潇不知道,那时候陈慧祥可能已经跟导师爆发过比较激烈的冲突了,根据6月6日的一份聊天记录,陈慧祥说“弄完了,结论就是,老板绝对不会撤稿”,还说“跟他吵了一架,差点叫警察”,并再次提到“他坚决不撤稿……我老板的原话是‘我要是毁了他声誉的话,他会弄死我,他说,这是红线’”。
事实上,美国的大学是教授治校,地位很高,取得了终身教授职位的学者,除非特殊原因,无法被解聘,而特殊原因里,学术不端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和导师的激烈冲突中,陈慧祥分析自己当时的状态:“第一,毕业遥遥无期;第二,处于精神崩溃边缘,其实也没事,这个事情如果能挺得过去的话,我再坚持三个月试试。”
但那时候他已经站在了悬崖上,根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事发前一个月,他对一名好友发出了想自杀的信号,这位好友与陈慧祥不在一个地方,他试图劝说陈慧祥看心理医生。5月25日,陈慧祥在某社交媒体上记录了体验上吊的感觉,发现“滋味儿没那么好受”,他觉得自己还挺“贪生怕死”的。但对死亡的恐惧最终被更大的阴影覆盖,6月12日晚,他没有回家,第二天,人们在他平时工作的机房里发现了他的遗体。那篇论文还是没有撤回,依然如期在ISCA会议上公布了,李涛代替陈慧祥上台做了演讲,截至发稿前,佛罗里达大学和ISCA主办方尚未给出调查结果。
陈慧祥的实验室同僚都出席了他的悼念仪式,但李涛没有。仪式上,陈慧祥的家人替他接过了象征着工程师骄傲与责任的工程师指环。在微博上,陈慧祥的哥哥说:“你喜欢的爱丽丝湖,你说你要来举行婚礼的教堂,你本该毕业时亲自接过的工程师指环,你的毕业典礼不该是这样的啊。”
(文中除了陈慧祥和李涛均为化名。实习生李秀丽对本文亦有贡献) 自杀李涛学术博士陈慧祥佛罗里达大学李潇潇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