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1919:思想者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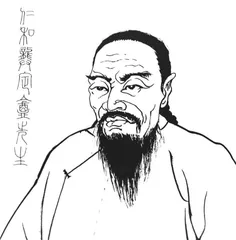 龚自珍(1792~1841年,字尔玉,浙江杭州人)
龚自珍(1792~1841年,字尔玉,浙江杭州人)
不及而立之年,龚自珍已经意识到,在庙堂之外的中国广大疆域里隐藏着重重危机。
龚自珍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师从宋璠,又随外祖父段玉裁学习,接受了严谨的训诂训练,奠定了厚实的朴学基础。青年时他常随父母宦游,得以观察社会,增长阅历。19岁他参加科举考试,在四次乡试后终于中举,但次年进京会试时落榜。他在京师与同样科举不中的魏源结为好友,一起拜师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他深受其师影响,秉承了“道、学、治”一体的思想。
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第二次进京参加会试,依然未中。两次会试失败和多年的游历见识,使他将目光转向了社会现实问题及重大国家方略。当时耕地大量开垦和人口增加给清社会带来了突出的矛盾,新疆动乱及周边民族矛盾激化,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洋盗”闹市,鸦片输入中国致白银大量外流,再加水旱灾害频发……以诗文闻名朝野的龚自珍开始从庙堂今文转向广阔的中国边疆,从礼仪中国的视野走向帝国舆地学。他撰写了《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已佚),其考察内容从西北、东南的地理环境差异拓展至两个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变化。《西域置行省议》主张在新疆建立省级行政建制,使新疆领土直接归中央政府统治,但并未受到重视。60年后李鸿章看到此文,才意识到龚自珍思想的前瞻性,“龚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
之后龚自珍以举人身份进入朝廷,任内阁中书一职,期间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又任国史馆校对多年,具备了完整的陆地边疆知识。他负责校理《理藩院》,熟悉了理藩院管辖藩部所在,以地理学为中心,形成“中外一家”视野下的“天地东西南北之学”。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林则徐前往广东查禁鸦片,龚自珍提出可参考明代抗倭名将胡宗宪《筹海图编》中关于沿海地理形势及海疆防御的内容,重点关注辽东沿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到广东一线。由此可见,东北也成为龚自珍边疆观的一部分;西北与东南并称联动,则显露了龚自珍经学视野中的边疆结构。在中国面对西方威胁的国际环境中,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在国家空间中的互动成为19世纪上半叶中国地缘政治最为深刻的洞见,是魏源等后来人“开眼看世界”的先声。(文/胡艺玮 参考书目:《龚自珍评传》,陈铭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汪晖著;《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研究》,王鹏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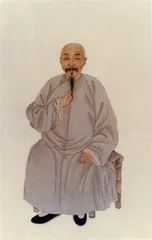 1898年7月17日,戊戌变法已开始一月有余,在这天,光绪皇帝下令将《校邠庐抗议》印刷1000部,发给各级重要官员签注,引起一片或褒或贬之声。
1898年7月17日,戊戌变法已开始一月有余,在这天,光绪皇帝下令将《校邠庐抗议》印刷1000部,发给各级重要官员签注,引起一片或褒或贬之声。
该书的作者就是冯桂芬,他早年是林则徐的学生,也是魏源的好友。魏源的《海国图志》出版后,时人并未给予多少关注,但冯桂芬专门写文章指出其中不合史实之处,而魏源也一一接受批评,在扩充时对书稿进行了修改。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联军在北京放下的一把大火不仅烧光了圆明园,也烧光了中国人对“万年和约”的幻想,从这时起,时人才渐渐意识到:变局来了。
面对这样的变局,冯桂芬极其冷静而务实。这年年末,52岁的冯桂芬来到上海,两年前他才经历过政治的攻讦与冷遇,为此隐居山间了一段日子。到上海后,他住在租界的一座小寺庙里,在这里开始撰述《校邠庐抗议》。
在《校邠庐抗议》中,冯桂芬清醒地写道:中国虽大,也只占到世界的“十有五分之一”,更不是世界中心。而中国更有许多地方不如外“夷”:除了利炮坚船不如夷外,还有“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冯桂芬在书中提出了较为全面的“采西学”主张,不仅仅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还要学习他们的生产机器、自然科学,乃至人才的教育与选拔。他在书中说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可说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先行。事实上,无论洋务派,还是维新派中,都有人从他这里吸取思想的养分。
写完《校邠庐抗议》,冯桂芬又参与了广方言局的筹划,而这正是基于他的建议才得以创立的外语人才培训机构。他的行动与他的思想一起,跳跃在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中。(文/曾宇清 参考书目:《冯桂芬评传》,熊月之著;《冯桂芬传》,周菊坤著)
 “我能够称自己是一个已受教育的人,而且就此种身份,我应该问自己‘我将用自己的所学去做些什么呢?’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之前,我已把自己将要付诸行动的事在心中规划出一幅略图。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the rising generation of China)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
“我能够称自己是一个已受教育的人,而且就此种身份,我应该问自己‘我将用自己的所学去做些什么呢?’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之前,我已把自己将要付诸行动的事在心中规划出一幅略图。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the rising generation of China)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
写下这些文字时,容闳已经在美国留学8年,他从中国华南一隅的小乡村中走出来,成为耶鲁大学首位中国留学生。他深知留学机会不易,想将在西方受教育的机会传递给下一代中国年轻人。
不同于哥哥从小接受私塾教育,7岁容闳便被父亲送入德籍传教士郭士立之夫人(英国人)所开办的教会学校,因学校由马礼逊基金(英国)支持,后改名为马礼逊纪念学校。学校位于澳门,在那里容闳学会了英文。鸦片战争之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马礼逊纪念学校随即在1842年搬至香港。在其中担任教师的勃朗牧师,在1846年因身体不适离校返美,同时携带三位学生赴美留学,容闳就是其中之一。
容闳满怀欣喜地来到美国,1850年于麻省孟松预备学校毕业后考入耶鲁大学。同去的黄胜、黄宽因不同原因离开,容闳于是成为耶鲁大学历史上的首位中国留学生。1854年毕业后,容闳即刻返回中国,因为8年以来他的主要学习目的就是“以造就自己,为终身服务祖国做准备”。
在曾国藩担任总督的江南制造局,容闳凭借出色的外语能力,负责制造局的所有机器采办,之后他提议在局内设立相应的机械训练学校,被曾国藩采纳。1870年,在好友丁日昌的帮助以及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位重臣的联衔奏请下,朝廷批准了容闳提出的派幼童赴西方国家留学的建议。从1870年成立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到1875年李鸿章呈奏撤销肄业局,容闳周旋各方,尽全力为四批学生争取到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以保证留学事业的延续性。
幼童留学事业虽中途被撤弃,但经过国外的学习,四批留美幼童回国之后大都成为国家政治、工业、军队、教育、商业等方面的人才。留美幼童之一梁诚,作为驻美公使,成功促成了美国政府退回超额部分的庚子赔款,用来选送优秀青年赴美留学。1909年第一批“庚款”学生前往美国,容闳将此计划的实行喻为肄业局事业的再生。
1911年5月,83岁高龄的容闳在美国患中风。当年10月,孙中山发来信函恳请容闳归国巩固共和,容闳此时已得脑溢血昏迷不醒,于次年4月去世,临终前仍不忘叮嘱二子弃所营业,回报祖国。
(文/胡艺玮 参考书目:《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容闳评传》)
 王韬(1828~1897年,字兰瀛,江苏苏州人)
王韬(1828~1897年,字兰瀛,江苏苏州人)
1874年,苏州人王韬在香港集资创办了《循环日报》(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并担任主笔。这是香港第一份华人资本、华人主理的商业报纸。
王韬在早年只是个失意的落榜者。他7岁即在父亲的严教下开始学习儒家经典,乡试时主考官赞其“文有奇气”,但随父参加省试却落榜,那以后他对科举制度已经颇有不满。1849年夏天其父去世,他被迫承担起供养母亲、兄弟、妻女的责任。相比在私塾教书的微薄收入,基督教伦敦会所创立的墨海书馆的丰厚报酬显然更具吸引力。1850年王韬去往上海,通过相识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介绍,到书馆担任中文编辑。在通晓中文的传教士帮助下,王韬参与翻译撰著了一系列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书。
但他仍有士人报效朝廷之想。太平天国运动发生期间,1861年,王韬在他所写的进言文章中提出,帝国最痛之疾在于官僚体制及其擢才方法之僵化,人才不应仅收发公文,还要能为政府办理实际事务,而这些仅凭科举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从政之心又一次被挫败。之后一年,王韬因支持太平天国而被清廷缉拿,辗转逃往香港。
在老友麦都思的安排下,王韬凭借深厚的中学修养,在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开办的香港英华书院(现香港岭南大学前身)负责中国经典的译介工作。1867年理雅各回苏格兰探亲,王韬也应其邀请往欧洲游历。他在欧洲两年,遍游各地,体验电报、火车、纺织机给生活带来的便利,接触各地民俗与国家风物,还曾参加法国世博会。另外,王韬对英国君主立宪制度颇感兴趣,曾旁听英国下议院开会,目睹议员们自由地表达政见,深为所动,以之为“君民共主”政体。
此番再回到香港的王韬,见识和心境已大不相同。创立《循环日报》后,他逐渐通过文章和丰富的西学知识,开拓出自己的言论空间。
王韬在欧洲开始意识到报纸作为收集传播各种消息的载体的重要性。《循环日报》经济版的商讯能够适应当时华人贸易稳步增长的需要,成为报纸的主要收入,使报纸能维持独立。除此之外,《循环日报》还设有时评专栏,刊登的社论针砭时弊,大部分为王韬自己撰写。1875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变法,包括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3篇政论,文中主张“除弊、兴利、尚简、设领使、练水师、射电线、制战舰、办铁路”,把学习西方放到重要位置,并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这些文章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王韬也凭此取得他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奠基地位。罗斯威尔·布林顿(美国汉学家,著有《中国报刊:1800~1912》)认为他是“香港中文报纸早期发展中的首要人物”,林语堂则称他是“中国记者的先行者”。(文/胡艺玮 参考书目:《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金观涛、刘青峰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湖南浏阳人)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湖南浏阳人)
1896年秋,谭嗣同31岁,他的父亲、湖北巡抚谭继洵替他谋得一个江苏候补知府的小官职。
早年谭嗣同先后拜过欧阳中鹄、涂启先、刘人熙为师,系统学习中国典籍,尤爱研读王夫之,汲取其唯物色彩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与此同时,他四处游历,观察风土,结交名士。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满怀忧愤的谭嗣同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同年,康有为公车上书,受到感召的谭嗣同赴京,并因此结识了梁启超、翁同龢等人。
赴南京上任后,谭嗣同充分体会了当时官场的黑暗腐败,对此深恶痛绝。他无心做官,而潜心著述,于1897年写就了一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惊世骇俗且影响深远的奇书——《仁学》。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路上急行军,谭嗣同却试图以古为鉴,在历史的漫长时间轴上追问维新改良思想的价值。《仁学》杂糅了儒、释、道、墨各家学说,又有一些西方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同时加入了经世致用的佛学思想,形成了比较独特的面貌,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学理著作。
谭嗣同的努力在于,他要把“仁”和“礼”(包括“三纲五常”)剥离开来,恢复孔、孟仁爱思想的初衷,在“仁”的基础上引入西方平等的内涵,让中国传统文化找到与时代的结合点。
1897年以后,谭嗣同回到湖南,在维新派的支持下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组织,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坚力量。1898年,慈禧太后废黜光绪帝,谭嗣同参与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他拒绝出逃,决定以死殉志,“愿以颈血刷污政”,“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同年9月28日,他在北京宣武门外的刑场赴死,年仅33岁,是被杀的“戊戌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身后,《仁学》的余波仍在思考中国变局的人们中间延续。梁启超把《仁学》称为当时思想界的“飓风”。《仁学》中的观点对后来的唐常才、邹容、陈天华、吴樾等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此书在一定程度上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
钱穆曾经评价道:“晚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谭嗣同的《仁学》既是对民族生存意识与生存意志之召唤的自觉应答,又如梁启超所言,是放眼全球的“世界主义”。(文/张佳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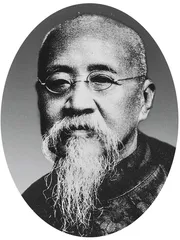 罗振玉(1866~1940年,字式如,浙江上虞县人)
罗振玉(1866~1940年,字式如,浙江上虞县人)
1910年,数千卷文书被跋涉千里从敦煌护送至京。在此之前,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已先后从敦煌带走近万卷的珍贵文书。
这批敦煌文物得以留存,背后是一位国学大师的努力:罗振玉。1909年,罗振玉从伯希和手上看到了出自敦煌的“唐人写本及石刻”,他“欣喜若狂”“诧为奇宝”;得知敦煌尚有卷轴8000卷后,他马上告知学部,请求朝廷购藏剩余国宝,免于外人掠夺。
罗振玉17岁时即通读了1000多卷的《皇清经解》,随着阅读经史的进阶,他感到古碑刻的重要,开始收集、整理碑刻资料。他与古学的缘分自此开始。
但罗振玉后来的事业却是从西学开端。甲午战争后,他与友人创农学社,翻译外国农学书籍。1901年他前往日本考察,归国后投身教育,创办东文学社,王国维即出自该学社,他也成为罗振玉学术事业上的同行者。
1901年,罗振玉第一次见到甲骨,便决意肩负起搜集、研究和流传后世的责任。他自己收藏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他正确判断出甲骨文的出土地不是当时商人所说的汤阴、羑里,而是河南安阳的小屯,这为后来殷墟的发掘奠定了基础。他又致力于让甲骨文为世人所知,出版了5部作品,著录甲骨5400余片,占到甲骨出土问世后30年间所有著述的三分之一。而在研究上,罗氏考释出大量的单字,又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现象。他编、著有《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考释》等作品,近代甲骨文研究中被称为“甲骨四堂”的四位大家: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罗振玉名列其首。
罗振玉也是敦煌研究的先导者。敦煌文书被发现后,他除了致力保护,又写下《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唤起国人注意。1914年,他与王国维合撰《流沙坠简》,鲁迅评价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是一部研究国学的书”。这本书是近代简牍学的开山之作,而他的努力也带动了一批研究敦煌的学者。
郭沫若说“欲论中国的古学……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欧风美雨之中,这位“嗜古”的国学大师或许在政治上显得颇为保守,但在学术上却使中国文化的研究开出新篇,也为巨变之下中国文化的流传做出贡献。(文/曾宇清 参考书目:《罗振玉评传》,罗锟、张永山著)
 王国维(1877~1927年,字静安,浙江嘉兴人)
王国维(1877~1927年,字静安,浙江嘉兴人)
1894年甲午战败,有识之士开始在激愤中思考国运寻求变革。同年,17岁的王国维赴杭州考入崇文书院,逐渐走上追求新学的道路。
王国维与学术的渊源,似乎在他一出生时就确定了。1877年,他生于浙江省海宁县城双仁巷的书香世家,从小接受塾师的启蒙教育,后在秀才出身的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古籍,同时初步接触到一些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
在杭州求学六年后,他在名士罗振玉的资助下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进修,因病于次年归国,开始在罗振玉主办的《教育世界》杂志做编译工作,为国人系统介绍近代西方在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先进思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亡,王国维再次东渡日本,四年侨居期间潜心研究经史、小学。归国之后,他多有著述,并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地讲学,为时人所仰望。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来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以在1904年问世的《红楼梦评论》为例,从叔本华的哲学精神谈论到《红楼梦》蕴含的悲剧精神与美学价值,再到辨妄求真的考证,其批评体系可谓严谨缜密。
王国维也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为之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在著作《古史新证》中,他总结出具有开创意义的“二重证据法”,即“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以及考证古代历史文化,这后来成为公认的科学的学术正流。
可以说,王国维的方法论是对19世纪末以来部分新史学思想与观点的总结,其中包括西方的进化观、价值观等。他既不墨守自封也不轻易疑古,反而充分依靠地上、地下之证据,以过去的经籍为基础,注重对新发现的史料的研究,从而完善求证。陈寅恪曾经总结王国维的治学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异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于颐和园自蹈昆明湖,时年51岁。这一事件当时震惊了全国知识界。对于王国维自杀的原因,学界莫衷一是。陈寅恪为他撰写墓志铭:“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伟大学者,著有《人间词话》《静安文集》等62种著述,批校古籍逾200种。郭沫若曾评价道:“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文/张佳婧) 校邠庐抗议中国近代史冯桂芬王韬清朝罗振玉龚自珍容闳谭嗣同思想者晚清五四王国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