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3)
作者:朱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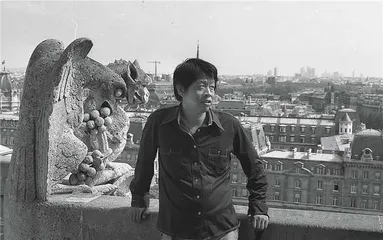 1995年8月,我接管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留下的残部,成为第四任主编。那时,周刊只留有四个记者,能调度的力量有限,我只能依靠在新闻界与文学界朋友的资源。我想到了要开一个讨论生活态度的专栏,就邀请一帮作家朋友——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写小品,当然也就找了王小波。小波交稿是最快的,他给我的第一篇《个人尊严》就发表在我主编的第一期刊物——1995年第五期上,刚开始的栏目叫“生活广场·大家谈”,放在最后两页,是尾声。
1995年8月,我接管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留下的残部,成为第四任主编。那时,周刊只留有四个记者,能调度的力量有限,我只能依靠在新闻界与文学界朋友的资源。我想到了要开一个讨论生活态度的专栏,就邀请一帮作家朋友——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写小品,当然也就找了王小波。小波交稿是最快的,他给我的第一篇《个人尊严》就发表在我主编的第一期刊物——1995年第五期上,刚开始的栏目叫“生活广场·大家谈”,放在最后两页,是尾声。
现在回想,王小波给周刊开专栏所写杂文,要尊严是个大主题。尊严是人的立足之本,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独立自主的人互为尊敬,不被奴役,才有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按小波的说法是,我们的社会环境导致了对自己、对他人尊严的忽视,因此,个人位置,是他最“内急”要疾呼的。给我的这第一篇文章中,他以春运与公厕的现状,说一节车厢里的人“挤在一起像一个团”,公厕肮脏则是“满眼都对黄白之物”。他说,“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关系上定义”,所以,当个人单独存在时,居然只能算是“一块肉”。我称好,示谢。他紧接着又发我一篇《有关媚雅》,调侃大众被格调蛊惑,易在高雅门槛里装态,其实比媚俗害处更大——找罪受也是小波要挖苦的重要主题。他举例自己听布鲁克纳交响曲与巴赫的合唱,前者是“恨不得一头碰死算了”(遗憾的是他接受不到布鲁克纳的感人之处);后者是写老太太唱“哈利路亚”,用力过猛,假牙从口中飞了出来,使神圣的赞颂变成了一声“噗”。当时邀稿要求千字文,篇幅在一千五百字内,他的叙述简练,有投枪匕首的意思,又带冷幽默,周刊同事们读了,人人叫好,以争相传阅为快。我因此就邀王小波专门开一个专栏。
专栏从1996年过完春节他就开始写,但《三联生活周刊》那时从发稿到出刊要一个多月,因此,刊出是3月下半月那本了。王小波自己给专栏起名叫“晚生闲谈”,与前辈比,他称自己是“晚生”,这“晚生”又隐含些微挑衅的意味。他那时已经用传真机,稿子写完就用传真机传到编辑部。专栏的第一篇是《另一种文化》,“另一种”是指人人心中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暧昧的共识”。小波要嘲讽那种不敢面对自己真实内心,掩藏自己本能趣味,“鬼鬼祟祟”的人。他这样一种姿态,令当时周刊很多人着迷。苗炜说,他经常守在传真机旁等王小波的传真,做第一读者,可见他的文字对周刊这些年轻人的影响力。当然,苗炜的办公桌本就在传真机的边上。
王小波有时也来编辑部找我,还是慢慢拖着步子,歪斜着身子,慵懒疲惫的样子。编辑部的人都崇拜他、喜欢他。那时办公空间很小,他也会跷着腿,随便拉把椅子,与年轻人闲聊。我后来在李银河编的王小波书信集中,看到他给刘怀昭的回信,说到他不喜欢“学以致用”的说法,认为“智慧本身就是尺度”,“人有了智慧才能有出息”,“假如你相信智慧是好的,就应该从善如流”。可见刘怀昭当时可能与他交流深入些,两人居然还有私下的交往。刘怀昭是当时周刊思想最敏捷的才女。王小波是一直强调,智慧是立人之本的。智慧是参透、超脱,脱身于外,了然于胸,而能会意一笑。我们也有一两次走出胡同去吃饭。胡同很长,夏日的阳光耀目。走出胡同,地安门的马凯餐厅是最高待客规格了,但王小波其实对吃不讲究,他对物质的东西,似乎不懈分辨。他确实是独孤的精神贵族,却一直自诩为“粗鄙之人”。
 他的专栏维持了一年。其中有一些名篇,如《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现在已经成为人人挂在嘴上的名词了。小波要表达的是,对设置别人生活者、对被设置安之若泰者的厌恶。规定角色、规定生活,逼迫生活,所以才诞生出那么多精神侏儒。但王小波的有趣是,不空谈概念。他绘声绘色写了一头能敏捷地上房顶,在屋顶晒太阳,俯视傲视他类,我行我素的猪。学汽笛的细节有点《半夜鸡叫》的意思。我想,莫言大约就因这篇文章触发,才调动他的想象力,写成了《生死疲劳》吧?
他的专栏维持了一年。其中有一些名篇,如《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现在已经成为人人挂在嘴上的名词了。小波要表达的是,对设置别人生活者、对被设置安之若泰者的厌恶。规定角色、规定生活,逼迫生活,所以才诞生出那么多精神侏儒。但王小波的有趣是,不空谈概念。他绘声绘色写了一头能敏捷地上房顶,在屋顶晒太阳,俯视傲视他类,我行我素的猪。学汽笛的细节有点《半夜鸡叫》的意思。我想,莫言大约就因这篇文章触发,才调动他的想象力,写成了《生死疲劳》吧?
比如《肚子里的战争》,调侃的是“文革”,“工农兵占领舞台”、“卑贱者最聪明”时代,所谓“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荒谬。虽然“真正的大夫都下放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医院里全是工农兵出身的卫生员”夸大了,但当时专家也确实都靠边站了,造反派当家。文章中三小时找不到阑尾,把“下水”都翻腾出来,最终太阳下山前才找到,这变成写小说了,但它确实让苗炜们读到眼泪都笑出来了。小波要表达对那个“闹事者”的愤怒——“他明知道自己在胡闹,但还要闹下去,主要是因为胡闹很开心。”
比如《谦卑学习班》。学费两千美元,两周,膳食自理,教人学习谦卑。参加者尽是各路名人,在山中废弃的学校里,睡破床垫,吃粗劣食物,排队盥洗,质疑之,就被反问:“别忘了你是来学什么的!”结尾,只听一堂课就结业,讲演者说,我只说一句话,大家就会终生受用,再不会狂傲。这句话写在黑板上:“你是个傻×。”这样的学习班,正在当今中国,以各种各样的名义,遍地开花。缴费参与者大约都没读过王小波的这篇小说;而那些办班的人,则直接、间接都受了这篇文章的启发。
再比如《体验生活》,本在生活之中,却还要去“体验”,小波笔下,就成了“像死人诈尸”。他调侃的是要把好日子变成苦日子——那个司务长说:“这些菜不吃就坏了”,于是,吃掉旧的,新的又老了。持这样愚蠢生活态度的人,自称“勤俭持家”,现在也有的是。小波调侃“文革”中吃“忆苦饭”的找罪,写到“北回归线皎洁的月光下”,闹肚子者络绎不绝,为了“出清”所食,索性坐到月光下的小桥上聊天,有点小说的味道了。现在回想,1995、1996年的王小波真是才华喷溅,在极短的时段里,他在小说与随笔两个领域里同时天马行空,旺盛的想象力真如火山喷发,其光焰在喷发中迅速地耀亮,又很快熄灭。人的生命的能量其实是有限的,王小波真为这痛快淋漓,奢侈地挥霍了这有限。
记忆中,王小波给我的文章,经常会以“我插队的时候……”“我年轻时……”开头,文中经常会引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罗素是他的精神导师。王小波告诉我,数学原理本就是他的爱好,数学最能体现逻辑。但我想,还是罗素的《自由之路》,及对权力的社会分析对他影响更深吧!
净土胡同的那些日子,构成了难忘的记忆。王小波是用他的专栏支持了我,他的随笔中的精华,大多发表在了那一年的《三联生活周刊》上,它们成了早期生活周刊极需要的一种气质,吸引与哺育了一批年轻读者。王小波以他幽默、不妥协的特立独行姿态,甚至影响了一代人的生活态度,这是他的随笔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走了,就再找不到这样的专栏作家了。(待续) 读书文学小说王小波80年代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