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被继承的,被改变的
作者:驳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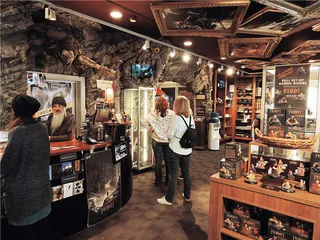 2019年2月20日下午,北京人艺联排《茶馆》,准备为老舍诞辰120周年献上十余场演出。
2019年2月20日下午,北京人艺联排《茶馆》,准备为老舍诞辰120周年献上十余场演出。
这天下午,循着走熟了的左侧小径一直往前,绕到后台入口,却发现眼前一派工地气象,绿网结张,近处,挖掘机已开到后台门口,在离剧院这栋漂亮的苏式建筑不到一米远的路面开垦出一道大口子——这是北京人艺正在建设的新剧场。首都剧场的后台呈凹字形,化妆间小小地排布在一起,演员们或二或三地共用一间,走廊尽头即是舞台。联排这天下午,后台涌进许多人,多是媒体,采访、拍摄乱乱哄哄,小小化妆间能挤进去五六个人,但演员们脸上相当镇定,拍摄聊天都不影响他们上妆。这一代演员的《茶馆》演了这20年300多场,台词早就长在心里,化妆的动作也娴熟至极。我注意到,濮存昕贴他那两撇胡子的时候,刻意未贴平整,胡须与皮肤之间突起一小块空隙,免得一说话牵动了它。
濮存昕扮演常四爷,与扮演秦二爷的杨立新共用一间化妆室,二人背对着坐在各自镜前,一抬头,就能从镜子里头看到对方。我问濮存昕一个跟时间有关的问题,他想不真切,放下手中的胶水瓶,转过身去跟杨立新商量,仿佛别人能帮他想起来似的——俩人都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虽然杨立新进剧院更早,但二人在剧院里作为青年演员挑起重担则是前后脚。他们也都是“《茶馆》二代”,二人同时期开始在《茶馆》里跑龙套,演小角色,看于是之、郑榕和蓝天野这三位“初代仨老头儿”怎么处理台词和节奏,边亲近边学习。
“王利发”梁冠华在另外一间,凑近了才发现,他脸颊两侧按了些许腮红,红扑扑的,远看能显年轻。也是,“《茶馆》二代”早就不年轻了。算下来,这拨“仨老头儿”中最小的梁冠华今年也有55岁,而杨立新和濮存昕两位都已前后退了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演戏。2019年,也正好是他们这一代人出演《茶馆》的第20个年头。
二代的20年
在1999年人艺下定决心重排《茶馆》之前,濮存昕等几位演员其实都在老《茶馆》里跑过龙套,演过小角色。濮存昕还记得当时他刚到剧院没多久,扮演秦二爷的蓝天野身体不大好,有两次排练,他就替老爷子走位置。
“秦二爷管王掌柜叫‘小王’,我就回身喊于是之老师‘小王’,他就抿嘴跟那儿笑。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现在管他叫‘小王’,他就笑。”濮存昕边上妆边跟我讲述过往。
但老辈里面,身体最先支撑不住的是于是之。1992年人艺成立40周年,这一年的《茶馆》演出,也是于是之、郑榕和蓝天野的最后一场。当时的观众仍能记得于是之谢幕时的凝重,林兆华也在场,他后来回忆,“于是之老师那个时候语言有一点儿小小的障碍。很悲壮”。
到了1999年,建国50周年,人艺终于决定重排《茶馆》。实际上,这中间,作为人艺副院长的于是之一直鼓励林兆华重排。“动人艺老祖宗的东西,”林兆华说,“越想越是件挨骂的差事。”所以最开始他想在剧院外面排,“可以大胆一点儿”,甚至已经找了姜文、葛优和李雪健等演员,后来还是没成。
事隔7年,人艺重排《茶馆》,新的导演、新的演员、新的舞台设计,这个被称为“林兆华版”的《茶馆》新剧组几乎处在暴风眼,一举一动都被观众、媒体以及整个文化界关注。它曾引起的讨论,不身处那个时代恐怕很难想象。评价的各种声音扑面而来时,暴风眼中的当事人,感受不尽相同。杨立新记得当时“基本上是负面的”。“观众说,别再糟践这个戏啦,给我们留个完整的好印象吧,干脆让它以一个完整而辉煌的形象保留下去吧!”多是这样的言辞。濮存昕也记得当年的确没有收到太多表扬。他当时去请了黄宗江来看,这位德高望重的作家看完后只说了“不易”二字。当然,“你们居然敢弄新版《茶馆》”,舆论当中最多的还是这类声音。林兆华当时还感慨,对梁冠华他们年轻一代的表演的肯定,大家太吝啬了。
林兆华版《茶馆》总共上演过的次数很少,2005年,《茶馆》去美国巡演,两个版本中,最终走出国门的还是“焦菊隐版”,从此大家看到的《茶馆》舞台基本回归到了1958年初创时的形态。好在经过这一次重排,演员保留下来了。
北京市社科院文化所副所长高音看过1992年那轮封箱演出,在她记忆中,那版《茶馆》,开场著名一幕“喧嚣而壮阔,拥挤却有序,充满了市井气息和老北京风味”。高音能代表《茶馆》观众中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观戏、研究戏,经验丰足,同时又极热爱《茶馆》,“没事儿时家里就放着《茶馆》视频,听着声儿”,对焦菊隐版《茶馆》可谓熟稔至极。从他们的视角看当时的林版《茶馆》,感到有不及也在情理之中。20年后的这轮演出,高音咂摸出许多好来,比如,她注意到,经过这么多年,杨立新在扮演秦二爷时又有新东西,“他没有完全模仿蓝天野,而是加入了自己很细微的设计”。最后一幕仨老头儿在《茶馆》会面,高音看得真切,秦二爷讲话有点哆嗦,舌头在嘴里打转,节奏也有变化,“他最后离开《茶馆》的时候,第一步是迈不上去的”。
蓝天野在一次采访中跟我谈到1958年3月份,北京人艺初排《茶馆》时的情形。“老舍先生偶尔也来,说一点儿,但从不多说。但对演员很有启发。他跟童超(扮演庞太监)说,这角色,应当是阴柔,不是阳刚。就这么一句话。”
所以濮存昕这一代人最感慨的是,上一代演员在排练《茶馆》时,老舍和焦菊隐先生两位创作者都健在,可以跟他们交流。在讲究体验生活的北京人艺,童超曾去鼓楼大街寻着过还在世的太监,蓝天野就近观察过不少民族资本家的生活,而如今,只能从资料与影像中复刻与想象那个时代。但好在,他们从年轻时就看着《茶馆》成长。对于一部保留剧目来说,这种言传身教式的传承尤为重要,这也是梁冠华最遗憾之处,他开始进入王利发这个角色时,于是之先生因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已无法与他沟通。
正是这拨当初饱受争议的演员,把《茶馆》继承了下来。如今演了20年,回过头去看当年,濮存昕的感觉是,“还是挺有差距的,但那时候我们真觉得挺好的,觉得自己还是拿下了角色”。观众慢慢地就抢着买票了,这些年,买票队伍越来越长,近五六年每逢《茶馆》开票,头天傍晚人艺售票窗口就有人开始排队,一排就是通宵——这是互联网时代几近绝迹的观戏热忱。
 何以经典
何以经典
1956年,老舍创作完毕三幕话剧《茶馆》。这年年底,老舍在北京人艺205会议室为全体演员朗诵他的剧本,蓝天野在他的自传《烟雨平生蓝天野》中记录过这一天,“他一边念一边讲,有时候还站起身来比画”。角色就这样分了下去,蓝天野分到了秦二爷这个角色,当时林连昆还跟他表示了羡慕,“你可摊上个有趣的好角色了”。
而导演焦菊隐则要求演员们去体验生活、做人物小传。蓝天野跟扮演庞太监的童超创作过一个体现人物关系的小品,名字叫《鹌鹑斗》,讲秦二爷与庞太监如何在语言上互相挑衅。小品在戏外补充的是戏中第一幕:二人在茶客们的围观下,来了一场暗流汹涌的机锋对话。后来杨立新拿二人这短短的碰面分析秦二爷的身份。“庞太监说:‘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秦二爷什么话呢,他说‘我早就知道’。请注意这句话,我早就知道,这当中可能有几个意思,我早就知道他们弄不起来,政治改良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也可能是,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想法,我早就知道你们能下这样的狠手,我早就知道他们政治改良这条路走不成,剩下什么?实业救国。”
老舍安排两位人物碰面,秦二爷未点明的政治立场即刻呼之欲出,他与后来都不再有交集的庞太监之间,该是什么关系呢?蓝天野与童超准备的《鹌鹑斗》小品,后来时常被用作例子,来说明《茶馆》最初排练时,演员们在体会人物时付出的心力。这也从侧面说明,北京人艺的这部《茶馆》成为经典,自有它的缘由。
《茶馆》上演后的第一个20年,中间掺杂了“文革”的风风雨雨,等到1978年人艺决定复排,老舍与焦菊隐两位先生已然离世,靠着原班演员和导演夏淳,《茶馆》得以保留,并一直演到了1992年。
1958年首演至今,《茶馆》两版已走过700多场,去到过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北京,新版“松二爷”冯远征的观察是,从前观众也很热情,但从最近五六年开始,总有观众头天晚上就开始排队,看完了演出也不肯走。
究竟是什么在持续地吸引观众?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陶庆梅近距离研究戏剧多年,她把北京人艺的话剧(或者说中国话剧)分为两条线:一条线是曹禺的,偏知识分子方向;另一条则是偏市民的,《茶馆》即其中最典型代表。
陶庆梅认为,今天中国的戏剧市场把戏剧当作太高雅的东西,这种偏见导致的结果是,整个戏剧的表达愈发狭窄,“像波兰导演陆帕的戏、立陶宛OKT剧团的戏,受到文艺青年追捧,认为它们了不得。但那样的戏,显然是脱离中国普通观众的”。在她看来,知识分子口味的戏剧作品更偏重感受与思考,这种戏当然应该有,但当下中国话剧市场,恰恰缺乏像《茶馆》这样更贴近普通人生活感受的“市民话剧”。“老舍笔下永远是那些从事着各种职业的人,它所包含的面向非常宽广。对这个宽广的普通老百姓的普通生活,老舍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关怀。而这种关心,今天的市井百姓仍然能感受到。老舍戏剧和文学创作中这个重要构成,是它今天仍有生命力的原因。”
北京人艺另一部戏《窝头会馆》近几年在观众当中也拥有极大号召力,这一事情倒能佐证陶庆梅与本刊分享的观点。这部作品的故事发生在建国前北京南城的一处小四合院中,几位主要人物无一不是普通北京市民,他们性格当中的较真儿、刻薄与圆滑,又全都是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会有的小缺点,整部戏展现了“老北京的杂陈,底层人的盘算,市井里的幽默和粗鄙”,这些都叫观众感到亲切。对普通人来说,过去时代发生的故事,因为那一股热融融的关怀,而与当下生活产生了联结。《窝头会馆》每轮演出的票房,也早就证明了它受到的喜爱是何等热切。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与《茶馆》共有的那个“关怀普通人”的内核,为它们在今天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老舍的文本之外,焦菊隐的舞台艺术当然功不可没。第一幕一开场,几张八仙桌错落排布,王利发在不同桌子之间游走,“确实像舞蹈一样优美”,这种行走方式,以及每位人物的登场,都借鉴了中国戏曲的元素,而这些符合中国人对戏剧舞台想象的方式,“使得舞台的时间与空间都被很美的表演充满”。观众获得的大量愉悦的源头正是在此处。陶庆梅因此总结,焦菊隐的审美与老舍的内在关怀,这是《茶馆》今天仍然立足不衰的最基本的原因。
经典可以动吗
从1958年初排到90年代林兆华重排之前,30多年中,除了北京人艺,没有其他剧院排演过这个戏。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老《茶馆》精致精巧,小角色都是大演员,过去的戏又都在观众脑子里,想突破非常困难。
林兆华当年为了重排《茶馆》,费了很大心思作调整。他打破原来单一的《茶馆》封闭空间,在舞台上拾整出两条街道,为老裕泰茶馆添几位街坊,这些老字号进一步展示出老北京历史风貌。甚至,他还设想过删掉群戏,将时间更凝练地集中在仨老头儿身上,表现他们的意识流动,让王利发回忆过去,再回到现在,以期让舞台和表演更自由——这一步只停留在了设想中。
即便作为北京人艺的大导演,重排也受到剧院与前辈的支持,林兆华排演的《茶馆》后来上演的次数也很有限。2005年,《茶馆》去到美国巡回演出,恢复了“焦版”,“林版”就此搁下。如今又一个20年过去了,随着濮存昕这一代演员年岁增长,“《茶馆》第三代如何接班”成为许多人关心的问题。
刘麻子和唐铁嘴两个角色,二代演员是何冰与吴刚,都是北京人艺如今最出色的演员,这两年他们的角色逐渐由更新一代的雷佳和闫锐接替。冯远征倒仍在扮演松二爷,作为人艺演员队队长的他告诉本刊,剧院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计划,找什么人,接谁的班,只不过“能够一对一接班的人还没有到齐”。显然,为仨老头儿找到合适的出演者,并非易事。
《茶馆》将来面临的挑战,倘若说有,最大的可能还是演员。正如当年濮存昕他们年轻时曾面对的挑战,未来一代或许也将在万众期待里挣扎与成长。与承接经典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摆在戏剧人面前:经典可以动吗?
对《茶馆》这个文本来说,它既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也是以同一幅模样上演了60年的剧目。从保留剧目的角度来理解,保持连贯、不变的演出,其实无可争议,比如2015年,俄罗斯亚历山德琳大剧院曾带着果戈理代表作《钦差大臣》到中国演出,陶庆梅看得很仔细,她发现该剧院的这部保留剧目,其实也维持着1926年梅耶荷德版本的基本形态,微调的部分有限。
“保留剧目最大的好处在于对演员的训练,对表演风格的继承”,《茶馆》之于北京人艺,其中一项重要职责便是以经典剧目为通道,将表演风格传承下去。只不过,铁打的《茶馆》,面对的是流水的观众,他们只会与戏中时代越来越疏远,捕捉台下观众的反馈,适当微调表演,倒的确是压在演员与复排导演身上的重担。
杨立新从2014年开始承担《茶馆》的执行导演,他告诉我,他对第一幕做过些许调整,比如让跑堂送面的早些出来,在台上多跑一个来回,原本从边上出来的李三,改到从中间出,“要是怕撞上就躲开,这一躲不显得更热闹吗?原来嘴上说的多,走动的少,不够热闹”。
一面是北京人艺自己对保留剧目的微调,另一面则是广大戏剧人对《茶馆》的实验性改编。陶庆梅觉得,面对经典,有两种倾向值得警惕。一种是,它是传统的、最好的、不可触碰的,另一种是,这么多年一直这么演,那是不行的,要创造。这两种倾向都没有必要。或许最适合的平衡之法,是让经典的归经典,让实验者归实验。
2017年,“80后”话剧导演王翀创作了《茶馆2.0》,用中学生做演员,用“教室”这个故事环境重划人物关系;同年,李六乙导演了一出四川话版的《茶馆》;2018年,更有孟京辉对《茶馆》的颠覆性改编。这个创作于大半个世纪前的话剧文本,与现实发生了更多关联。
高音告诉本刊,2018年孟京辉在乌镇戏剧节推出的《茶馆》,其具有实验精神的剧场实践太值得关注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从老舍《茶馆》这一母体上长出来的新生事物”。站在当代戏剧文学的财富之上,改动经典,或许也是另一个满足观众的渠道。
(实习记者王雯清对本文亦有贡献) 杨立新于是之濮存昕林兆华蓝天野中国电视剧戏剧爱情电影智利电影老舍茶馆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