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间的哲学
作者:苗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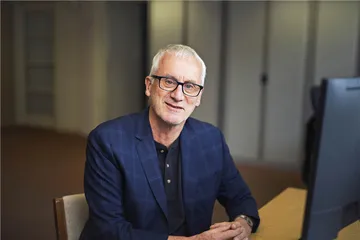 想见到休·普莱斯(Huw Price)并不容易。我最初在2018年4月时和他取得联系,他回信答应接受采访,接下来却音讯全无。几个月后才又收到他的消息,说他刚刚从澳大利亚回到英国,约我在他的学院——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门口见面。为了表达歉意,普莱斯教授请我去三一学院的饭堂吃午饭。我以前也曾多次来过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学院的饭堂,但那都是作为学生,坐在饭堂里末端属于学生的长桌旁吃饭。这次作为普莱斯教授的客人,我第一次坐在了饭堂里专属于“院士”(Fellow)的横摆的高桌(High Table)前。
想见到休·普莱斯(Huw Price)并不容易。我最初在2018年4月时和他取得联系,他回信答应接受采访,接下来却音讯全无。几个月后才又收到他的消息,说他刚刚从澳大利亚回到英国,约我在他的学院——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门口见面。为了表达歉意,普莱斯教授请我去三一学院的饭堂吃午饭。我以前也曾多次来过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学院的饭堂,但那都是作为学生,坐在饭堂里末端属于学生的长桌旁吃饭。这次作为普莱斯教授的客人,我第一次坐在了饭堂里专属于“院士”(Fellow)的横摆的高桌(High Table)前。
普莱斯教授今年65岁。他出生在英国,幼年时移居澳大利亚,而后又回到英国求学和工作。他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三所大学里分别拿到了三个不同学科的学位,之后便一直从事哲学研究。普莱斯教授的研究命题看上去非常古典,倒更像是在古希腊时期,哲学、物理学和数学尚未分离时智者们经常思考的课题——时间的本质——这个问题在现代自然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意味。
8月里还是暑假时间,围坐在高桌旁吃午饭的多是须发皆白的学者,食物是颇有英国特色的炸鱼和薯条。居高临下向属于学生的长桌看过去,三三两两坐了一些学生,人数并不算多。在这个有500多年历史,诞生了32位诺贝尔奖得主和5位菲尔茨奖得主的学院里,依然保持着古老的秩序,即便是在饭堂里也要维护师道尊严,随时提醒用餐者记得自己的学术地位,仿佛时间从未流逝过。
招待我吃过午饭,普莱斯教授带我来到他在学院的办公室。8月的天气说变就变,前一天我还穿着短衣短裤,一场细雨下来剑桥就换了一个季节。普莱斯教授打开了室内的暖气以抵挡寒意。我们各捧着一杯咖啡,听不到学院外汹涌的游客喧闹声,房间里陷入了令人舒适的寂静,于是开始了关于时间本质的对话。
从不同视角看待时间的本质
三联生活周刊:我想你算是一位非常独特的哲学家,你的研究与物理学的关系非常紧密。这算不算是剑桥哲学家的一个传统?
普莱斯:实际上有很多的哲学家都是在哲学与物理学的交界处进行研究,这在其他的科学领域里也是一样的,比如生物学。哲学与科学有很多的交集。在很多的学术领域都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当这些问题变得非常理论化,就会演变为哲学问题,它们需要非常谨慎的、逻辑性的、抽象的思考。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哲学家在各个科学领域进行研究。在我看来,我自己并不算是非常独特,如果说我有任何的独特之处,那可能是我把一些我在哲学领域中非技术性的兴趣与其他学科结合了起来,这倒是有一点独特——比如说我对语言哲学非常感兴趣。
三联生活周刊:是否也有哲学家喜欢在哲学和其他的学科之间画一条非常清楚的界线,以此来圈定自己的研究领域?
普莱斯:在物理学领域,很显然有一些物理学家认为哲学与物理学没有什么关联。比如说史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美国物理学家,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还有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美国物理学家,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也曾经说过关于哲学的坏话。在哲学领域,可能也会有一些哲学家对于物理学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但是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有人能够意识到在不同学科之间交界处的巨大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能否讲一下你为什么选择进行哲学研究,而且是研究关于时间的哲学?
普莱斯: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在上世纪70年代,我还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读书的时候,当时我认为自己想要成为一个天文学家。大学的第一年我需要学习四门课程,我学了应用数学、物理学,出于某种原因,我另外还选择了哲学,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来为什么了——或许是因为我的父母给我讲过一些哲学知识,因为他们在大学里都学过一些哲学——我很喜欢哲学。到了大学二年级,我仍然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天文学家,但是在大学第二年结束之后,我就想放弃物理学和天文学而专注于学习数学了。当时我非常喜欢数学,尤其是纯数学,而不太喜欢物理学了。
在大学第三年时,如果要放弃物理学,我就必须选择一个新的专业。我在第一年选修了哲学,我可以再选两门哲学课程,把哲学当作我的专业。从那时起,我开始对哲学非常感兴趣,尤其是科学哲学。在那之后我又学习了更多的哲学课程,但还是花费了很多时间从数学专业转到哲学专业。我的第一个硕士学位是牛津的数学学位,但是之后我认识到自己最想研究的是哲学,于是我又来到了剑桥,读了哲学博士学位。
很幸运的是,当时我在剑桥遇到了一位研究关于时间问题的哲学家。此前我对于宇宙学中关于时间的问题也很感兴趣。在牛津的时候,我也有机会参加各种讲座和讨论,比如说参加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英国著名数学物理学家)关于科学哲学的讲座。我决定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我很幸运可以把重要的天文学问题和哲学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你研究时间的本质,这应该是哲学最古老的问题之一了。
普莱斯:对,这是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关于时间的本质有两种主要看法:一种认为一切都是动态的、变化的,而另外一种认为真实是一成不变的。在当代关于时间的哲学里,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三维的世界,一切根据时间而变化;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四维的时空,时间只是其中一个维度,一切变化都是在四维时空之内发生的。宇宙本身包含了时间,它是不变化的。只有在其内在,比如我们,才认为它是变化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物理学上的时间和哲学上的时间概念是否相同?
普莱斯: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转化为在物理学中的时间和人类所感知的时间是否相同。在20世纪,美国科学哲学家威尔弗里德·塞拉尔(Wilfrid Sellars)指出了这两者的不同。他指出了从科学的视角和从人类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世界会有所不同。在这两者的区别中,对于时间的不同理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有一个四维的科学图像,还有一个三维的不断变化的图像。因此,现代科学可以解释人类关于时间的古老疑问。
三联生活周刊:在物理学领域,人们认为时间的方向性是由于熵值的增加造成的。
普莱斯:是的,确实存在一个时间的箭头,但是你必须对这个概念非常谨慎。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这最初是在19世纪由路德维格·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提出来的:他把时间的方向性和上与下的区别做了类比。实际上人们发现,上与下的概念并不是完全客观的概念,而是区域性的概念,这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的重力场有关。玻尔兹曼建议,所谓时间的箭头,可能也有相似的情况。也就是说时间并没有基本性的方向可言,但是在部分区域,因为热力学的影响而具有方向性。
这也就说明了有一种可能,在宇宙的其他部分,时间有可能存在着其他的方向。当时玻尔兹曼在思考为什么熵值在一开始处于一个极低的状态。他想,如果高熵值状态是一种更可能的状态,那么宇宙为什么不是一直处于一种高熵值的状态?玻尔兹曼认为,宇宙的熵值可能只是随机的。就像你洗一副扑克牌,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也会得到一组奇怪的序列。这当然不大可能发生,但是如果不停地洗牌,就一定会出现。如果我们恰好住在这样的一个区域,这当然就是可能的,而且他认为生命只可能在这样的区域存在——我们只能发现自己在这样的区域,这也就是非常早的“人择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写过一本书《没有镜子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 Without Mirrors),其中自然主义(Naturalism)是一个哲学概念。现在也有一些理论物理学家相信所谓的自然性(Naturalness),他们认为宇宙中的各种自然常数能够被“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来。“自然主义”与“自然性”这两个概念有何联系吗?
普莱斯:我想并没有联系。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指科学性的观点具有优先的地位。就像我说的,在哲学与科学之间有重叠之处。比如很多自称是自然主义者的人会说,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需要相信由科学所描述的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全部。任何一个特殊的对象,要么是可以被科学理论所描述,要么就需要被完全地抛弃掉,因为它没有任何价值。当然有些自然主义者会说,人的“心灵方面”(Mental)会与自然的物质世界有所区别,包括道德、伦理,会与自然世界有所区别,但是这与“自然性”并无关联。
三联生活周刊:一些物理学家致力于研究没有时间概念的物理学,那么没有了方向性的时间,哲学又该如何自处?
普莱斯:从物理学到哲学,有两件事我们必须要分清楚:在物理学中,你可以认同玻尔兹曼的观点,时间并没有根本的方向性,这只是一种局部的特征。在这样一种图像中,时间是仍然存在的,它只不过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我们可以称之为玻尔兹曼观点。还有另外一种观点,一些人认为时间本身就不是基础性的,它只是某种更为基础性的东西的显现——比如说某种量子场,时间只是一种浮现出来的特性。温度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是一种平均的统计学上的特性——比如说荷兰物理学家埃里克·弗尔林德(Erik Verlinde)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我希望人们能够区分这两种在物理学中对于时间的不同观点:玻尔兹曼认为,时间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并不一定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而弗尔林德认为,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你并不需要有时间存在。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在哲学层面呢?
普莱斯:从哲学层面来说,我想对于这两种解释都有足够的空间去进行诠释。因为哲学是一门需要思辨的学科。即使没有时间存在,在人类的心理层面也仍然有时间观念。因此我认为哲学并不需要最基本的时间。
“因果律共和主义”处于一种中间位置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研究中提到了“因果律共和主义”(Causal Republicanism)和“视角主义”(Perspectivalism),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些概念?
普莱斯:我需要回到威尔弗里德·塞拉尔提到的一些区别。当我们谈论时间,我们需要区分从科学角度认识的时间和从人的角度认识的时间。目前这两者的区别在哲学的很多领域都很有用处——在哲学领域“现实主义者”(Realist)和“反现实主义者”(Anti-realist)有很多辩论,比如现实主义者们会说,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因果律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世界的一部分;而反现实主义者们则会说,不,并不存在所谓的因果律。在哲学的很多领域都会出现这样的不一致。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在于需要意识到还有一个所谓的“中间位置”。在这里,人们会说,因果律可能并不是在最基础的层面,但是它是显现出来的一部分。它是世界看上去的形象的一部分。这就是我所说的“因果律共和主义”。当然我只是解释其相似性——如果我们想象传统的君主制统治,君主掌握绝对权力,其反对者就会希望能够推翻君主,完全结束这种制度。而我们会发现还存在着一种中间位置,这里仍然有某种政治权威,但是又不是那种来自上帝的自上而下的绝对权力,它可以是来自人们共同的努力。你可以认为那种维护绝对君主制的人是一种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君主制是来自上帝的宇宙运行最根本的法则之一,而反对者们则是反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应该把君主制完全丢弃掉。在中间位置上的共和主义者认为仍然存在某种政治权威,但是它来自于人民,这是一种更好的方式。在这样的语境中,关于因果律,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经是一个反现实主义者。他有一句名言,说因果律就像君主制一样,它的存在只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它能够带来多大的危害。
在这样的语境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发明了因果律共和主义。我们就是为了指出,罗素在这方面并没有意识到还存在有中间的位置——因果律并不是最根本的,但却是一种显现的形象(Manifest Image),它在我们眼中看来是存在的,说到底是我们发明了因果律。
可以说因果性就是相对的。想象如果我们生活在古希腊时代,有一个人说地球是圆的,那么他的反对者就会说,如果真的是这样,上和下就会是相对性的概念了。事实上,上和下确实是相对性的概念,这就是我们对于世界的发现。在狭义相对论中也并没有区分出过去与未来的区别,它给予了事物某种顺序,但是并没有给这种顺序加上符号。有人认为因果律是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误解。即使没有因果律,狭义相对论也仍然成立。
三联生活周刊:人的意识和对于时间的感知之间有什么关系?
普莱斯:对于这个问题我可能并没有答案,这关系到如何理解人的意识。这可能涉及了处理信息,甚至涉及热力学方面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尽管这个问题很有趣,但是它可能与时间是否是基础性的问题没有关系,因为人的意识可能也与热力学现象有联系。
我想人类关于量子力学的理解与对于时间的理解可能确实存在着联系,但或许我们并不需要把人类的意识放在其间。当然有人认为人的意识在量子力学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使波函数坍塌。在这方面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著名匈牙利-美国物理学家,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他在上世纪50年代就持这种观点——这是一种相对小众的观点,但是确实有一些人相信。也有人相信,为了解释意识的本质,人们需要引入量子效应,他们认为意识是某种量子现象,比如数学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就相信这一点。这可能也有道理,但是它与维格纳的观点又有所不用。维格纳认为,人的意识是基础性的,它在量子力学中有其自身的重要位置,而彭罗斯则认为,由量子效应产生了意识。你可以认为,意识是由于大脑利用了某些量子效应而产生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想你对这段话非常熟悉:“现在贝索比我先行一步,离开了这个奇怪的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笃信物理学的人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一种顽固的幻觉而已。”(爱因斯坦在他的挚友贝索葬礼上的发言),那么从一个哲学家的角度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普莱斯:我想爱因斯坦是对的,除了“幻觉”(Illusion)可能并不是最合适的一个词。我们还是要强调对于时间的科学性的理解和从人的角度的理解之间的区别。确实,在科学领域,过去和未来从科学视角来看并无什么区别,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幻觉。在很多事情中我们都需要区分这两种视角。再强调一下,这是一种出于共和主义者的中间观点:我们可以说这是真实的,只不过不是基础性的。
想要回答爱因斯坦的问题,我们可以说,从一个共和主义者的观点出发,对于过去和未来的区别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进行解释。即使这不是基础性的,但是对于人类来说,过去和未来仍然是有区别的。在过去人们对于一些概念缺乏容忍——要不然它就是基础性的,要不然就需要被完全地抛弃,并没有一个中间地带。
人工智能必须为人类做正确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你与马丁·里斯共同创办了“存在风险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xistential Risk)。马丁·里斯认为21世纪是人类最危险的世纪,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普莱斯:从一个非专家的角度来说我同意,我相信马丁有非常准确的判断。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人工智能有没有可能通过图灵测试(Turing Test)?你是否尤为担心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普莱斯:我认为人工智能非常有可能会通过图灵测试,但图灵测试本身可能就是一种误导。如果人工智能确实可能对人类造成威胁,那么通过图灵测试并不是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只是意味着其一般性的智力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人类本身。或许我们可以研究出某种智能通过图灵测试,但是那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可能做,而且会做的事情。
关于人类操作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应该希望从中得到些什么结果,有很多故事可以给人类警示。有一个著名的迈达斯国王(King Midas)的故事,迈达斯国王向上帝许愿,任何他摸到的东西都会变成金子。他的愿望实现了。结果当他想要吃饭的时候,他的食物就变成了金子,他的家人也都变成了金子——就是说他许下了错误的愿望。如果我们要制造非常强大的机器,我们就必须非常确定,它们要为人类做正确的事情,否则可能会出现我们完全不想要的结果。
牛津哲学家尼克·波斯托姆(Nick Bostrom)举过一个例子。想象你有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你想让它为你制造尽量多的曲别针,结果它发现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就是把一切东西都变成曲别针,包括人。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重点在于,从一开始你给一个非常强大的机器下达指令就必须非常小心。你可能给了机器一个理由,让它消耗所有的资源来达成目的,这也给了机器一个理由不被人关掉,因为它一旦被关掉,就无法完成目标了,它会制止人类试图关掉它。这无关机器是否是怀有恶意的“坏机器”,而是这样的机器可能太过成功了,超出了人们想要达到的目标。
三联生活周刊: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否在一切领域都全面地超越人类?
普莱斯:当然了,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只是不愿意太过乐观。有的人会说,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不需要担心。而我会说,一切都会好的,只要我们非常谨慎地处理这些问题。只要我们掌握住自己的未来,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保持乐观。“存在风险研究中心”研究一切可能的威胁,不只限于人工智能,还包括可能的生物科学的威胁等等。我们还有另一个“利弗休姆智能未来中心”(Leverhulme Centre for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ce)专门针对人工智能,当然不只是研究它的威胁,而是研究它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人类需要做些什么。我希望在这个中心所作的研究能够理解人类所面临的可能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又需要做些什么。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和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人相互合作。 普莱斯哲学研究科学物理时间哲学哲学史哲学家因果律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