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友谊”都被他解剖了,我却不敢断言他的性别
作者:孙若茜女性友谊从来都是复杂的话题,复杂到让人产生怀疑:是否真的有这种东西存在?
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小说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探索通常是过于简略的。简略到只能让人看见女性友谊的伫立,却无法看清究竟是什么搭建了它,是明亮的,还是暗黑的。少有人向我们展示女人间的友谊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少有人愿意去直视那些在暗地里供养它的成分,比如嫉妒,比如伪装,比如很可能在一开始就存在的背叛,它们容易被认出,因此更容易被回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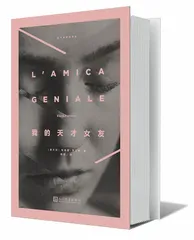 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作品《我的天才女友》
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作品《我的天才女友》
而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作品——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四本相互关联的小说:《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在描述主人公埃莱娜和莉拉这两个女人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友谊时,恰恰指向了那里。作者就像在进行一场解剖,把“友谊”这个缥缈的个人化的概念,还原成为那些构成它的东西。
《我的天才女友》是其中的第一部,按照时间线索,里面的故事来自童年和青春期,她们友谊的开端正在其中:“那天我们坐在地下室的有破洞的通风口旁边,我们交换了娃娃,我拿着她的,她拿着我的。这时候,莉拉不动声色,把我的娃娃从通风口的破洞那里扔了下去。”“我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平静地做了一件事情,就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尽管我的举动并不自然,我知道我在冒险,我只是把她的玩偶,她刚刚交给我的诺也扔到了地下室里。”——“你怎么做,我就会怎么做!”接着,为了捡回玩偶,她们一起奔向了充满黑暗和恐惧的地下室。
这就是埃莱娜和莉拉正式开始交往的片刻,友谊的起点。这样的起点充满了暗示:不管这两个女孩在之后的几部书中终究变成怎样的女人,过怎样不同的生活,她们之间的友谊大概终将沿着它初生时的这般姿态去生长,维系——那种亲密的牵连中,将始终暗含着较量、背叛乃至暴力。
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小说《新名字的故事》中,当已婚的莉拉把自己记下所有秘密过往的笔记本交托给埃莱娜保管后,突然有一天,埃莱娜无法控制自己地走出了门,她在索尔费利诺桥上停下来,将装满莉拉笔记的盒子放在栏杆上,“用手慢慢地把铁盒向前推,直到盒子落入河里”。然而前几天,她还在毫不犹豫地偷看,然后沉迷、钻研,甚至于背下来自己喜欢的片段。
这一刻,埃莱娜的动作和将莉拉的玩偶扔进黑洞时如出一辙,依然不能自然。表面上她的动机截然相反,上一次是在有意地模仿和主动地被莉拉影响,这一次是企图抹掉对方在自己身上所造成的影响,然而“坠落”一旦发生,她的行动在本质上却再无两样。
费兰特曾在散文集中这样解释他笔下这两个女孩的情谊:“在莉拉和埃莱娜的生命中,有很多事件显示了一个人如何从另一人身上汲取力量。但要记住这一点:不仅仅是在她们帮助彼此的层面上,同样也体现在她们互相洗劫,从对方身上窃取情感和知识,消耗对方的力量。”彼此帮助又相互洗劫,这才是真正的所谓女人之间的友谊。
蕾切尔·多纳迪奥在给《纽约书评》的文章中评价费兰特的“那不勒斯”系列及其以往的写作时说道:“这些故事带着血迹、谋杀、经血,同样还有泪水和汗水。”从1992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讨厌的爱》开始,费兰特所写的《被遗弃的日子》《遗失的女儿》等等小说,几乎都是在关注处在不同人生阶段和不同境遇下的女人。“将这些作品归为‘女权主义’作品是准确的,虽然这也许是一种简化。我们完全可以说,(费兰特的)这些作品探索身为女人的完整经历中那些私密的甚至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细节,以及在那不勒斯系列中,探索女性友谊的深刻复杂性时所带有的审视和强度,是当代文学——可以说是任何时代的文学——少有的。”
而这并不意味着费兰特的小说仅仅是写给女人的。多纳迪奥还给出了一种很棒的解读:“费兰特的那不勒斯系列本质上是关于知识的小说——关于知识的可能和局限。智性的知识,关于性的知识、政治知识。我们需要哪种知识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来?我们又是如何获得那种知识?我们拥有的知识又是如何同时改变我们、伤害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我们想要知道什么,又宁愿永远不去知道什么?我们能控制什么,又是什么在控制我们的生活?”
同样,女性视角的写作就意味着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位女性作家吗?我们无法确定。
因为根本没人知道埃莱娜·费兰特究竟是谁。虽然,大家几乎一致判断他(她)近乎自传性的写作明确了其女人身份,但始终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这个在意大利文中并不女性化的名字不过是印在书上的一个符号。自从它进入读者的视野,20多年过去了,它背后依然只走出了作品,而并非具体的人。我们不只不知道费兰特的性别,甚至都不能确定费兰特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
1991年,费兰特在给他的出版方E/O出版社的信中清楚地表明过匿名写作的初衷:“你知道,要解释我的这个决定很难。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我和我自己、和我的信念的一次赌博。我相信,书——一旦被写出来就不再需要他们的作者,如果它们真的足够好,它们迟早会找到自己的读者;反之则不会。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我很喜欢这些神秘的作品,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它们的作者并不确定,但却拥有一种持续的生命力。在我看来它们就像夜间的奇迹,是贝法娜的礼物,我就像一个孩子那样满心期盼等待着。……此外,难道推广不昂贵吗?我会是你们出版社成本最低的作者,我会让你免于这些费用。”
如他(她)所说,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勃朗特姐妹、凯瑟琳·厄休拉·陶勒、多米尼克·奥利、玛塔·海勒斯,甚至也包括对埃莱娜和莉拉的童年非常重要的小说《小妇人》的作者路易莎·梅·阿尔科特等等。他们的作品最终都没有被忽视,而他们的匿名在起初也无外乎出于躲避,躲避社会对写作者性别的歧视,躲避具有争议的写作内容引起的非议,躲避敏感主题带来的审查,躲避媒体因为自己已有的名声而忽略作品本身发出的评价……
费兰特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也提到过,很多有名的意大利作家都在高校任教,“好像文学不能借助文本自身来展示其严肃性,而只能靠外部声誉获得认可”。他一开始选择匿名是因为怯懦,而后来的坚持,是感受到了媒体在这方面的恶意。
“我并没有选择无名,我的书还是被签约出版,但我让自己远离作家们或多或少都要扮演的某些行为,通过让自己被消费的形象来让自己的书长盛不衰。这种套路现在还是有效的。”在接受《名利场》杂志的采访时,他这样说。
“匿名”要求他拒不参加任何有关自己书籍的会议,不出面回应讨论,不出席任何颁奖,仅有可能接受书面形式的采访。但他的作品还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找到了自己的读者,他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甚至引发了现象级的阅读热潮,这四本小说的全球销量目前已经超过了500万册。《格兰塔》甚至评价说:“如果你还没读过费兰特,就好比你在1856年还没读过《包法利夫人》……”
“我的书越来越宣告它们自身的独立,因此我想我没有任何理由改变我的立场。那会是可悲的前后不一致。”2015年接受采访时,费兰特对于匿名一事表示出了更加坚决的态度。2016年10月,意大利记者Claudio Gatti在《纽约书评》发表了《费兰特是谁,终于有答案了》:他试图通过查询房产记录和出版商的付款记录“人肉”出费兰特。感受了媒体的这又一种恶意之后,费兰特或许会更加神秘? 文学小说我的天才女友南非兰特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