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运两案
作者:卜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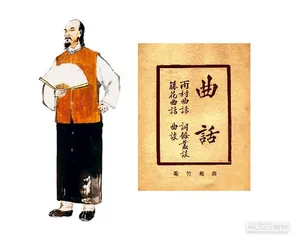 关于四库七阁的入藏,对于运送过程的记载较少,乃因关注点不在此处也。而由于乾隆帝要东巡,从四库总裁到军机处,也包括直隶总督、盛京将军都对文溯阁本的运输格外上心,计议周详,记载亦多。京师到山海关约700里,全为杠夫抬运,仅用11天就运达交接,应说效率可嘉。署直隶总督英廉接李调元禀报很满意,当即命他接着办理第二拨书籍的起程运送,会同内务府司员沿途妥善照料。
关于四库七阁的入藏,对于运送过程的记载较少,乃因关注点不在此处也。而由于乾隆帝要东巡,从四库总裁到军机处,也包括直隶总督、盛京将军都对文溯阁本的运输格外上心,计议周详,记载亦多。京师到山海关约700里,全为杠夫抬运,仅用11天就运达交接,应说效率可嘉。署直隶总督英廉接李调元禀报很满意,当即命他接着办理第二拨书籍的起程运送,会同内务府司员沿途妥善照料。京师与盛京之间官道贯通,设置驿站,配备车马夫役,为什么还要雇用抬夫?想来一则驿站兵役车马不多,需要保障军报公文的及时传递;二则官道的路况并不好,车行颠簸,为慎重起见,只能选择抬运。每拨以180抬计算,约需抬夫400人,由经行地方官提前雇备,按站给价,也是一份不小的花费。而发运时已然入冬,出关之际更冷,肩负沉重,行期复紧,少不得冲风冒雪,那种辛苦也只有亲历者所可感知。从山海关到盛京约800里,第一拨运输用了14天,也算正常,但在路上发生了不少情况,据伯兴奏报:
奴才奉命自山海关外交界处所接运,按站押送……其知州伊汤安、知县李廷扬、文良三员雇觅人夫,均各足数多余,运送亦皆整齐迅速。惟广宁县知县杨鹏翮界内人夫,不但不能多余整齐,且运至第三日行到平拉门地方,抬夫竟将书箱五六抬抛掷路旁雪地,逃散而去。奴才尾随督运,恰至其所,急行查问。见该县侍立道旁,面禀抬夫业已逃散,现在差役各处雇觅等语。奴才随面加斥责,令其作速雇觅人夫,飞行押送。后于起更时该县始行押运到站。奴才彼时即思具折参奏,不意于次日抬至新民屯地方,复将书箱数抬抛掷村内,并无一人照管。奴才行至其所,见之不胜恐惧。新民屯系人烟凑集、车马壅挤之处,所运书籍设或稍经触碰,关系匪轻。奴才即派随行驿丞在彼看守,俟承运官一到,即行催逼雇觅人夫,星速赶运,后亦更余方能到站。
场景鲜活,带写出监运大员伯兴的惊恐,亦四库书厄之一端。伯兴出身满洲镶黄旗,已任盛京兵部侍郎十余年,两个月前奉旨兼管奉天府尹事务(称“兼尹”),另有正三品的奉天府尹,秩在兼尹之下,所幸他办事较认真,不光是到山海关办理交接,沿途也一直跟着前后督察,总算没有出大纰漏。
经过此事,伯兴自不敢再用杨鹏翮,奏请将他交部严加查议,另派干员前往广宁县预备接运第二拨书籍。弘历阅后大为不满,认为该县竟两次发生抬夫抛弃书箱脱逃之事,可知杨鹏翮缺少管理地方的能力,诸事废弛,自应参奏革职,而不应“仅请交部查议,殊不知事理轻重”,命另行缮折参奏。伯兴接旨后“愧悚交至”,连忙会同奉天府尹奇臣参奏,请旨将杨鹏翮革职,并自请交部严议。这位杨知县也是个官场倒霉蛋:乾隆二十二年(1757)就考中进士,列于三甲,得了个待分配(归班铨选),等候约10年才得署任湘潭知县,再实授湖南首县长沙知县,像是快要熬出头了,却因在湘潭时对一件传播谣谚案追查不力被革职;接下来差不多又是10年,鹏翮获任锦州府广宁知县,又遇上这么一档子事,触发圣怒,再次遭遇革职。人常说性格就是命运,其实命运亦常被机遇操弄,同年进士如彭元瑞已位列卿贰,而他总是遇上不大不小的坎,就连个知县也坐不稳。
第二批文溯阁本的运送,十一月二十日自京起程,共计1491函,另有宝座、靠背、木椅及金玉铜磁陈设1438件。轮到关内段出事了,抬运民夫行至卢龙地方,突然雨雪交加,又缺少遮盖,造成一些书箱沾湿。沾湿,文档中也写作打湿,与淋湿、淋透有很大区别,应是飞雪造成箱子的表面有些湿,未及箱内书卷。永平知府弓养正、卢龙知县郭棣泰皆不在现场,闻知后赶紧做了些处置,在郡城找库房安放停当。而督运道员李调元因前晚在滦州喝酒看戏,并未随抬运队伍行进,得知后不免着急,即行禀报署直隶总督英廉,指责郭棣泰做事不认真,在书籍过境时“并不亲身照料,又不预备席片油单,适当雨雪交加,箱藤沾湿,幸内发原箱封裹紧密,得免渗漏。似此玩视差务之员难任姑容,理合据实禀请以才力不及纠参”。郭知县出身贡生,捐纳知县,曾在四库馆效力多年,期满后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选任卢龙知县,应属经验不足,遇到此等雨雪天气不免手忙脚乱。好在并无严重后果,若遇到宽容些的上司,训斥几句也就罢了。
李调元还是太书生气了,请求总督将属下知县解职,却不知此类报件应有知府合署。英廉以大学士暂署直督,精晓行文程序,应也看出端倪,不愿将属员争斗公开化,驳回令再查,其中已有提醒的意思了。怎知李调元一向不太尊重上司,倔劲儿上来,接着又递一本,将弓知府以“徇庇属员”一并劾参。这样一来英廉就没了回旋的余地,只能命布、按两司拟文。而就在这时,弓养正的报件来了,弱弱地反揭李调元的劣迹——
十一月二十五日,书箱由丰润起程,至滦州榛子镇,该州蔡薰预备大戏,该道即在彼宴饮住宿,并未随书前进,有内务府委官并护送各员可证。二十六日书箱已抵郡城,该府与该县将书箱安顿后始行往接该道,即斥其不行远迎。一入公馆,家人需索门包八十两,书办、承差、轿上人等各有使费,骑马不下四十匹。该县畏其威势,只得曲意顺从,如数应付。访查迁安、抚宁、临榆等处,无不皆然。该府后询之东路同知李汝琬,亦云三河、蓟州等处看大戏,要门包亦皆如是,每日所用木炭约至七八百斤之多。该道由山海关回至卢龙,该府与理事同知巴星阿禀见,犹余怒未息,责郭令不善办差,该府以理言解释不允,反被以徇庇同乡揭参。
此亦英廉的转述,虽未详记,可知李调元与弓养正必有一次正面冲突,也可推想双方都憋了一肚子的气。目前看不到李调元的原禀,但可以想象,他一定会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也会对当时情形详加描绘。英廉为当朝重臣,深知皇上出手必重,本来想压下此事,可自负的李道台不听,对其行为失范、心胸狭窄也有几分厌烦。他说郭棣泰的确是“玩误差务”,弓养正也显得“徇庇同乡”,应予参处;而李调元为官不谨,“骚扰地方证据确凿”,亦应调集人证,展开进一步的查证。
发生这样的碰撞是令人遗憾的。李、弓二人其实为同榜进士,是科甲出身者颇为看重的同年。李调元品学兼优,正直明爽,选庶常,留翰林,提督学政,颇得皇上嘉许,而新任地方监司大员,全不知如何管束下人,加上诗酒歌吟、酷爱戏曲的文人积习,不知不觉间就被带到了沟里。弓养正则先做县学教谕,已通过乾隆二十二年(1757)会试,因父丧6年后才得以参加殿试,复经过10年候任选授河南内黄知县,渐升为知州、知府,对生民之艰和基层官员之苦,比李调元的感受可就深多了。李调元瞧不大上他这个老同年,弓养正也看不惯李调元那牛哄哄的做派,是以隐忍不成,终至于决裂,撕扯得一地鸡毛。 李调元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