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的衣橱:“集大成”时代的服饰宝库
作者:丘濂 作为一位明代服饰的研究者,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蒋玉秋会抓住每一个和明代服饰实物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最近的一次,是她去了趟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刚刚结束的“孔府旧藏礼乐服饰文物特展”,专为再去仔细看看那套明代孔府衍圣公留下的红色朝服。这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传世朝服实物。
作为一位明代服饰的研究者,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蒋玉秋会抓住每一个和明代服饰实物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最近的一次,是她去了趟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刚刚结束的“孔府旧藏礼乐服饰文物特展”,专为再去仔细看看那套明代孔府衍圣公留下的红色朝服。这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传世朝服实物。朝服是用于隆重的大朝会或仪式中的一类冠服。它定型于汉代,历代相沿革,明代朝服则承袭唐宋之制。一套朝服是“上衣下裳”,由赤罗衣和赤罗裳构成。蒋玉秋此前在史料中看过不少描述,第一次亲眼见到它,是在2012年山东博物馆举办的“斯文在兹——孔府旧藏服饰特展”中,第一眼就深受震撼。“有一种大象无形、大美无言的感觉。这样官员礼服中规格最高的品类,反而是全素的。”这套朝服是“罗”的材质。“在绫罗绸缎中,‘罗’在织造工艺上难度极高。它和纱一样通透,却比纱要更重,能很好地垂坠下来。穿朝服的时候,内里还要再穿中单等几层。这样一层层叠加起来,我们就能想象它所形成的体量感和威仪感。”
每一次看到实物,都能让蒋玉秋思考一些服饰上的细节,而这些往往是在看照片时不太容易注意到的。“比如它青色的衣襟处冒出一个‘小尖’,其实那是通向里面一个长条的口袋,用来装象牙笏板。”整件衣服展示在那里,蒋玉秋充分感受到了它又长又大的袖子。整个通袖长达250厘米,袖子宽73厘米。“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这是考虑到穿上朝服来躬身抱手行礼的需要。如果是和手臂一样可丁可卯的长度,行礼时袖子必然会往上跑。唯有留出余量,袖子才能在行礼时像个四方体一样将人整体包裹起来,有种庄重的效果。”蒋玉秋给研究生开设了一门“中国古代服装复原研究与实践”课程,为的就是学生们在亲自动手仿制的过程中,体验一件服装和人体的关系,并且是放在古时的生活情境中,从而深刻理解古人的着装方式。
对于“汉服”的研究者来说,明代是一个材料最为丰富、感知最为直观、复原最为便利的朝代。这首先是源于明代有传世的服饰实物存留下来,这就比考古出土的服饰文物形制更加完整,色彩和纹样方面也更加清晰。这其中,最大的一批就来自山东孔府衍圣公家族留下的服饰。衍圣公是孔子的嫡长子孙的封号,始于宋,历经元、明、清、民国,直至1935年国民政府改封衍圣公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为止。孔子博物馆孔府旧藏服饰研究中心主任徐冉告诉我,孔府旧藏的服饰涉及了明、清和民国三个时期的服饰资料,当年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接管孔府文物时,在孔府后堂楼的阁楼内,发现很多樟木箱子就存放着这批衣物,其中明代的衣物有100多件。 明清易代时,明代的衣物基本上都随着“改易衣冠”等政治事件而被毁掉了。徐冉推测,孔府的这批明代衣物能够完好地保留下来,一是得益于衍圣公的地位,因为清代仍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工具,孔子后人的地位只升不降,对他们也就没有销毁前朝服饰这样苛刻的要求;另外孔府的“祭孔”仪式,也需要将先人的衣冠摆放出来进行祭祀,他们就会刻意去保留好前人穿过的服饰。这就造就了这批服饰保存完整妥善,色彩和纹样也是艳丽生动。现在这批服饰一部分在曲阜的孔子博物馆,一部分在济南的山东博物馆。继2012年的“斯文在兹”展览后,2020年山东博物馆和孔子博物馆还联合举办了“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这两次都算是“汉服”爱好者心中的大事件。尤其较早的那次“斯文在兹”展览,更成为早期爱好者的一次重要启蒙,得以首次目睹明制汉服的真容。
明清易代时,明代的衣物基本上都随着“改易衣冠”等政治事件而被毁掉了。徐冉推测,孔府的这批明代衣物能够完好地保留下来,一是得益于衍圣公的地位,因为清代仍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工具,孔子后人的地位只升不降,对他们也就没有销毁前朝服饰这样苛刻的要求;另外孔府的“祭孔”仪式,也需要将先人的衣冠摆放出来进行祭祀,他们就会刻意去保留好前人穿过的服饰。这就造就了这批服饰保存完整妥善,色彩和纹样也是艳丽生动。现在这批服饰一部分在曲阜的孔子博物馆,一部分在济南的山东博物馆。继2012年的“斯文在兹”展览后,2020年山东博物馆和孔子博物馆还联合举办了“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这两次都算是“汉服”爱好者心中的大事件。尤其较早的那次“斯文在兹”展览,更成为早期爱好者的一次重要启蒙,得以首次目睹明制汉服的真容。
除了孔府旧藏服饰外,还有一批明代的传世衣物是明朝万历皇帝对丰臣秀吉的赐服,他曾经被万历册封为日本国王。这批服饰藏于日本京都妙法院,已公开的有22件。 而如果要知道明代人穿什么衣服,还可以参考大量的明代写实风格的绘画。“宦迹图”就是其中的一种。“宦迹图”这种类型可以追溯到东汉的墓室壁画。在当时的官员墓室壁画中,会用描绘官员不同时期的车马出行图来反映他的升迁经历,从而显示墓主人的显赫生平。根据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的学者杨丽丽考证,到了明清时代,宦迹图的目的变为服务于活着的人,往往是像主功成名就后邀请画师来创作的,并且非常追求人物的逼真。比如故宫所藏明代的《徐显卿宦迹图》,就是万历年间吏部右侍郎徐显卿请画师余士和吴钺绘制的,一共包括26个画面场景,每个里面都蕴含有服饰信息。像“皇极侍班”这幅,就表现了皇极殿举行大朝会的情景,官员穿着的就是赤罗衣和赤罗裳。
而如果要知道明代人穿什么衣服,还可以参考大量的明代写实风格的绘画。“宦迹图”就是其中的一种。“宦迹图”这种类型可以追溯到东汉的墓室壁画。在当时的官员墓室壁画中,会用描绘官员不同时期的车马出行图来反映他的升迁经历,从而显示墓主人的显赫生平。根据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的学者杨丽丽考证,到了明清时代,宦迹图的目的变为服务于活着的人,往往是像主功成名就后邀请画师来创作的,并且非常追求人物的逼真。比如故宫所藏明代的《徐显卿宦迹图》,就是万历年间吏部右侍郎徐显卿请画师余士和吴钺绘制的,一共包括26个画面场景,每个里面都蕴含有服饰信息。像“皇极侍班”这幅,就表现了皇极殿举行大朝会的情景,官员穿着的就是赤罗衣和赤罗裳。
“宦迹图”在更大的类别上则属于肖像画,明代也是一个肖像画极其发达的年代,至今也有大量肖像画存世。到了明代中晚期,伴随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肖像画不再是属于帝后名臣、文人雅士的专利,而是普通庶民也可以花钱购买的一件商品。《中国传统服饰》一书的作者侯佳明曾经梳理过明代肖像画走向商业化的过程。她告诉我,明代人请人画像写真,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在于亡故之后供后世瞻仰。既然是要挂在家中享受后人祭祀,容象就注重写实,不仅面容精确,还要追求周身穿戴的还原。“明代的《醒世姻缘传》里就讲过一段故事,讲画师一定要遵从穿衣品级来为主人已过世的父亲画像。但这部小说是以明代前期为背景来写的,等到明晚期,则‘僭越’现象严重,这时的祖容象则依靠高于身份的服饰来‘升官’,真实性应当区别来看。”
有意思的是,尽管明代服饰的实物和图像遗留下来不少,今天一位普通人对明代人的服饰形象依旧很模糊。“大家对明代服饰‘好像很熟悉,又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Q版大明衣冠图志》的作者、北京十三陵特区明代帝陵研究会特邀会员董进(笔名:撷芳主人)这样对我说。“说‘熟悉’,是因为今天戏曲舞台的服饰就是以明制服装为基础的,大家多少脑海里都有个样子。而感到陌生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肖像画这类画作并不受到艺术史的关注,他们推崇的是文人绘画,大众认知的层次也就没有什么说出来都知道的画作。再加上影视作品的创作领域,也缺乏精准还原明代服饰的作品。”
不过,基于明代服饰在物质和视觉方面的可感知性,也就注定了只要稍加用心,一座服饰宝库就展现在眼前。 《红楼梦》中的人物衣着,据考证应该是明代服装样式。从左往右人物:鸳鸯、妙玉、林黛玉、王熙凤(黄宇 摄)孔府旧藏:明代“集大成”的缩影
《红楼梦》中的人物衣着,据考证应该是明代服装样式。从左往右人物:鸳鸯、妙玉、林黛玉、王熙凤(黄宇 摄)孔府旧藏:明代“集大成”的缩影
专注于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大家孙机曾提纲挈领地说过明代服饰的重要性:明代是汉族服装发展的最后阶段。明代服装既有对古代的继承,又有很多变化和发展。明代衣服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服装最后一个定格。
蒋玉秋形容明代服饰有“集大成”的特点。“这种‘集大成’的风貌是一种‘道器并重’的结果。一方面,明代在服饰制度上有一种始自顶层的设计——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上采周汉,下取唐宋,形成了大明王朝的衣冠制度,建立了一个‘上下有等,贵贱有别’的严密周备的服饰等级系统;另一方面,明代的纺织技艺在前代的积累上有了大幅提升。制度的持续更定和技术的日新月异,共同成就了明代服饰独特的时代特色。”
孔府旧藏的服饰则可看作明代服饰全貌的一个缩影。这批服饰包括男装和女装,在品类上几乎涵盖了明代服装的大类,并且涉及不同用途的着装。而从面料和织造工艺上,也代表着明代服饰所达到的水平。 董进参与了“衣冠大成”的策展,并专门为展览撰写了孔府旧藏明代服饰分类的文章。我们一般的直觉是,女性要比男性拥有更多的服饰选择。但董进告诉我,对于一位在朝为官的男性来说,他反而会因为各种场合的需要,而拥有更多的服装门类。“按照《大明会典》的记载,文武官冠服分为朝服、祭服、公服、常服、吉服、素服、忠静冠服几个大类。此外还有用于丧礼的丧服、征战或仪卫用的戎服,以及日常起居穿着的便服等等。”
董进参与了“衣冠大成”的策展,并专门为展览撰写了孔府旧藏明代服饰分类的文章。我们一般的直觉是,女性要比男性拥有更多的服饰选择。但董进告诉我,对于一位在朝为官的男性来说,他反而会因为各种场合的需要,而拥有更多的服装门类。“按照《大明会典》的记载,文武官冠服分为朝服、祭服、公服、常服、吉服、素服、忠静冠服几个大类。此外还有用于丧礼的丧服、征战或仪卫用的戎服,以及日常起居穿着的便服等等。”
这里面,容易混淆的是朝服、公服和常服三个概念。常服并不是官员日常穿的衣服,而是日常上朝穿的衣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圆领袍加上代表品级的“补子”的形象,圆领袍可以是红色、绿色和蓝色等不同颜色。孔府旧藏里有一件大红色暗花纱缀绣云鹤方补圆领袍,就是典型。衍圣公在明代品秩为二品,但有着“同一品”的待遇,因此可以用一品官员的仙鹤补。公服用于朔望日参朝,以及宴赏、谢恩、见朝、辞朝、谢假和加散官等时刻。朝服则是在大祀庆成、元旦、冬至、圣节等重大朝会穿着的礼服。从常服、公服到朝服,服饰的隆重性递增,穿着频次递减。
而对于女性,即使是官员的配偶、被君主册封过的命妇,由于出入场合有限,和官员相对应的只有礼服、常服、吉服和便服几类。董进说,礼服是女性的朝祭之服,在祭祀、朝见君后、见姑舅与夫时穿着,一身装束包括翟冠、大衫、霞帔、坠子、笏等等,是人们通常所称的“凤冠霞帔”。其他礼仪场合,女性可以选择穿常服,也就是各色圆领袍,上面的补子则随夫、子的品级。 无论男女,最绚烂的服饰出自吉服这个门类。董进向我解释,吉服可以理解成“吉庆之服”,是明代人们在时令、节庆活动、寿诞、筵席、婚礼等吉庆场合穿的衣服。吉服的用色明朗,多用大红色的喜庆色彩,款式也很丰富,有圆领袍、直身、贴里、道袍等,还会大量使用提花、妆花、织金、刺绣等工艺技术,赐服的一些纹饰也经常用在吉服上,比如蟒、飞鱼、斗牛、麒麟等。董进说,由于今天的汉服爱好者也基本都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穿着汉服,更偏向穿一套盛装感觉的汉服,所以主要做明制汉服的品牌也都会从吉服这个门类里汲取灵感。
无论男女,最绚烂的服饰出自吉服这个门类。董进向我解释,吉服可以理解成“吉庆之服”,是明代人们在时令、节庆活动、寿诞、筵席、婚礼等吉庆场合穿的衣服。吉服的用色明朗,多用大红色的喜庆色彩,款式也很丰富,有圆领袍、直身、贴里、道袍等,还会大量使用提花、妆花、织金、刺绣等工艺技术,赐服的一些纹饰也经常用在吉服上,比如蟒、飞鱼、斗牛、麒麟等。董进说,由于今天的汉服爱好者也基本都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穿着汉服,更偏向穿一套盛装感觉的汉服,所以主要做明制汉服的品牌也都会从吉服这个门类里汲取灵感。
吉服当中,有一类装饰的纹饰叫作云肩、通袖、膝襕,它是在前胸、后背和两肩处装饰柿蒂形“云肩”,左右肩部至袖端装饰“袖襕”,前后襟下摆处装饰“膝襕”。这种组合在一起的装饰方式在元代形成,在明代广泛应用。山东博物馆负责织绣类藏品保管与研究的吕健告诉我,由于它的纹饰面积很大,并且会和妆花、织金工艺相结合,最能体现出明代织造技艺的高度。
关于妆花的技艺,蒋玉秋向我做了一个比拟:绣花相当于是两个图层,妆花则是要在一个图层完成图案,织造者要提前设计好“花本”,上织机前相应图案的经纬线就已经排好了。起花的时候,同一列纬内,当其中一种颜色的纬纱浮现在正面,其余纬纹就以抛梭的方式沉入织物背面。“比如一朵深粉和浅粉结合的牡丹花,两种颜色的线都排布在下面,想要深粉色的地方,就要用纬线把浅粉色压住,反之亦然。这样起花的位置就相对厚一些。”妆花的工艺前朝就有,但无论是孔府旧藏中大比例的妆花衣料,还是《天水冰山录》这部记录明朝贪官严嵩的家产清单里妆花衣料的比例,都表明妆花工艺在明代的广为流行。“妆花的普遍使用,侧面说明了明代经济的发达程度。因为妆花的过程中,为了显示正面的一点颜色,要牺牲很多其他颜色的丝线。物料有限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这样做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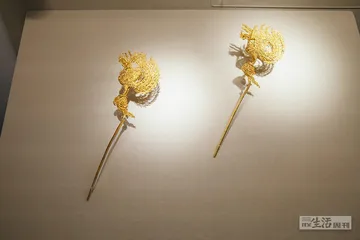 而织金则更是财力的一种体现。吕健说,织金线有片金线和圆金线之分。片金线是由金箔切片而成,后面加褙衬,褙衬的材质主要为动物的皮或纸;圆金线则是以丝线为胎,外加金箔而成的金缕丝线。在孔府旧藏中,就有一件大红色四兽朝麒麟纹妆花纱女袍,是以妆花的织造方式,完成了云肩、通袖、膝襕的纹饰分布。在柿蒂形的区域内,胸、背和两肩各有一只大麒麟,下面顺时针是四只小兽——老虎、狮子、小麒麟和獬豸,并间以海水江崖、杂宝花卉纹饰。这些瑞兽的轮廓线是以片金线勾勒,这就使得整件衣服有着金彩交辉、雍容华贵的效果,成为孔府旧藏服饰中图片被广为传播的一件“明星”文物。
而织金则更是财力的一种体现。吕健说,织金线有片金线和圆金线之分。片金线是由金箔切片而成,后面加褙衬,褙衬的材质主要为动物的皮或纸;圆金线则是以丝线为胎,外加金箔而成的金缕丝线。在孔府旧藏中,就有一件大红色四兽朝麒麟纹妆花纱女袍,是以妆花的织造方式,完成了云肩、通袖、膝襕的纹饰分布。在柿蒂形的区域内,胸、背和两肩各有一只大麒麟,下面顺时针是四只小兽——老虎、狮子、小麒麟和獬豸,并间以海水江崖、杂宝花卉纹饰。这些瑞兽的轮廓线是以片金线勾勒,这就使得整件衣服有着金彩交辉、雍容华贵的效果,成为孔府旧藏服饰中图片被广为传播的一件“明星”文物。
孔府旧藏的服饰如此华丽,那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明代服饰的全貌?董进告诉我,首先它能够反映明代士大夫阶层的着装风貌。“古代服饰的拥有情况,是一种倒金字塔的结构,也就是你越往上走,社会阶层越高,拥有的服饰类别就越多,越往下走,越是普通老百姓,服饰类别就越少。有个说法叫作‘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说的就是较高社会阶层人的服饰就把他之下的人都涵盖了,普通人的服饰就相当于是在做减法,类别、款式要少一些,用料要差一些,纹饰要简单一些。”而衍圣公作为高级别的官员,他家族的服饰也就缺乏帝王后妃相对应的几个品类。“这些则可以靠考古上的发现来作弥补,比如北京定陵就有出土帝王衮服。”这些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更加完备的明代服饰体系。 除去一些礼仪性的场合,女性需要穿圆领袍、大衫这样礼服性质的外衣,明代女性最常穿着的服装款式其实非常明确,就是上身穿袄衫,下身穿裙。明代口语中常用“三绺梳头、两截穿衣”来指代女性。好比《醒世姻缘传》三十二回写道:“此等美举,我们峨冠博带的人一些也不做,反教一个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女人做了,还要这须眉做甚?”两截穿衣是唐宋以来女子便装的基本装束,也是明代女性的典型搭配。
除去一些礼仪性的场合,女性需要穿圆领袍、大衫这样礼服性质的外衣,明代女性最常穿着的服装款式其实非常明确,就是上身穿袄衫,下身穿裙。明代口语中常用“三绺梳头、两截穿衣”来指代女性。好比《醒世姻缘传》三十二回写道:“此等美举,我们峨冠博带的人一些也不做,反教一个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女人做了,还要这须眉做甚?”两截穿衣是唐宋以来女子便装的基本装束,也是明代女性的典型搭配。
只是这裙和衣都与前代不同。裙,形制就是近年火遍全国的“马面裙”,而“马面裙”是后世对它形象的叫法。马面裙能够出圈,一在于它方便和现代服装搭配,二在于它穿上之后活动方便。这也是马面裙被创制出来的初衷。马面裙的鼻祖是宋代的“旋裙”。《中原女子服饰史稿》一书的作者、服饰研究者孟晖告诉我,北宋的著作《江邻几杂志》中有这样一条记录:“又说,妇人不服宽袴与襜,制旋裙,必前后开胯,以便乘驴。”孟晖说,自汉代以来,传统女裙一直是一片式的“片裙”。而旋裙的开拓性就在于它是两扇裙片部分叠合在一起,再缝连到裙腰上,这样裙子就会形成一明一暗两道开衩。这样骑驴时裙裾就不会堆叠在马鞍上,而是以开衩为分界分开两旁笼覆住双腿,就很方便。这就是马面裙的雏形。
“马面”本意是指城墙上凸出来的一个墩台,它的立面形如马面。“马面”第一次用于形容服饰,是在明代的一部著作里去形容一种叫作“曳撒”的长袍上的构造。到了明代,马面裙在旋裙上的发展,就是在交叠的裙门两侧来打褶,这不仅增加了裙子的活动空间,还有美观的效果。这样的结果就是它很像是曳撒的下部,中间裙门交叠处形成了长方形的马面,两侧是褶。
今天的各个汉服商家纷纷生产马面裙,但很多时候只能做到形似,并没有掌握真正明代马面裙的设计语言。比如,打褶应该怎么来做?蒋玉秋曾经修复过一条浙江嘉兴王店镇李家坟明墓出土的马面裙,“当时那条裙子很残破,看上面的折痕,有的向里,有的向外,我就用折纸的方式来模仿和琢磨”。她发现在这条马面裙左右每组褶子的正中,存在有一个“合抱褶”。“‘合抱褶’的设计有什么功用呢?当它两侧的对褶将压力从外向内施向中央,合抱褶则将压力从内向外推向两侧,这样内外的压力相互抵消,裙子形成的空间感就更加自然。”后来在更多的明代马面裙文物中,蒋玉秋都看到合抱褶的存在,很是佩服古人在设计上的智慧。而现在我们进行明代马面裙仿制的时候,往往容易忽略这些细节。
马面裙的纹样装饰也有规则。董进告诉我,现在很多商家为了马面裙看上去华丽,纹饰是在裙面上来满铺的。“其实明代马面裙的装饰主要在膝襕和底襕。明代早期上衣较短,相配的马面裙就会装饰膝襕。到了晚明上衣较长,马面裙就会装饰底襕,因为只能露出裙子底部的纹样。而如果是膝襕和底襕都来作装饰,膝襕较粗、底襕较细,上面一定是配一个较短的上衣。反之如果膝襕较细,底襕较粗,视觉中心在最下,上面一定搭配一个长衫。从马面裙膝襕和底襕的装饰,也就可以推测出上衣应该穿什么。” 孔府旧藏中的一件葱绿地妆花纱蟒裙是这批藏品中非常重要的一条马面裙。它上面的图案是五爪蟒龙纹,级别很高,由此可知是来自帝王的赐服。工艺上又是妆花和织金相结合,尽显奢华。葱绿的颜色和《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女性所穿马面裙的颜色相仿,说明是当时的流行色。它不断被今天的汉服商家复刻,尤其上面的蟒龙纹契合今年龙年的生肖,复刻版就成为今年春节前穿着的“爆款”。这条裙子上有着上窄下宽的两条襕纹。董进说,这条马面裙过去在一些图册搭配里常被认为是和孔府旧藏的另一件暗绿地织金纱云肩通袖翔凤纹女短衫是一身,其实它较宽的底襕说明它应该搭配一件较长的上衣,又根据它蟒龙纹的隆重程度,上衣应该配一件圆领袍才对。
孔府旧藏中的一件葱绿地妆花纱蟒裙是这批藏品中非常重要的一条马面裙。它上面的图案是五爪蟒龙纹,级别很高,由此可知是来自帝王的赐服。工艺上又是妆花和织金相结合,尽显奢华。葱绿的颜色和《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女性所穿马面裙的颜色相仿,说明是当时的流行色。它不断被今天的汉服商家复刻,尤其上面的蟒龙纹契合今年龙年的生肖,复刻版就成为今年春节前穿着的“爆款”。这条裙子上有着上窄下宽的两条襕纹。董进说,这条马面裙过去在一些图册搭配里常被认为是和孔府旧藏的另一件暗绿地织金纱云肩通袖翔凤纹女短衫是一身,其实它较宽的底襕说明它应该搭配一件较长的上衣,又根据它蟒龙纹的隆重程度,上衣应该配一件圆领袍才对。
在那次“衣冠大成”的展览中,北京服装学院教授楚艳和山东博物馆合作复制了三件孔府旧藏的服装,既为深入研究它们的制作工艺,也为日后相关展陈能够用来替代。她选择进行复制的是另一条白色暗花纱绣花鸟纹马面裙。这条裙子上的装饰并没有级别上的象征,因此它只算是一件“便服”,但楚艳对它情有独钟。“因为很多马面裙的装饰都是一种‘二方连续’的循环往复的纹样,这条马面裙上的刺绣就像一幅画一样,每一个元素都是不同的。”楚艳在学校教服装设计,也拥有自己的“新中式”风格的服装品牌,觉得这样的图案布局对今天的中装设计也很有启发。 楚艳为我展示那条复制的裙子,它的装饰全部集中在底襕,用丝线绣有山石、小桥流水、牡丹、石榴花、睡莲、蜀葵、牵牛花、竹子、蝴蝶、翠鸟、鸾凤等等。“它的仿制难度就在于,那些刺绣图案隐藏在褶子里,你需要将它小心翼翼地展开才能看到全部。”这种刺绣采用的是有山东地域风格的“鲁绣”,它用的丝线要稍粗一些,绣出来有一种北方特有的粗犷在里面。“并且你看上去有的花朵颜色差不多,其实所用丝线的颜色都有差别。”楚艳用色卡对比,看到整幅刺绣一共涉及30多种颜色。重绣这条裙子花了四位绣娘一共两个月的时间。这个过程足以让楚艳感叹,当时的贵族之家对这样一条用作便装的马面裙也何其讲究。
楚艳为我展示那条复制的裙子,它的装饰全部集中在底襕,用丝线绣有山石、小桥流水、牡丹、石榴花、睡莲、蜀葵、牵牛花、竹子、蝴蝶、翠鸟、鸾凤等等。“它的仿制难度就在于,那些刺绣图案隐藏在褶子里,你需要将它小心翼翼地展开才能看到全部。”这种刺绣采用的是有山东地域风格的“鲁绣”,它用的丝线要稍粗一些,绣出来有一种北方特有的粗犷在里面。“并且你看上去有的花朵颜色差不多,其实所用丝线的颜色都有差别。”楚艳用色卡对比,看到整幅刺绣一共涉及30多种颜色。重绣这条裙子花了四位绣娘一共两个月的时间。这个过程足以让楚艳感叹,当时的贵族之家对这样一条用作便装的马面裙也何其讲究。
穿在马面裙上的袄衫在明代有一个很突出的特色,就是从明中期开始,在传统的圆领和交领之外,出现了竖领这样的形制,竖领大襟和竖领对襟的袄衫成为一种常见的女性上装款式。这种竖领和后来人们更加了解的旗袍的领口不一样,它的领子要高,也并不严丝合缝贴合脖颈,而是留有余量,它成为之后中式女装立领的演变基础。女性穿着时还可以将领口微微下翻,呈现不同的视觉效果。 竖领的出现也为一种装饰风格提供了舞台,那就是纽扣的使用。孟晖告诉我,明朝与中亚、西亚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各色外来的宝石成为制作纽扣的材料。一枚精巧的子母套结式纽扣,会以金银打造,镶嵌宝石,再做出或花卉草虫、或人物神佛、或吉祥文字等各种造型。如果是竖领对襟的衫袄,上面的金银宝石纽扣能缀上最多七枚,贵族女性会以此来彰显财力。
竖领的出现也为一种装饰风格提供了舞台,那就是纽扣的使用。孟晖告诉我,明朝与中亚、西亚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各色外来的宝石成为制作纽扣的材料。一枚精巧的子母套结式纽扣,会以金银打造,镶嵌宝石,再做出或花卉草虫、或人物神佛、或吉祥文字等各种造型。如果是竖领对襟的衫袄,上面的金银宝石纽扣能缀上最多七枚,贵族女性会以此来彰显财力。
竖领为何会出现?孟晖说,一个解释是明代中期是一次小冰河时期,领子升高有助于御寒。另外的解释则是,明代的程朱理学对女性有着严苛的保持贞洁的要求,尤其是明中后期,人体禁忌观念被强化至极端的地步,“凭借着竖领与纽扣,宗法社会的人体禁忌观念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女子的脖颈也消失在服饰之下”。 和女性的袄衫加马面裙的配搭相对,如果选出一套代表明朝男性普遍的装扮,那就非道袍莫属了。明代学者范濂在《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的服饰部分写道:“男人衣服……隆、万以来,皆用道袍。”也就是说,自明朝隆庆、万历皇帝的中后期,道袍成为男子常穿的袍服,从帝王官员,到士庶阶层,均有穿着。
和女性的袄衫加马面裙的配搭相对,如果选出一套代表明朝男性普遍的装扮,那就非道袍莫属了。明代学者范濂在《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的服饰部分写道:“男人衣服……隆、万以来,皆用道袍。”也就是说,自明朝隆庆、万历皇帝的中后期,道袍成为男子常穿的袍服,从帝王官员,到士庶阶层,均有穿着。
正如它的名字所示,道袍最初就是道家释道之服。服饰学者徐小盼、王蕾在梳理道袍的源流变化时提到,元代统一天下后,由于皇室大力扶持,道教活动增多,道士的活动频繁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其中外穿的道袍因为衣身宽松、衣袖宽大,能体现文人的儒雅之风,受到士大夫阶层的青睐。它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形制也渐渐确立下来。一件典型的明代道袍是上下通直,采用大襟交领,领子常镶白色或素色护领。它有“暗摆”来遮蔽衣身两侧的开衩,避免内穿的衣裤外露。穿着道袍时,腰间可配丝绦、布制细腰带或者大带。
楚艳当时在孔府旧藏男性服饰中进行复制的时候,选中的就是一件蓝色暗花纱的道袍。它是以蓝靛染色,图片上看不出来,其实纱上有暗纹,织了仙鹤衔灵芝、寿桃、石榴还有四合如意纹。“这件样式简单,但又特别经典,一眼看上去就能想到明朝读书人的样子。”楚艳对我说。今天的仿制难度不在于暗纹,而在于纱这种材质。“现在的织机能织出来很细的纱线,反而模仿当时那种手工纱线较粗并且粗细不均匀的感觉,有点困难。” 事实上,孔府旧藏的这批服饰的材质当中,纱罗质地占了绝大多数,说明这是当时受到追崇的面料。这也给今天的汉服品牌以启示。专门生产明制汉服的品牌、明华堂的创始人钟毅告诉我,他当年在看完孔府旧藏的展览后,发现纱料质地的服饰会非常挺括且有筋骨感,而绸缎虽然柔软,但在塑形上并不如纱,于是果断将产品面料的重心改为了纱。“而且纱质面料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古人在下面还会穿多层打底的衣服,外层穿纱不至于太热。”纱质道袍也常见于明代小说笔记的描写之中。《喻世明言》第一卷描写一位陈姓商人的打扮:头上戴一顶苏样的百柱鬃帽,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醒世姻缘传》第二十六回有写:“十八九岁一个孩子……穿了一领鹅黄纱道袍,大红缎猪嘴鞋……”
事实上,孔府旧藏的这批服饰的材质当中,纱罗质地占了绝大多数,说明这是当时受到追崇的面料。这也给今天的汉服品牌以启示。专门生产明制汉服的品牌、明华堂的创始人钟毅告诉我,他当年在看完孔府旧藏的展览后,发现纱料质地的服饰会非常挺括且有筋骨感,而绸缎虽然柔软,但在塑形上并不如纱,于是果断将产品面料的重心改为了纱。“而且纱质面料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古人在下面还会穿多层打底的衣服,外层穿纱不至于太热。”纱质道袍也常见于明代小说笔记的描写之中。《喻世明言》第一卷描写一位陈姓商人的打扮:头上戴一顶苏样的百柱鬃帽,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醒世姻缘传》第二十六回有写:“十八九岁一个孩子……穿了一领鹅黄纱道袍,大红缎猪嘴鞋……” 道袍的颜色有很多。明代学者朱之瑜在《朱氏舜水谈绮》这本著作里,谈到道服主色“月白、翠兰、天蓝、牙色、松花色、酱色、羊绒色、葱白,以上八种皆可用”。明代万历朝初期的礼部尚书陆树声请画师为自己画像,记录下他身着不同服装的样貌,形成了一本《陆文定公画册》。其中一幅画像中,垂垂老矣的他还身穿了一件粉色道袍,颇有一种时尚感。正是道袍在花色上的包容度,也让它成为今天明制汉服的男性爱好者酷爱穿着的对象。
道袍的颜色有很多。明代学者朱之瑜在《朱氏舜水谈绮》这本著作里,谈到道服主色“月白、翠兰、天蓝、牙色、松花色、酱色、羊绒色、葱白,以上八种皆可用”。明代万历朝初期的礼部尚书陆树声请画师为自己画像,记录下他身着不同服装的样貌,形成了一本《陆文定公画册》。其中一幅画像中,垂垂老矣的他还身穿了一件粉色道袍,颇有一种时尚感。正是道袍在花色上的包容度,也让它成为今天明制汉服的男性爱好者酷爱穿着的对象。
道袍之外,另一种明代男士服饰款式在今天也很受到追捧。这就是属于断腰袍形制的贴里和曳撒。根据服饰研究者常晓君、王楚昀考证,贴里和曳撒有着相同的起源,就是蒙元时期的辫线袍。它们看上去都是交领、右衽,前衣身并非上下通裁,而是分成上衣和下裳再连缀起来,下摆上都有着裙褶。但两者又有形制上的些许区别,最明显的,就是贴里的下摆全都是褶子,像个百褶裙;而曳撒的下摆正中是一个“马面”,类似马面裙的下半部分。
两者在明代也有穿着阶层和穿着用途上的不同。贴里的穿着人群更广,从王公贵胄到士庶平民都可以穿。并且它外穿和内穿皆可。外穿可以很豪华,有蟒纹这样的图案。而士人一般是内穿一件实用性质的贴里,因为它“百褶裙”一样的设计能给外衣一个很好的支撑。曳撒则通常为王公贵胄、朝廷命官的礼仪性着装,明中期以后,主要作为军队的戎服来使用。
汉服爱好者为何会注意到这类形制的衣服?这和孔府旧藏中的另一件“明星”藏品——香色麻飞鱼贴里——以及爱好者对它的仿制有很大的关系。2013年,陈雪飞还是“汉服北京”这个社团组织的成员,他和里面的一些“同袍”形成了一个叫“控弦司”的小团体,大家在一起穿汉服,也一起练习传统射艺。有一天,陈雪飞看到了那件香色麻飞鱼贴里的图片,觉得很漂亮,就决定利用自己在美术方面的特长把它给仿制出来。
“我把能找到的图片资料都凑在一起,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在一件棉质布袍上来一点点手绘。因为它就是云肩、通袖、膝襕的纹饰,图案分布有一定的规律,衣服反面是什么纹饰都是对称的,可以推测出来。”陈雪飞这样告诉我。这件衣服做出来就在圈子里大获好评,于是之后他又用印花的方式让“控弦司”的成员每人都有了一件。后来,总是有汉服爱好者不断找过来想买同款衣服,陈雪飞干脆就走上了商业生产的道路。他创立了“控弦司”这个主做明制汉服男装的品牌,最热销的产品,依然是飞鱼图案的贴里或者曳撒。 这样的衣服也被汉服爱好者称作“飞鱼服”。“但其实这种称呼并不准确。”《中国甲胄史图鉴》一书的作者周渝告诉我,“‘飞鱼’是一种纹样的名字,它长得像龙又不是龙,是一个具有龙头和鱼尾的形象。飞鱼服属于赐服,是一种特典,但它并非明代唯一的赐服。在明朝赐服制度中,纹样最高级别的为蟒,其次是飞鱼,第三为斗牛,它们都是一种‘类龙’的纹样,也就是和龙很相似,但细节又不同。”周渝说,所以“飞鱼服”可以泛指所有带飞鱼图案的衣服,可以是不同形制的,并不一定就特指贴里或者曳撒。“而大家看到影视作品里的锦衣卫,穿着贴里或者曳撒,一律统称‘飞鱼服’,上面也有可能是别的纹样。”
这样的衣服也被汉服爱好者称作“飞鱼服”。“但其实这种称呼并不准确。”《中国甲胄史图鉴》一书的作者周渝告诉我,“‘飞鱼’是一种纹样的名字,它长得像龙又不是龙,是一个具有龙头和鱼尾的形象。飞鱼服属于赐服,是一种特典,但它并非明代唯一的赐服。在明朝赐服制度中,纹样最高级别的为蟒,其次是飞鱼,第三为斗牛,它们都是一种‘类龙’的纹样,也就是和龙很相似,但细节又不同。”周渝说,所以“飞鱼服”可以泛指所有带飞鱼图案的衣服,可以是不同形制的,并不一定就特指贴里或者曳撒。“而大家看到影视作品里的锦衣卫,穿着贴里或者曳撒,一律统称‘飞鱼服’,上面也有可能是别的纹样。”
周渝是平时也会穿着汉服,最常穿的就是一身飞鱼的贴里。“贴里和曳撒的差别还有一点,就是曳撒的下摆两侧会有‘缯角’,像两个小翅膀一样,作用是避免内搭衣物漏出而有失优雅。所以穿曳撒的时候还需要整理,就没有贴里那么方便。”对于陈雪飞,他更偏爱穿着曳撒,因为下摆光滑的那片“马面”会让坐下的时候更加舒适。而无论贴里还是曳撒,他们都把这类服饰称为“汉服中的运动服”,和穿着宽袍大袖的道袍比起来,穿上它们更适合运动。陈雪飞在一些特别的节庆场合,会穿上它来射箭或者骑马。周渝则给我看了一段穿着贴里来舞剑的视频,贴里的下摆旋转飞扬,显得潇洒又自如。
在做了贴里和曳撒多年之后,陈雪飞也在为店里增加其他款式的衣服,比如带有补子的圆领袍,就是一个新的品类。他告诉我,每次翻看那些明代服饰的资料,他都会有一些新的出品想法。明代服饰这座宝库,还有太多的形制和纹样没有被汉服爱好者认知。
(感谢王非、赵丰、紫菀、杨汝林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明代服饰汉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