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续冬:诗何以群?
作者:艾江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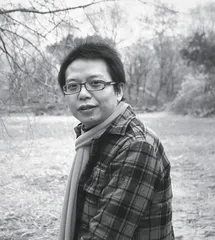 不久前,胡续冬的诗集《一个拣鲨鱼牙齿的男人:胡续冬诗选》出版,受到一些读者和书评人的关注。这本诗集,被介绍为他生前编选的一本自选集,除了收录那些他早已为读者熟悉的作品,还收入他去世前几年的一些新作。
不久前,胡续冬的诗集《一个拣鲨鱼牙齿的男人:胡续冬诗选》出版,受到一些读者和书评人的关注。这本诗集,被介绍为他生前编选的一本自选集,除了收录那些他早已为读者熟悉的作品,还收入他去世前几年的一些新作。朋友圈中那些带着怀念之情的转发信息,让人想起这个被朋友们叫作“胡子”的诗人,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两年多了。2021年中元节,疫情的阴云依然密布,他的猝然而逝,加重了某种共同的感受,近千人在八宝山为他送行后,朋友们自发组织了一场告别歌会。
为何一个诗人的离开,能引起如此多的共情、感怀甚至疼痛?如同他在诗歌中展开的各种分身一样,胡续冬有着许多精彩的分身:“70后”代表诗人;和学生没大没小打成一片的高校教师;灵光闪现、生猛诙谐的专栏作者;国内最早的新锐文化网站“北大新青年网站”的创办人;最能调动气氛的专业的诗歌节主持人;一个每天接送女儿上下学,教她辨析植物、喂养流浪猫的好父亲……由此他也连接起了形形色色的文化群落和热爱生活的人们。然而仅仅是这样吗?随着时间的沉淀,一些人试图做出解释。学者钱文亮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那句广为人知的话:‘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本身,胜于爱生活的意义。’……‘爱具体之人,向他者开放’,不仅是胡续冬其人其诗的独特气质,同样也被时代需要。这在当下充斥着过度强调‘私人原则’的极端社交心理——回避型‘社恐’或是侵略型‘社牛’——的社会生活中显得愈发珍稀。”
一切总结都容易显得煞有介事,胡续冬听到这样的话,多半会嘴角上扬、不以为然。然而,钱文亮的提醒却很重要:回到时代,回到诗去看待一位诗人。
胡续冬离世几个月后,熟悉他的几位诗人与评论家张洁宇、冷霜、姜涛组织了一场对话活动:“胡续冬与‘九十年代诗歌’”。对话的题目很有意味。胡续冬的博士论文题目便是《“90年代诗歌”研究》,连缀着“叙事”“个人写作”“及物性”“拒绝隐喻”“诗到语言为止”等关键词被讲述的“90年代诗歌”,区别于“朦胧诗”和之后的“第三代诗人”,曾成为一个被广泛引用与讨论的独立概念。之后,人们不再能找到一个囊括性的概念讲述当下的诗歌写作。那次对话中,姜涛谈到理解胡续冬诗歌的线索之一时说:“胡续冬喜欢将他生活的场域、他的‘朋友圈’搬迁到诗中,‘诗可以群’这个古老的功能在他这里不仅复活了,还成了他写作的内驱力。”
诗何以群?诗歌如何搅动身边的现实,从而抵达人心? 比胡续冬高一级就读于北大中文系的冷霜还记得,1993年万圣书店刚开业,包了一辆中巴车到校园卖书。他第一次可以随便翻找自己想看的书,而不是站在新华书店柜台旁,向售货员远远地指认。“一些新生事物开始出现,另一方面,我们当时的普通心理感受,老师学长们嘴里那个更有理想的80年代刚刚过去,觉得我没赶上好时候。而且没赶上好时候的一个现实背景是,在80年代的整体文化氛围里,诗歌处在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但到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算在中文系里面,写诗也被认为是一件有点奇怪的事情,诗歌是一个神秘的,和一个已经开始朝着市场经济方向挣钱的氛围格格不入的小圈子。”冷霜说。
比胡续冬高一级就读于北大中文系的冷霜还记得,1993年万圣书店刚开业,包了一辆中巴车到校园卖书。他第一次可以随便翻找自己想看的书,而不是站在新华书店柜台旁,向售货员远远地指认。“一些新生事物开始出现,另一方面,我们当时的普通心理感受,老师学长们嘴里那个更有理想的80年代刚刚过去,觉得我没赶上好时候。而且没赶上好时候的一个现实背景是,在80年代的整体文化氛围里,诗歌处在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但到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算在中文系里面,写诗也被认为是一件有点奇怪的事情,诗歌是一个神秘的,和一个已经开始朝着市场经济方向挣钱的氛围格格不入的小圈子。”冷霜说。
1992年秋天,冷霜最初见到的胡续冬,并非后来人们眼中的社交达人“胡子”,“寡言少语,而且说话还略有口吃”。在胡续冬后来不无夸张的自我叙述中,他这个脾气暴躁、智力上高度自负、来自湖北边缘小城暴力团体里的不良少年,看到五四文学社那张“一个大脚印踩在上面,非常简单粗暴,非常有冲击力”的招新海报时,很快有种找到组织的感觉。诗歌带给胡续冬巨大的改变:“第一,我变成一个喜欢跟人沟通的人;第二,由一个比较木讷、不善言辞的青年变成了话痨;第三,我接过五四文学社社长的位置,也倒腾了很多朗诵会,主持这,主持那,最后主持变成我一个副业,以至于后来我发现从五四文学社退役后,可以用主持技能干别的,于是后来我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了几年。”
这样一个天性活跃、有丰富可能性的少年,为何在90年代选择写诗?在姜涛看来,这与90年代整体的诗歌氛围相关:“90年代诗歌对于语言的开放性理解,极大满足了这个顽劣少年与更多不规则事务、与更多人打交道的欲望。虽然90年代诗歌后来受到了很多批评,像过多的叙事、过度的反讽、过分的经验主义而导致细节肥大症等,但在我看来,90年代也许仍是当代诗最具野心和活力,心境也相当蓬勃的一个时期,胡续冬诗歌的底色在这个时期确立下来。”
那时海子的诗歌神话刚刚形成,90年代初的校园诗歌写作,多少都会受到海子、骆一禾、戈麦那种质地相对纯净、偏于元素化意象的抒情方式的影响。然而,这更像是一个80年代的尾巴。1993年、1994年,整个诗坛的风向在发生变化,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孙文波等一批后来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对更年轻的诗人产生很大影响的诗人,都开始写出某种带有转型意味的代表诗作。在他们的批评文章中,一种更为强调诗歌技艺、强调诗歌综合处理当下现实经验的写作正在展开。
1993年底,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姜涛因参加北大未名诗歌节结识了胡续冬,之后便互相交换作品。尽管姜涛的写作已与那种抒情性很强、主要写乡村经验的诗歌有所不同,他看到胡续冬的诗仍很震撼:“我忘了1994年还是什么时候,他给我看新写的一首诗,大概写一个女孩坐出租车,最后出租车把她像一个枣核一样吐在北大南门口,我觉得挺意外,出租车这种东西还能写到诗里,我们那时写诗,哪怕写日常生活异质的经验,也是某种文学类型的。他带给我的感觉,一方面好像很直白外露,另一方面有特别强的活力。我们一般理解诗歌还是象征的暗示的,胡续冬开始的时候根本不管,直接把经验中最活泼、很魔幻的东西写出来,叙事性非常强。一定程度上我也受了他的激励。”
就这样,1994年底,几个共同意识到90年代诗风变化的年轻诗人,胡续冬、冷霜、姜涛、王来雨,包括后来到北京的蒋浩,一起参与到曾对90年代中后期的诗坛产生一定影响的《偏移》的编辑中。不同于“第三代诗人”提出的“PASS 北岛”,这些诗人提出的偏移,明显带有90年代的印记:理性而富有建设性。根据姜涛的解释,所谓“偏移”,一方面是偏移于上一代诗人所开辟的90年代诗歌氛围,找到自己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更多指向自我的偏移,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诗学理念,要求将诗歌看作不断释放可能性、扩充对世界认识疆域的写作方式。
胡续冬是这批人中最快摆脱学徒状态的人。在对现实经验的处理中,他很早就表现出那种对具有反讽与喜剧意味的东西的关注。这种搅拌着不同生活经验、带有喜剧的发现意味、叙事色彩很强的诗歌,从《在臧棣的课堂上》《为一个河南民工而作的忏悔书》《柱子到北大刷广告》《中关村》,到后来广为传播的《太太留客》,一度成为胡续冬诗歌的标签。那些闪现在诗行中,如同电影镜头一样纷繁的生活经验,如同一部压缩的诗体小说,带给人们那个时代的鲜活气息。
姜涛重读胡续冬的《中关村》,当时觉得好玩,现在则有些感慨甚至伤感。“诗的密度很大,写的是中关村桥下两拨人打架,一拨是卖打折机票的,一拨是贴小广告的,两拨人都穿着缩水西装,像电子游戏中搏击的两个小人。然后,一个小人跑了出来。跑到哪儿了呢?跑到一个发廊里,发廊里的发廊妹误以为警察来扫黄,于是也开始跑,跑过工地、售楼处、居民小区,又遇上了打劫的人……胡续冬就这样让一个人接着一个人跑起来,也带着整个中关村在跑,最后大家都跌在了这首诗里。……诗中出现的人物,穿缩水西装的人、发廊妹、小流氓等,在现在的中关村已经见不到了,现在街上走着的都是文质彬彬的、内卷的打工人。”
诗歌中的大开大合,同构于那个虽然混乱但充满能量与可能的时代。搅拌现实与虚构,让写作变得活色生香,则是胡续冬的长处。在随笔《在路上发明人生》中,胡续冬便讲述了自己在生活中遇到各色人等,难以忍耐的那种虚构现实的冲动:“要往简单里说,就是我有一破毛病,喜欢在路上跟不认识的人瞎贫,尤其是喜欢乱编自己的身世以配合对方聊天的兴头。”
这种扮演性,在胡续冬那里成为一种自觉的写作意识:“我大概成为不了佩索阿,所以我将以往的抱负中对我的发明收缩为一种高强度的‘自我腾挪’,方言只是我在诗歌中修炼‘乾坤大挪移’的一种路数而已。更多的时候,我所倾心的挪移状态体现在心智快速反应的其他层次上。”
这种戴着面具的戏剧化的书写方式背后,在冷霜看来,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胡续冬诗歌中的主体是一个善于自嘲的把自己放得很低的形象”。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续冬的写作在90年代诗歌中闪烁着自己的独特光芒,吸引着那些同样带着缺点、喜欢自嘲的年轻人。每个人都与你有关
2003年,胡续冬到巴西国立巴西利亚大学任教。两年后回国,胡续冬结了婚,因为肝病的原因,很早便宣布戒酒,从当年鲜衣怒马的诗歌青年一下转入规律日常的家庭生活。与此同时,他的写作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冷霜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从一个拼贴光怪陆离的当下中国社会进程的观察者,变为一个连接世界有趣、有意义部分的写作者。于是,壁虎、狗、麻雀、蝗虫、花栗鼠、蛐蛐、松鼠还有紫荆花、杜鹃、木棉这样带有博物性质的写作出现在他的诗歌中。这些诗中,虽然同样充满那些熟悉的戏剧化场景,但却展现出一种将这些动植物与自己的生活快速建立联系的能力,北美的蝗虫,“它们是最棒的乡村乐手,/翅膀和后腿稍事摩擦,/就足以令我从北美大草原/回到四川盆地的稻田”。深圳的木棉花则让他想起女儿,“木棉花围坐一地/像提前退休的一群人在练习瑜伽/木棉花深处有一个三岁的女娃/挥着小拳头高呼‘打爸爸’!”即使是在西班牙的埃库勒斯塔,胡续冬所注意到的,仍是一个在护栏边哭泣的来自河南南阳的天主教徒。在《里德凯尔克》中,无聊等船的他甚至和云打起了招呼,“我们互相打了个招呼。/它的云语言元素聚合不定/很难沟通。它伸出/飘忽的云手,试图递给我/一根云烟,我表示婉拒/因为我只抽黄鹤楼”。
这些作品中,胡续冬的诗与人是打成一片的,他在诗中能让任何陌生的风景物相转化为让人会心一笑的熟悉场景,如同他在生活中总有办法能迅速拉近你和他的距离。冷霜将之形容为一种“轻微的推搡”,“他会通过语言或其他方式,给你一种轻微的推搡的感觉,如果在人与人边界感非常强的情况下,推搡就会带来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推搡恰好使我们建立起一种身体上或心理上更近的关系。有时候他会开一些带颜色的玩笑,给人起外号,打破大家的边界感,建立起一种更加亲密的联系。”
这种轻微的推搡感,事实上保留着小地方熟人社会中的某种影响,“这就好像在你的生活半径里头,每个人其实都和你有关,你都可以去跟他攀谈”,冷霜由此想到了人类学家项飙所说的“附近的消失”,“项飙谈到我们的生活中少了附近,要重新了解我们的生活,但胡续冬就是一个与他附近菜市场这些卖菜的、居委会的大妈,包括附近的猫,都能建立起特别真实连接的人。”在那首纪念挚友马雁的《七年》中,胡续冬描述听到坏消息的那天,带着学生星娃到早市卖菜的场景,那种对每个摊贩的熟悉跃然纸上:“我们先来到了写有歪歪扭扭的‘南方菜’/字样的一块硬纸壳下,卖菜的连云港小哥/把我从一群挑菜的千手观音拉到摊位后面,/打开了一个沾满泥巴的大口袋:/‘大哥,今天最好的冬笋都在这里,给你留着的。’我买了冬笋、芦笋、豌豆尖,/又带着星娃来到了长得像赵本山的/四川达哥的菜摊前,他家的儿菜/已在塑料布上排成了一个儿菜幼儿园。”
“我觉得胡续冬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实际上是对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中小城市市民生活的理解方式。他少年时期所生活的湖北十堰这种中小城市,地方社会文化非常发达,人情世故很多,大家在一个熟人社会中,非常自在,跟所有人打成一片,打麻将聊闲天,跳广场舞,没有大城市人的包袱,也没有农村的不满和怨恨。”姜涛说。
如果说波兰诗人米沃什身上带着“小地方人的谨慎”,那么胡续冬身上便带着“小地方人的自在”。那种自在,曾是我们所熟悉的感受。然而,这似乎并不足以解释胡续冬笔下的诗何以群,或者说,并不足够。
十多年前,我也曾是一个文学社团的土鳖文学青年,那时对胡续冬还有他诗中表现出的那种冒犯或者推搡,多少有一种不适感,这也让我错失了很多与他深入交流的机会。如今重新阅读他的诗作,忽然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在那些张牙舞爪、戏谑夸张的诗句背后,其实一直藏身另外一个胡续冬:深情,天真,有着深沉而严肃的关切。当你在《回乡偶书》中读到他这样写那些洗头妹:“洗头的妹儿多含一口鸭儿,就为/乡下的娃儿多挣了一口饭。”还会觉得这是一句不洁的诗吗?当你在《犰狳》中读到:“精英们不愿提及那些黑夜的喉结上/一小片茧皮一样喑哑的,不可见的后裔。”没人会觉得这只是一首简单的博物诗。姜涛说胡续冬把朋友圈搬到了他的诗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为亡友写下那么多的悼念诗篇,据他的朋友说,他去世那天是中元节,他还为亡友马雁和马骅准备了晚上要烧的纸钱。
胡续冬曾用“金蝉脱壳”形容臧棣的诗歌艺术,其实对他来说,何尝不是如此。正是在一个个轻盈的蝉蜕之上,我们得以窥见夏日曾经许诺的盛大,还有那份生命的热力与嘈杂。 胡续冬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