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筠入馆
作者:卜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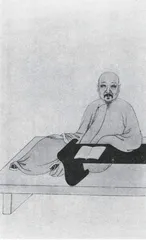 兴修《四库全书》,功臣和苦臣甚多,朱筠应属首功之臣:是他奏请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引起乾隆帝的极大兴趣,致使原本的征书变为编书;是他提出对民间珍本“官抄其副,给还原书”的思路,为乾隆采纳,使一场极可能发生的强征变得文明了许多;是他建言“兼收图谱一门”,扩展了传统的藏书范围;是他提议为每种书撰写提要,“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催生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是他热诚识拔和聚拢人才,将之推荐到四库馆。本连载一路写来,常会提到此公,终于可作专节记述了。书写追摹一个高贵的灵魂,总是令人愉悦的。
兴修《四库全书》,功臣和苦臣甚多,朱筠应属首功之臣:是他奏请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引起乾隆帝的极大兴趣,致使原本的征书变为编书;是他提出对民间珍本“官抄其副,给还原书”的思路,为乾隆采纳,使一场极可能发生的强征变得文明了许多;是他建言“兼收图谱一门”,扩展了传统的藏书范围;是他提议为每种书撰写提要,“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催生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是他热诚识拔和聚拢人才,将之推荐到四库馆。本连载一路写来,常会提到此公,终于可作专节记述了。书写追摹一个高贵的灵魂,总是令人愉悦的。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安徽学政朱筠奏报献书之事,称在各地巡考时发动生员提供线索,组织抄录,陆续上交巡抚衙门;自己数十年来收藏亦多,已将随身携带的珍稀图书十余种誊清,转巡抚衙门集中呈送;更多善本存于京寓,由门人程晋芳、史积容代管,现据记忆开列宋元集部目录40余种呈览,“伏祈皇上可否即以臣所开单付馆,令臣程晋芳等拣取校录,其可用者附入全书,缮录进呈,俾陈册幽光彰发轩露,臣所抱献,与有荣施”。京中官员献书之事,一个多月前就由刘统勋等奏请批准,朱筠属于积极响应,做法则有些着痕迹。他完全可以写信给程晋芳,或纪昀,或于敏中、王际华,似不宜直接报告皇上,再由皇上一级级交办。更觉不妥的是后面的一句:“至其录讫原本及无用者,仍发交程晋芳等领收。”呵呵,像是将皇上当成办事员了。朱筠明爽单纯,急于向皇上表达忠心(哪个臣子不如此呢),却忽略了一班近臣和四库馆总裁的感受。
当年九月下旬,朱筠还在一年一度的巡考过程中,将他降级调用的吏部咨文已自京师发出。据安徽巡抚裴宗锡的奏折,降级的缘由是“礼部参奏安徽学政朱筠将欠考三次、例应黜革之附生宋邦孚列入援纳项下”。每年统计在学诸生,例由府县学官逐级上报,学署仅负有审核之责,为何事发?又是谁捅到礼部?皆缺少具体记述。朱筠的性格,决定他会得罪一些人,也不知安徽官员抑或京中大佬是否借以发难?洪亮吉当时在幕,所作《书朱学士遗事》,另有解释:“其降调入都也,亦为门下士大兴徐瀚所误,瀚即司刊《说文》者,蓄厚资,后以饮博荡尽,先生仍录入门下,衣食之,卒不念前事云。”若此,问题还是出在学署中,是朱筠身边人在汇总制表上报时做了手脚。
朱筠并非出身豪富,热衷于购买善本,帮助朋友,提携晚进,很难有什么积蓄。安徽学政每年有4000两养廉银,本可缓解一下经济压力,可他竟邀请了十余幕友,又随时延揽门客,又要编校刊刻图书,必也捉襟见肘。而人一多故事便多,出点儿幺蛾子,也不意外。好在朱筠本人并无沾染,乾隆对他的印象甚佳,降旨:“朱筠因生员欠考捐贡一案,议降三级调用,自属应得处分。念其学问尚优,着加恩授为编修,在办理四库全书处行走。”这份谕旨是裴宗锡在安庆当面宣读的,朱筠刚刚从考场出来,跪聆之下,大约有些个“懵圈”。他的教育试点已见成效,正带着一帮志同道合者勾画蓝图,孰知竟此戛然而止。皇命如天,朱筠只能立刻交出旗牌印信等物,打道回府。对于皇上这样的安排是必须谢恩的,未看到朱筠的谢恩折,倒是其弟朱珪闻讯上奏:“在臣兄感奋自新,宜何如报称,而臣之关情惊宠,实莫可名言。”比较起来,朱筠更牵挂的是署中幕友,将最贫穷的汪中推荐给好友冯廷丞,修书曰:“汪生,通人也。其学知经传之义,而达于史学,又善为古文词。筠在江南,尚或为之所,筠去恐遂穷死。其才当为世爱惜之。”而对更多的人,怕也爱莫能助了。
解任后,朱筠本想游历东南山水名胜,找个好地方休息一段时间,哪知廷臣以皇上屡屡问及,催促速回。而他似乎不急,在太平学署停顿约20天,路过南京、扬州等地皆盘桓数日,至春节前才回到北京。弟子黄钺、王念孙随同北上。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朱筠到四库馆上班,受到老友的热诚欢迎,纪昀、姚鼐、程晋芳等皆为之赋诗,朱筠一一作答,其和纪昀诗中,有句“江南君行璧几碎,我璞一跌亦一斑。乃知鬼神瞰吾辈,奇福忌享佳水山”,感慨系之。
朱筠重节操,向来不事攀附,早年曾在大学士刘统勋府上处馆,成进士入翰林后则不再登门。一日相遇于途,统勋问之何故形影罕见,答以无公事不敢擅入贵人府邸,受到激赏。但这只是一个特例,不是所有的大吏都有这份胸襟。朱筠进入四库馆,以其学识、能力和对该项目的贡献,理应作为总纂、总阅人选,怎知只给了一个纂修。或因刚刚因事贬官,应徐徐安排,而在当年十一月刘统勋病逝后,便无人为他说话。四库馆前期纂修事务的主持人为于敏中,表面上待人温煦,实则行事颇有几分霸气,对在馆众翰林也是任意调遣。因其职事繁忙,遇有文稿问题,便要馆臣到军机处直庐或私邸面谈。这也是很多纂修乐为之事,趁机休息一下,顺便在上官跟前表现表现,有何不可?朱筠则坚守翰林修书的惯例,认为总裁与纂修应该相见于馆所,拒绝前往。一次在同事劝说下勉强一见,结果当面争执起来,“先生持论侃直不稍下”,整得于相国很尴尬。后来朱珪因事由山西布政使贬归,兄弟二人同在翰林,私下里劝告哥哥不宜过直,应讲究些上下和谐。朱筠反问:“连你也这样说吗?”弟弟连称惭愧,从心里承认哥哥是对的。
多数馆臣也认可甚至敬佩朱筠的做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朱筠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核心,过往密切者有翁方纲、姚鼐、曹学闵、程晋芳、钱载等,西郊北园,名寺古刹,看桃花,赏海棠,诗酒唱和。次年三月三日相约至右安门外十里的草桥修禊,竟有28人,就连公认的书呆子周永年也在其列,未及参与者当晚复集于曹学闵家中,合之得39人,多数为四库馆臣。朱筠作《草桥修禊序》,曰:
昔人之会者不必是水,今日是水之会不必其恒是人也,然则诸君子其将以喻夫庄生所云野马尘埃之相吹者,而偶集于斯,不其信乎?
令人神往的幸福生活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一些馆臣整天想着约酒和诗,游览名胜,上班时仍宿醉未醒,又怎么编好文稿呢?
开馆之初,刘统勋、于敏中等就遵旨制订了编纂条例,对不同岗位的纂修分校也规定了课程(任务量),具体到每月乃至每天。像朱筠这样是不可能完成课程的,于敏中忍无可忍,一次借机向皇上告状。孰料弘历并未发作,只说:“命蒋赐棨趣之。”赐棨时以户部侍郎、顺天府尹兼《日下旧闻考》督办,皇上让其催促朱筠,也是已知于氏那点小算计了。 朱筠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