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涅丝、历史之轻与小说的隐喻
作者:袁筱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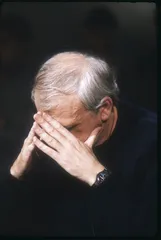 昆德拉在《不朽》的开头直接以叙事者的身份进入了小说,他同时还兼有小说人物的功能,闯入了小说的虚构之地,见证了自己笔下人物的诞生。那个叫昆德拉的“我”在泳池边看到一个女人“做了一个手势”,于是,“在一刹那间,她那种不从属于时间的魅力的本质显现出来,把我迷住了。我心里异常激动。这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阿涅丝这个名字”。
昆德拉在《不朽》的开头直接以叙事者的身份进入了小说,他同时还兼有小说人物的功能,闯入了小说的虚构之地,见证了自己笔下人物的诞生。那个叫昆德拉的“我”在泳池边看到一个女人“做了一个手势”,于是,“在一刹那间,她那种不从属于时间的魅力的本质显现出来,把我迷住了。我心里异常激动。这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阿涅丝这个名字”。阿涅丝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大概六十岁,或者六十五岁”的女人。她已经经历了人生的大半,能够摒弃幻觉,平静地面对真相。昆德拉让《不朽》里的阿涅丝不再直接承受既定历史阶段、既定国家、既定制度、既定民族的沉重,这就使得她有可能与大写的历史脱钩,和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成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失去典范意义的小说人物。她出生于普通家庭,有丈夫和女儿,还有一个和丈夫相处颇为和谐却总和自己意见不一的妹妹。她每周的日程也分为工作日和周末,休息日比在办公室工作还要累得多:去邮局、采购、维修家里的设备、打扫卫生,或者还要去桑拿——因为桑拿的时间,是她能够停下来,思考自己究竟是谁,和周围的人究竟有何种区别的时间。
阿涅丝是谁呢?简单来说,她是昆德拉安排在小说世界的一个提问者,失去了具体的社会意义,与存在拉开一段距离。作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她合法地替代了昆德拉——当然也合法地替代了我们——从人“希望不朽”的存在符码入手,向自己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存在的问题:人为什么是“我”?人与他者的本质区别在哪里?人期待永恒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永远是无经验的人,永远不能够避免重复那些诸如战争之类的蠢事呢?在一个最大的对立似乎已然消失的时代,人类就此得到安宁了吗?
阿涅丝没有直接回答她向自己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她更像一个阅读者,也是一个观察者。阿涅丝知道自己与“肩膀上扛着一个脑袋”的生灵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和丈夫不一样,和妹妹不一样。妹妹洛拉的图解由一个向上(上半部分)和一个向下(下半部分)的箭头构成:“她的充满幻想的脑袋仰望天空。但是她的身体坠向地面:屁股和乳房——也是沉甸甸的,往下凝视。”阿涅丝的图解则由一个向下(上半部分)和一个向上(下半部分)的箭头构成,表示“她的身体像火焰一样升起,但她的头总是略微耷拉着,凝视地下的抱着怀疑态度的头”。
于是阿涅丝的“自我”时不时地会跳到一边,审视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个现代人构成的世界。人人都在说,都在展现自我,人人都在试图说服他人,人人都在将所谓的自由演变为一种权利,人人都试图凭借这种将自由演变为权利的游戏进入一个“同一”的社会。我们以自由为名,获得了一系列权利——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指责他人的权利,甚至是裸体的权利。只是,阿涅丝的问题接着又来了:如果所有的自由都成了“权利”,如果我们都是“自由”的,并且这“自由”不具有普适的意义,而只是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那么我们的自由还有什么意义呢?这种将个人的自由变成普世价值的“权利”的希望,难道不是人类冲突的根源吗?
于是在小说的最后,其实并不遵从小说既定规则的昆德拉却没有忘记再回到人物的诞生之初,再次使用那个叫作昆德拉的“我”的视角:“汽车在按喇叭,传来愤怒的喊叫声。从前,在同样的环境里,阿涅丝想买一株勿忘我,只一株勿忘我;她想把它置于自己眼睛前面,当作隐约可见的美的最后痕迹。”
因为诞生于一个手势中的阿涅丝在确信了自己想要与这个现代社会分道扬镳之后,梦想着在生命的某一天,她同样借助一个手势“遁出”,买上一株勿忘我,“只要一株,细细的茎上一朵小花。她要把这株草举在面前走到街上去,眼睛紧盯着它,除了这点魅力的蓝色以外什么也看不到。这是她想保留的她已经不爱的世界最后的形象”。
一朵蓝色的小花,或许这是《不朽》中最打动人的意象。因为我们无法否认,即便我们个体的存在也是“由一个向上和一个向下的箭头”构成,在某些“凝视地下”的时刻,我们还是会对自己产生怀疑,我们也曾希望通过凝视一朵蓝色的小花忘记自身的存在。 作为存在符码的“不朽”是阿涅丝一系列疑问的反面,是我们每个人不假思索确信应该向往的东西,那就是:无论是借助荣耀、爱情甚或是现代社会媒介手段纯属偶然创造出来的“走红”,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借以抵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死亡。因为有那么多过来人告诉我们,倘若肉体终将泯灭,历史却是永恒的记忆,能够进入历史也就意味着获得了永恒。
作为存在符码的“不朽”是阿涅丝一系列疑问的反面,是我们每个人不假思索确信应该向往的东西,那就是:无论是借助荣耀、爱情甚或是现代社会媒介手段纯属偶然创造出来的“走红”,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借以抵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死亡。因为有那么多过来人告诉我们,倘若肉体终将泯灭,历史却是永恒的记忆,能够进入历史也就意味着获得了永恒。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已经不无残酷地揭示出一个我们不愿面对的,有关历史的真相:我们渴望历史的沉重,觉得这份重量可以赋予我们的存在以价值,然而历史之重一旦被消解,我们就会发现,人的价值也随之消解。
从《不朽》之后,昆德拉的小说就彻底进入了历史虚无的状态。他甚至不再展现此前执着的一个事实,即历史仿佛一个玩笑,在不断解构自身。从《不朽》开始,昆德拉只为我们描绘失去历史之重后人类所处的平庸境遇,这些碎片一般的个人记忆的垃圾有助于我们理解到“不朽”的本质。对于没有得到“历史之重”的机会的人来说,有一种构筑自己存在的方法,那就是创造历史,或者说,拼命挤进“历史的舞台”——因为历史好歹留下了它象征的空壳——让自己在历史的聚光灯下大放异彩。等待历史呈现出机会是被动的,但是,镌刻进历史可以是自己掌握的。
人类抵达“不朽”的途径多种多样,造成的结果也是多种多样。政治家的表演是其中的一种,例如竞选成功之后,手执三朵玫瑰的密特朗;而诗歌或者其他形式的艺术也是其中的一种,例如歌德、海明威、贝多芬(谁叫他创作了作为“不朽”象征的《英雄》呢)、毕加索,嚷嚷着“必须绝对现代”的诗人兰波,以及昆德拉自己塑造出来的诗人,《生活在别处》里的主人公雅罗米尔;一无所长的普通人不断地伸张自己的主张也是其中的一种,例如在小说开始,那个“宣称痛恨热水澡的陌生女人”,她“像一个女战士那样把自己呈现在大家面前”,通过“告诉所有在场的女人:(一)她喜欢出汗;(二)她非常喜欢骄傲的人;(三)她蔑视谦虚的人;(四)她喜欢冷水淋浴;(五)她对洗热水澡深恶痛绝”,她“用无数根线条勾勒出了她自己的形象”,从而也有了跻身不朽的可能。
退一万步,爱情或许也可能成为我们的第二次机会。不是留在大写的历史的大舞台上,而是留在对方记忆的小舞台上——谁说私人关系就不算是历史呢,尤其是在混淆了公众与私人空间的今天?由此贝蒂娜就通过歌德留在了“大写的”历史上。因为即便我们不能够创造历史,我们也能够抓住创造历史的人的衣襟。而现代社会超越歌德时代的关键在于媒体手段的发展:摄影、摄像、电视直播,再加上昆德拉尚未来得及涉及的网络虚拟空间,使得“历史的舞台”更成为一个虚空的象征。卸下所有历史重负的《不朽》也由此从存在的角度而言成为昆德拉最为丰富的作品之一。因为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昆德拉借助阿涅丝的思考验证了“世界是价值(源于中世纪的价值)贬值的进程,这一进程绵延现代的四个世纪,是现代的本质”。在此前的小说里因为意识形态的对峙而延搁的没有一下子崩溃的价值——秩序、忠诚、牺牲、理想、崇高等——于是以另一种形式一一得到了清算。
只是昆德拉要说的是,所有这些人类以为在其中可以得到救赎的价值,都抵不过阿涅丝想要买下的那株勿忘我上的一朵小蓝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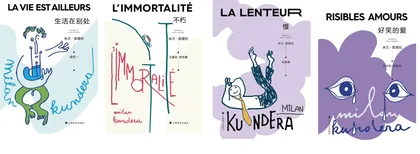 熟悉昆德拉的人都理解《不朽》在昆德拉作品整体中所具有的转折意义。《不朽》仍然是用捷克语创作的,并且保留了昆德拉一贯迷恋的七部分结构,但是其法译本则由昆德拉本人和艾娃·布洛赫合作,历时九个月共同完成。而从内容上来看,《不朽》中的人物第一次跳出了捷克背景。此后,小说《慢》《身份》《无知》和《庆祝无意义》均用法语直接完成,人物也继续置身于西方的生活环境中。这几部小说相较于《不朽》之前的作品,改变了从部分到章节的构成形式,直接划分为章节,篇幅也比较短,彻底进入了昆德拉的“轻小说”时代。因而如果我们把昆德拉的作品整体分为“上半时”与“下半时”——我们姑且使用他在阐述欧洲小说史时所用的语汇——昆德拉私人小说史的上半时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结束,下半时则以《慢》开篇,《不朽》居于上半时与下半时的中间,是一种总结与交代,也是一种消解与否定,更是一种澄清与宣告。
熟悉昆德拉的人都理解《不朽》在昆德拉作品整体中所具有的转折意义。《不朽》仍然是用捷克语创作的,并且保留了昆德拉一贯迷恋的七部分结构,但是其法译本则由昆德拉本人和艾娃·布洛赫合作,历时九个月共同完成。而从内容上来看,《不朽》中的人物第一次跳出了捷克背景。此后,小说《慢》《身份》《无知》和《庆祝无意义》均用法语直接完成,人物也继续置身于西方的生活环境中。这几部小说相较于《不朽》之前的作品,改变了从部分到章节的构成形式,直接划分为章节,篇幅也比较短,彻底进入了昆德拉的“轻小说”时代。因而如果我们把昆德拉的作品整体分为“上半时”与“下半时”——我们姑且使用他在阐述欧洲小说史时所用的语汇——昆德拉私人小说史的上半时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结束,下半时则以《慢》开篇,《不朽》居于上半时与下半时的中间,是一种总结与交代,也是一种消解与否定,更是一种澄清与宣告。
在昆德拉小说史的“上半时”,他的小说基本上都是用捷克语写成的“大作品”——即便像《好笑的爱》这样的短篇小说集也被昆德拉赋予了“变奏”的形式概念,因而也和一般的短篇小说集不同,可以被当作一个作品整体来对待——有严谨的、对称性的结构,也大多围绕同一(组)主人公的情节展开,尽管情节不一定是按照线性的逻辑来推进的。这种结构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得到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实现,例如七个部分——在星相学杂志上做过专栏作者的昆德拉迷信“7”这个数字——借助关键词不断展开的离题,人物和情节意义的对称展开等。昆德拉的小说野心从《玩笑》开始就已经在了,只是被所谓的历史之重遮掩。正是经历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误读高潮之后,愤怒的昆德拉将《不朽》变成了自己最好的反击机会。
《不朽》并没有终结“昆德拉式”叙事,恰恰相反,它甚至强化了该叙事的所有要素,乃至可以被看作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小说分成七个部分,在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不解之词”同样的位置——都是第三部——作者也同样安排了由一组关键意象组成的“斗争”。小说仍然充满了“哲学暂停”,例如和尼采永恒轮回概念相类似的“钟面”意象。种种二元对立的存在态度也通过人物在每一个细节处交锋。我们于是看到了作为对称人物的阿涅丝和洛拉姐妹,历史真实中的歌德、海明威、密特朗与现实虚构里的洛拉、保罗、贝尔纳的遥相呼应。不同空间的人物进入同一个虚构空间,又带来了昆德拉所谓的多声部、对位式的叙事方式。
但是《不朽》和其“上半时”作品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另一个故事,或者说是基于同一(组)主题的变奏,它是对此前所有作品的“合成”。在《不朽》中,昆德拉彻底放弃了对于小说某种不成文的约定,废黜了虚构世界的边界,不仅让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作为作者和叙事者的自己,乃至于自己笔下的人物共同居住在同一个小说世界里发生关联,阿涅丝这个人物因而也同时负有和读者一起发现新道路,从而一起迷失的“任务”。《不朽》这部小说本身就像是阿涅丝喜爱漫步的树林,一条小径的最终意义并不取决于它的尽头,而是取决于它在半途中岔开去连接上的另一条小径。
在《不朽》之后,昆德拉一改“大作品”的进路,开始创作“小型”的“赋格曲”:随着我们的存在不再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向历史提问,存在的范畴也都分裂成一个个不再等待答案,似乎也无从改变的“无意义”的问题。和语言失去“意义”的重要性一样,当同一的世界将人类的行为演变成自我重复,演变成“对自己的滑稽模仿”,昆德拉的小说也改变了提问的方式。不再是通过一个类似“不朽”的存在符码进入存在的所有面向,而是一一探讨“不朽”这个母题所包含的“子题”。《身份》是对现代社会人人张扬的“自我”的拷问。《慢》探讨的是在快速、疯狂的自我重复中,速度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无知》展现的是在世界趋同的观念中,人会不由自主地走向自己先前所界定的存在的反面。这个尤利西斯式的问题似乎答案明确,即从时间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是永远回不去的。《庆祝无意义》更像是一个告别的手势,将一切意义消解为无。那也是一个俏皮的手势,就像阿涅丝的手势一样,“这是一个淹没在已经衰老的躯体里的富有魅力的手势”。
而今,已经衰老的躯体真正“遁出”了这个世界。或许,对于他最好的纪念就是接受阿涅丝的暗示,买一株勿忘我(《不朽》),通过凝视性的阅读来忘却这个并非是被“人类进步”而是被“病菌”同一化了的世界吧。
(袁筱一,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教授,米兰·昆德拉作品《生活在别处》译者) 米兰·昆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