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别处
作者:陆晶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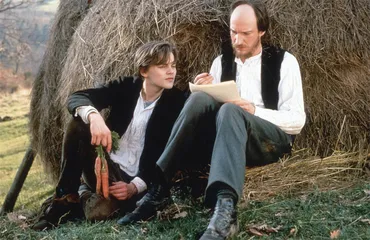 “生活在别处”是兰波说的。兰波是法国诗人,19岁前就已经完成了足以让他载入史册的所有诗歌。兰波从小就想离开故乡,有一次他出门散步,忽然就爬上了去巴黎的火车。
“生活在别处”是兰波说的。兰波是法国诗人,19岁前就已经完成了足以让他载入史册的所有诗歌。兰波从小就想离开故乡,有一次他出门散步,忽然就爬上了去巴黎的火车。兰波生活在19世纪末,那个年代很多诗人活得都不长。普希金活了38岁,莱蒙托夫27岁。兰波的生平很多人都不熟悉,兰波活了37岁,停止诗歌创作之后,兰波当过水手,卖过咖啡,甚至还当过军火贩子,发了财。总之就是再没写过诗,他在一封信里说,“我死于疲惫”。但后来的人们记住他,主要是因为他的一张照片。那时候他应该和现在的初中生差不多年纪,眼神高傲又迷离。他应该对自己的诗歌才能已经有了强烈的意识。其实今天的读者不那么容易理解兰波的诗,很多分析者甚至认为他根本就没想让我们以常人的方式去理解。但这不妨碍兰波在文学史上留下的形象,他的生平也是一件作品,先少年成名,再神秘地否定自己。总是去远方,最后死在远方。
相比那些直到老年还在写作的职业诗人,人们偏爱少年的天才诗人:这个身份包含了对我们这个充满日常细节的世界的双重否定。少年意味着他还没有被世界的琐碎毒害,没有背负上生活的重担,而天才诗人代表他超越我们平时生活的维度,代表人类可以超越平庸,到达更高的境界。他们就像是在替代另一些人生活一样。
这两者就构成了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的起点。这本小说是对诗歌非常激烈的挑战。它认为诗歌的基础很可疑,而和少年结合在一起,并为人所崇拜,就更加无法原谅。传记作家说这是因为昆德拉年轻的时候写诗,后来也像兰波一样骤然停笔,觉今是而昨非,作为对自己青春年代的告别,才写下了这本小说。这倒是有道理的,今天昆德拉已经名满全球,但谁也没见过他几首诗。其实,从根本上去冲击诗歌这种文体的基础,昆德拉算不上最激烈的。我们知道阿多诺在“二战”后曾经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欧洲人思考了那么多年的哲学和文学,最后竟然发生了奥斯维辛这么惨烈的灾难,如果不对这种灾难进行彻底的反思,还转过头去继续吟风弄月,这就不可理喻,就是野蛮的。这句话提出来的时候,人们都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但是诗人们也并没有停止写诗。
《生活在别处》写于1969年,世界已经是另外一副样子,欧洲分化成两个阵营。昆德拉是在阿多诺的基础上继续追问,我们理解人们有继续抒情的需要,但这种需要本身正当吗?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抒情呢?
这本小说的观点是,诗歌可能成了某种逃避,成了某种否定现实的借口。这种逃避始于认识上的幼稚,终结于审美上的庸俗。所以诗歌在阿多诺那里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昆德拉这里就是一个美学问题。总而言之,崇拜诗人是不对的,崇拜少年诗人更不对;没有什么别处的生活,没有什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只有你在当下,你清醒地活着。这是一个激进的挑战,但很不幸的是,他有时候是对的。
《生活在别处》讲了一个叫雅罗米尔的诗人的一生,诗人出生,诗人出名,最后诗人在很年轻的时候死去。他的一生从未摆脱他的母亲。很多诗人都被自己的母亲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关注,比如普希金一直忘不了他的奶妈,里尔克被自己的妈妈打扮成小女孩(他的中间名玛利亚是一个明显的女孩名字)。昆德拉在这里创造了一个和兰波的暴虐的母亲相反的角色——一个热爱文学的女人。她生来就是一个读者,等待自己的体验被书写,如果能够进入诗歌的世界,她将会感到非常光荣。小说开头,母亲就在回忆,到底是在哪里怀上了她的诗人儿子。答案是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下面。诗人只能是伟大爱情的结晶,而当这位母亲发现自己的丈夫并不像她以为的那样浪漫,自己的爱情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些生理的冲动,父亲在这个家里就已经象征性地死亡了。当然他后来也确实被纳粹杀死了——这并不重要,在此之前母亲已经把雅罗米尔当成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了。儿子是她生活合理性的来源,怀孕和分娩是丑陋和令人痛苦的,可是有了儿子,她就无视这些,认为一切都是美好的,她满怀激情地监控着儿子和自己的身体,觉得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都凝结在这个对世界一无所知的小生命上了。
有一次雅罗米尔对她说:“妈妈,我没那么小,我理解你。”这句话让母亲吓了一大跳。听到自己的孩子忽然说出一句成年人才会说的话,很多父母都有过这样的经验。雅罗米尔看到了自己母亲的惊慌和喜悦,这并非第一次,每当他说出一些与众不同但自己并非完全理解的话的时候,他都会得到赞赏和笑声,但这一次他得到了感动。我们今天的父母也会为这种一句话、一幅画或者一首歌带来的时刻骄傲,甚至去炫耀,也许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种魔法瞬间终将过去。不过,雅罗米尔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以为铺满鲜花。 对于诗人动机的追问是我们社会的禁忌,似乎追问这些就会让诗意损失殆尽。而昆德拉就像怀着恶意一样,如果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么在冷战的时代,他要让刚刚恢复过来的诗人的声誉原形毕露。
对于诗人动机的追问是我们社会的禁忌,似乎追问这些就会让诗意损失殆尽。而昆德拉就像怀着恶意一样,如果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么在冷战的时代,他要让刚刚恢复过来的诗人的声誉原形毕露。
雅罗米尔的第一首真正的诗源于屈辱。这是小说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情节,它奠定了诗人和世界关系的基调。雅罗米尔中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父母都不在家,他趴在浴室的钥匙孔那里偷看保姆洗澡。他本来打算下定决心闯进去,但保姆提前发现了并叫了起来,他不得不在懊恼中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对自己的欠缺决心和临场退缩不满,更为中断的性行为感到挫败。昆德拉的恶毒与巧妙之处,就是揭示了这种猥琐的卑贱和诗歌的崇高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躲向崇高,才可以面对堕落。在诗里,浴缸里的水变成了大海,他在门外偷窥时候的心跳现在在水面上激起了涟漪,保姆也不再是保姆,成了水中的爱人。他借此获得了对生活的主导权,不是生活的经验让他感到挫败,而是他的诗歌在统率着所有的经验。从此他获得了处理经验的本事,要走向世界了。
他和世界最初的关系是由和母亲的关系构成的。随着他年龄越来越大,母亲对他的依恋也越来越深。既然儿子是母亲生命中唯一的男人,那么这种依恋发展成控制欲,也就没什么奇怪了。生活中不缺乏这样的父母,他们对自己孩子的男女朋友怀有巨大的嫉妒。这是一种病态的情感。一方面,雅罗米尔得到母亲的爱,因为他是他父亲的替代,因为他会写诗;另一方面,雅罗米尔渴望得到另一个女人的爱,渴望得到世界的爱,也是因为他是他自己的替代,因为他会写诗。所以他通过诗歌表达,生活在别处,这也是在表达,他想要逃离这样的生活。在这一点上他又和他的母亲达成了一致。生活在别处的意思,不是去别处生活,而是只有在别处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这种心理就像是一种自我囚禁的牢笼,因为当任何的别处成了此处,到达的时刻也就是厌倦的时刻,就要开始寻找另外的别处。这是抒情的逻辑,在抒情诗歌里,一件东西从来不会因为它是它自己而得到赞叹,它一定要经由诗人的眼睛和心灵,变成另一样东西,例如滤镜下的糖霜,或者梦中的鲜花,什么都可以是,但永远不会是它自己本身。
我们在这里看到母亲和儿子同样地在借助诗歌逃避生活。母亲逃避没有爱情的命运,儿子逃避被母爱囚禁的命运。之后雅罗米尔和不同的女人恋爱的过程中,母亲都像一个幽灵一样笼罩在他的上方。但他也没有放弃用诗歌来折磨他的母亲。自从雅罗米尔在家庭的赞叹里意识到,自己是这个社会选中的人以后,他就从来没放弃过诗歌给他带来的权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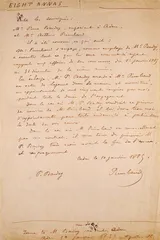 兰波后来来到巴黎,摆脱了他的母亲。雅罗米尔也来到了布拉格,他入了党。就像当初在家里,他因为提前窥见了诗歌世界的秘密而得到褒奖一样,在政治的世界里,一个年轻的诗人也总是受到欢迎。少年雅罗米尔认为诗是对世界的甜腻的变形,青年雅罗米尔认为诗和革命一样,是这个世界上最先锋的东西。母亲不是觉得诗歌必须押韵,必须优美吗?布拉格的秩序鼓励他告别过去的诗歌,反其道而行之。母亲不是觉得在世界面前炫耀自己,和真正走入世界不是一回事吗?他可以借助诗歌的武器,去为这个接受并鼓励他的新秩序战斗。只要世界还在崇拜青春、崇拜天才,雅罗米尔就可以顺利找到自己的位置。他有能力把歌颂工人阶级和他的诗歌艺术融为一体,这是了不起的一步,帮他超越了兰波,战胜了母亲,不过,他还需要向世界做出最后一个动作,否则诗人和世界的关系,就还是文字和象征的关系,而不是实在的、有重量的,像铁锤和铁砧之间的关系。
兰波后来来到巴黎,摆脱了他的母亲。雅罗米尔也来到了布拉格,他入了党。就像当初在家里,他因为提前窥见了诗歌世界的秘密而得到褒奖一样,在政治的世界里,一个年轻的诗人也总是受到欢迎。少年雅罗米尔认为诗是对世界的甜腻的变形,青年雅罗米尔认为诗和革命一样,是这个世界上最先锋的东西。母亲不是觉得诗歌必须押韵,必须优美吗?布拉格的秩序鼓励他告别过去的诗歌,反其道而行之。母亲不是觉得在世界面前炫耀自己,和真正走入世界不是一回事吗?他可以借助诗歌的武器,去为这个接受并鼓励他的新秩序战斗。只要世界还在崇拜青春、崇拜天才,雅罗米尔就可以顺利找到自己的位置。他有能力把歌颂工人阶级和他的诗歌艺术融为一体,这是了不起的一步,帮他超越了兰波,战胜了母亲,不过,他还需要向世界做出最后一个动作,否则诗人和世界的关系,就还是文字和象征的关系,而不是实在的、有重量的,像铁锤和铁砧之间的关系。
他向自己的小学同学、安全局的警察举报了女朋友的哥哥偷渡。举报给他带来崇高感。首先因为他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违背了不应该告密的人性;其次,也因为他做的事不再是写漂亮的句子,而是真实的,影响了他人的命运。只有他通过主动的行为,让女朋友因为她的哥哥被审讯、被折磨,他才完成了对这个女人最真实的占有,因为他主宰了这个女人的命运。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雅罗米尔对于世界也有一种病态的掌控欲了。
在小说的结尾,昆德拉表达了明确的意图,他认为诗人在现实面前永远是无力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在决斗中丧生,这就是诗歌企图走入现实的结局。雅罗米尔通过告密,享受了掌控现实的感觉,但他却在一次口角里被人推出房间,得了肺炎,几天以后就死了。他临死的时候,又重新回到孩子的状态。他握着妈妈的手说:“妈妈,我最爱的女人是你。”妈妈流下了幸福的泪水。透过泪水,她周围的事物都挣脱了原来的桎梏和形状,兴高采烈地跳着舞。母亲失去了儿子,获得了诗意。雅罗米尔看到的最后的东西,是他自己在水面上的倒影,说到底他的整个生命,就像那喀索斯一样是一场自恋。他死的时候仍然是一个少年。最后诗歌的读者战胜了诗歌,母亲战胜了儿子,她借助儿子的死亡,永远把儿子留在了自己身边,并且他从此永远是从未长大的孩子形象。崇拜青春是一种恋尸癖般的激情,它要求对方在生命的某一个点停止,不再变化。
《生活在别处》是《堂吉诃德》和《包法利夫人》序列上的作品,它告诉我们糟糕的作者不可怕,糟糕的读者才可怕。一开始它的书名叫《抒情年代》,抒情是作者和读者的共谋,比如《荔枝蜜》这样的东西,是作者在尝试抒情,如果我们对它无动于衷,抒情就会变得非常可笑。但更多时候,抒情是受人欢迎的游戏。这本小说里,母亲首先是一个读者,才能培养出儿子这样的诗人。抒情的诗歌就像是爱丽丝故事里的镜子,把我们与真正的世界隔绝开来,它让我们舒服,喝下糖水,也让我们停留在童年。一个人能够把耻辱转换成崇高,意味着他可以靠抒情自给自足,那他就无法在真正的世界里成长。童年是纯真的,但纯真的另一面就是幼稚。
昆德拉不能同意世界在抒情中陷入幼稚。后来,他在对抒情的批判上,发展出了更有力的对媚俗的批判。那就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故事。那里面也有一个“生活在别处”的人物,小城少女特蕾莎带着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着她所有的东西,只身来到布拉格。在故事的结尾,特蕾莎和她的爱人托马斯厌倦了大城市里无所不在的媚俗,去农村生活,这看起来又是一次“生活在别处”的尝试。但在一次出行中,特蕾莎和托马斯的卡车刹车坏了,他们一起死于车祸。昆德拉在这两本小说里同样想表达的是,镜子那边什么都没有,没有田园牧歌,更没有什么诗与远方。没有什么别处,只要想着在别处,就永远无法停止流浪。 阿瑟·兰波米兰·昆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