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疾病和封闭
作者:吴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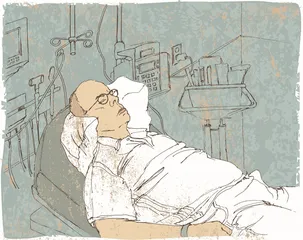 吴志坚的肝炎带给小家庭的压力,外人很晚才知道。吴谢宇后来一直说,爸妈没有告诉他真实病情,直到父亲去世,他都不知道父亲不行了,也不知道是肝癌,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吴志坚的肝炎带给小家庭的压力,外人很晚才知道。吴谢宇后来一直说,爸妈没有告诉他真实病情,直到父亲去世,他都不知道父亲不行了,也不知道是肝癌,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在70平方米洁净的家庭空间里,吴志坚的疾病就像房间里的大象,都看见了,但是没有人去坦率地谈论它。吴谢宇看到的是,妈妈早上五点多就起床,忙到晚上九十点睡下。“妈妈最讨厌医院消毒水的味道,却不得不每周带着爸爸去医院。”吴志坚总是在喝药,自嘲是“药罐子”,吴谢宇认为妈妈总是看起来很累。
吴志坚的父亲39岁去世,给他们一家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吴志坚太了解,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男性英年早逝,家族命运会遭遇什么。仙游老家还有一大家子等着吴志坚来托举,他本来在事业上有很好的前途,现在却什么也做不了。吴志坚内心的痛苦,几乎没有向人倾诉过。
谢天琴在婚姻早期相对明亮的心情,逐渐暗淡了下来。她本来就认为自己的命不好,随着父亲平反、她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在福州建立了小家庭,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机。而丈夫的肝炎以一种不断加重的方式在发展,未来不再值得展望,它很可能变成这家子“孤儿寡母”的苦难,成了等在前头的深渊。谢天琴在情感上一直牢牢抓住老公和儿子,而现在对命运的恐惧再次被勾起,她后来向马老师提到,他们一家是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守着吴志坚度过了40岁。
在吴志坚生病的日子里,夫妻俩对病情一直守口如瓶。大姐阿花向我们提起来,说她一直不知道弟弟有肝炎,只是看他的面色总是黑黑的。事实上大姐不知道病情的可能性太小了,大姐的儿子阿勤有一段时间住在吴志坚家,好几次吴志坚回家晚了,谢天琴不让开门,阿勤想开也不让。谢天琴对于吴志坚在外边酒局应酬,非常不高兴,其中一部分原因,应该也是怕吴志坚病情加重。吴志坚后来向朋友说过,北京来的领导喜欢喝白酒,他不喝不合适。
病耻感折磨着吴志坚和谢天琴,吴谢宇被隔离在信息之外,谢天琴把自己的一部分恐惧,化成让小宇少接触爸爸,觉得这样保护了孩子。但家里的氛围,让孩子实际上很不安。“我从来都极度自卑,没有自我,没有主见,于是我总是在模仿,我在书本里、屏幕上看到一个主人公,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要模仿。”谢天琴的自卑,是有实实在在客观原因的。而吴谢宇作为下一代人,从小在城市长大,爸爸妈妈是上世纪80年代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他从小聪明伶俐,哪里需要自卑呢?他幼小的心灵,在事实上承担着妈妈的情绪。妈妈看上去总是不快乐的,吴谢宇从来不敢问,只能是自己猜。是不是哪里没做好,又让妈妈不高兴了?
吴志坚担负的责任,一点也没有减少。他的收入,有相当一部分要留给大家庭。他在2008年左右跟关系亲密的人提到,每年回老家,除了给自家人钱,还要给村里老人钱,至少得一两万的花销。大姐一家是吴志坚惦念的重点,他在职业生涯里发展的关系,有相当一部分用来给大姐一家谋出路。吴志坚一度瞅准单位食堂承包的机会,让大姐与朋友合伙,拿下食堂的经营权。有同事在外地发展了业务,他疏通关系后,把这块业务的物流生意给了姐夫。姐姐姐夫没有文化,也缺一技傍身,谋生总是随着各种外在环境的变动,起起伏伏。
吴志坚搭建的各种关系,只要能解决姐姐姐夫暂时的生存问题,他都不惜力。这方面张力文很肯定吴志坚的能力,吴志坚轻易不求人,但跟人打交道也不怵,“虽然他的出身是个农村人,但他跟领导打交道很自然,不卑不亢。像我总是躲着领导,不自信,我还挺佩服他的”。
吴志坚最小的妹妹有智力缺陷而精神不正常,吴志坚帮她找了外地电工张明,做吴家的入赘女婿。张明仰仗着吴志坚的接济,每次吴志坚和谢天琴带着孩子回家,他都表现得特别热情。有一次他花20元买了盘肥肠,吴志坚温和地教育他,花钱还是要节约,细水长流。因为吴志坚还得负担张明两个孩子的很多开支。谢天琴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抱怨,所以虽然她态度上总是比较冷淡,但张明对她也很感激。
2008年,因为病情进展,吴志坚接受了一次介入手术。直到第二年,他关系非常好的朋友患癌,另一个朋友陆国鹏早些年下海做医疗生意,医疗资源很多。在福州的一家医院被医生判了“死刑”后,经过各种比较权衡之后,陆国鹏为这位朋友找到上海的一家医院做了手术,相当成功。这件事情后,吴志坚也找到陆国鹏,讲述了自己做介入手术的事情。张力文和陆国鹏这才知道吴志坚的病,很吃惊:“都得病这么多年了,平时我们聚会也不吭一声,做手术这么大的决定,也不到处寻求信息!” 吴志坚的老家,福建仙游度尾镇潭边村2008年,转折点
吴志坚的老家,福建仙游度尾镇潭边村2008年,转折点
谢天琴和吴志坚的小家庭,曾经在朋友中比较领先。1998年,他们就在福州市区和郊区,各有了一套单位的福利房。调到南平铝厂在马尾的分厂后,吴志坚一开始在基建部,他与分管的副厂长关系不错,工作能力也强,成了基建科经理。2008年吴志坚的病情严重了,他被调到安防部当负责人,管理安全生产和厂里的门卫,比过去要边缘。吴志坚仍然在为姐姐一家谋出路,他把姐夫弄到厂里当了保安。张力文说:“吴志坚基本上也只能做到这些了,他也没有多大的权力。”
吴志坚仍然是工作和朋友圈子里比较活跃的一员。他喜欢穿花衣服,在同龄男性中并不多见。以他为中心的好友圈有十几个人,吴志坚很乐于组织大家聚起来,陆国鹏也感激他的付出:“他做事的风格,就是他都包了。只要大家愿意聚会,里边的细节都是他来考虑,哪个时间大家都合适?去哪个地方大家最方便?他都会给安排好。”等到朋友们聚在一起,他话不多。张力文说,事后回忆起来,他才意识到吴志坚也是个要强的人,“好的分享,坏的从来不说”。他是朋友中的倾听者,很少提自家的事情,所以朋友们一直认为他没有什么困难,家庭生活也很和谐。
2008年前后,吴志坚将马尾78平方米的福利房卖了,换了一套98平方米的房子,那时的房价每平方米3700元。他还买了一辆北京现代的车,这样上下班不用坐班车。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仍然是向上的。但是马尾这套房子,吴志坚是贷款来置换的,这笔贷款后来也成为谢天琴经济上的一个压力。这一买一卖,只用补20来平方米的差价,并且房子还贷款了二三十万元,对经济上的要求并不高。但是吴志坚也得找朋友借钱。
吴志坚在度尾镇的老家,仍然是全村最穷的土坯房。有着光宗耀祖愿望的吴志坚,如果稍有点经济能力,他不会不在老家建新房。陆国鹏1994年就下海经商了,几年后回老家盖了新房,“我们这些人习惯有钱了回家盖房,给父母改善生活,也是给自家挣个脸面”。
莆田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市场经济中,一度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莆田人“垄断”了全国不少细分门类的生意,比如加油站、金银加工、民营医院、制鞋等。但在“莆田人”这个大概念之下,不同地域的莆田人,又表现为不同的特点。改革开放前,因为地理资源的不同,平原的莆田人生活最好,大山里的莆田人差些,但是海边的莆田人生活最苦。越苦的人越思变,所以几十年市场经济发展下来,海边的莆田人建立了不少商业帝国,反而是像吴志坚这样生活在平原的莆田人,整体变化没有那么大。
吴志坚所在的仙游,1983年与莆田县合并,成立了莆田市。仙游人和莆田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认为他们的气质不同。仙游人称自己为“海滨邹鲁”,文化气质强,不太认同莆田人闯荡商业社会的特点。吴志坚所在的度尾镇,尊重读书人,很少出商业强人。和下海经商的朋友比,吴志坚显得保守,他安心在铝厂发展,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创业。吴志坚的朋友圈子里,有些人抓住机会下海了,发展得很不错。
而文化程度不高的谢天琴的弟弟谢天运,在2006年也发了家。仙游在莆田各个区域里,经济发展比较晚,但最终等来了红木生意的红火。现在去仙游,也能在公路边、镇中心看到各种红木加工的商铺,形成了仙游的一个重要产业。谢天运结婚后,和老婆家的三姐妹一起做红木生意,2006年左右挣到了钱。谢天琴的妹夫说,谢天运那时候很快有了千万身家。仙游的老县城沿着木兰湖,那里建了一个高层的新小区,谢天运买了一套150平方米的房子,带着老母亲住了进去,成为县城新贵的一员。
但是对于弟弟变得有钱了,谢天琴心里是不开心的。她在日记里,指责他“有了几个钱就认为自己了不起”,说很讨厌人和人之间都是金钱关系。谢天琴对周围人的防范心一直比较重。她刚参加工作不久,弟弟入伍,照顾盲人父母的任务留给了妹妹两口子。但是对于妹夫刘裕宗,她写信提醒弟弟,要提防刘裕宗占自家的房子。刘裕宗无意间看到了信,非常生气,当天就要搬出去,以证清白。谢父苦苦挽留,说:“我们老两口要是没有你的照顾,那过的是个什么日子?我的房子愿意给谁就给谁,你不用在意。”
2008、2009年,当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在各种机会中一路向前的时候,吴志坚和谢天琴小家庭的发展势头,停滞了。
在吴志坚2010年去世后,谢天琴写给他的信里,提到了自己的失落。她抱怨自家一直住在一楼,灰尘多、蟑螂多,二楼是可恶的退休的领导。从她生活的福州火车站那一片的客观发展来说,漂亮的高层住宅越盖越多,“铁二中”的宿舍楼逐渐显得破旧了。“住在这套老房子,我的心情异常苦闷,原来我们有机会离开的,现在你走了,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了,现在寄希望于小宇,希望我们的儿子长大后远离这套房子,远离这座曾萦绕我们苦难的城市,远走高飞。” 2009年的一天,吴志坚拿到了自己新的诊断报告,是肝癌。他这才跟陆国鹏讲起一年多之前他做的介入手术,那时候他还只是肝硬化。2022年夏天在福州向我们讲起这件事,陆国鹏还是惋惜,“我当时就骂他,怎么不早一年来找我?从肝硬化到肝癌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段。如果他2008年的治疗方案选得好,可能不会走那么快。他这个人,太不愿意麻烦别人了。”陆国鹏急得骂他,吴志坚只是不吭声,他那时候看着状态还可以,陆国鹏没有预料到他后来病情进展那么快。
2009年的一天,吴志坚拿到了自己新的诊断报告,是肝癌。他这才跟陆国鹏讲起一年多之前他做的介入手术,那时候他还只是肝硬化。2022年夏天在福州向我们讲起这件事,陆国鹏还是惋惜,“我当时就骂他,怎么不早一年来找我?从肝硬化到肝癌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段。如果他2008年的治疗方案选得好,可能不会走那么快。他这个人,太不愿意麻烦别人了。”陆国鹏急得骂他,吴志坚只是不吭声,他那时候看着状态还可以,陆国鹏没有预料到他后来病情进展那么快。
朋友聚会的时候,吴志坚仍然会抢着买单,虽然大家真让他出钱的时候不多。不管是张力文还是陆国鹏,都是从农村靠着高考走出来的,对吴志坚特别惺惺相惜。陆国鹏说,高考对他们这些穷孩子是最公平的,让他们“能从穿草鞋变成穿皮鞋”。他们也肩负着把一大家子从农村带到城市的命运。
但细细比较起来,他们的负担却比吴志坚轻很多。
张力文的老家在仙游的大山里,家里的田地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梯田,窄的一米五,宽的不过两米。他的父母只靠种这几亩田,根本养不活家里的5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初中住校的时候,张力文要沿着山路一圈圈地走上四五个小时才能到家,背上一点咸菜,勉强回学校凑足一周的伙食。
张力文的妈妈能干,“文革”期间也偷偷砍芦苇编成席子卖。他爸爸初中毕业,是大队会计,空闲时到山上砍木头,再做成锅盖卖。待到张力文的大哥二哥高中毕业后工作,家里的生活就一下子改善了。1983年他家的土坯房重建了院子,90年代建起了楼房。
张力文1987年上大学,他的两个哥哥在泉州做建筑工,妹妹也开始打工了,挣的钱资助他读书。等到张力文开始工作,借着在铝厂做销售的机会,他在外边成立了运输公司,后来直接把公司给了大哥。等到2003年张力文结婚生孩子,他让妹妹来自家给他们带孩子做家务,一年给妹妹5万元。
二哥做橘子生意,每年资金需要周转的时候,张力文就给他垫上。二哥一般是10月份要钱,第二年到4月份还给张力文。这样在张力文的资助下,二哥的生意也做起来了。弟弟相对不争气,张力文给他出学费拿到了厨师证,帮他找各种出路。“我考出来了就给家人想各种办法,整个家族就被我拉出来了,这样一代就比一代好。”张力文的老婆是城里人,不太理解他的所谓家族责任,“三观不一样”,但是在经济上从来不拦着他。
陆国鹏作为从农村考出来的人,高考的时候为了求安稳,即使高出重点线60多分,他也没去报北京上海的好学校。因为怕滑档,怕错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家五个兄弟姐妹,三个考出农门,“一个带一个,就都出来了。几个孩子分担一下,担子都挑得起”。
作为吴志坚非常亲近的朋友,他们却并不知道吴志坚一个人挑起大家庭的困境。陆国鹏说,之前他们在一起,状态都很积极,说的都是正能量的事情。他认为,吴志坚不讲困难,是因为讲了也没用。“当你跟一个人倾诉的时候,是希望对方能够帮你化解,对不对?”
但是吴家的状况,其他人不可能长久地帮忙,正所谓帮急不帮穷。或许这也是吴志坚直到去世,也没有向任何人托付什么的原因。 谢天琴对于怎么处理婆家那边的关系,有她的各种苦恼。作为吴家的媳妇、作为小宇的妈妈和作为谢天琴这个个体自身,怎么平衡?她的选择是,把这种责任和物质付出画上等号。物质上的付出她做得到,也不太计较,但情感付出,她只能给亲密关系中的丈夫和儿子。
谢天琴对于怎么处理婆家那边的关系,有她的各种苦恼。作为吴家的媳妇、作为小宇的妈妈和作为谢天琴这个个体自身,怎么平衡?她的选择是,把这种责任和物质付出画上等号。物质上的付出她做得到,也不太计较,但情感付出,她只能给亲密关系中的丈夫和儿子。
住在楼上的马老师,成为她的知心人。谢天琴的盲人妈妈,几乎没有社会交往,没有能力告诉女儿,怎么应对成家之后的各种复杂关系。谢天琴随着婚姻关系的建立,被拉入这张以吴志坚为中心的、层层向外辐射的关系网。这个小家庭成为养分制造者,要全方位向大家庭和宗族输送养料。
阿花的儿子阿勤过来读初中,住在谢天琴家里。阿勤不是个爱读书的孩子,还特别调皮。按照谢天琴曾经向马老师的倾诉,因为阿勤不好管教,校长总是找谢天琴告状。吴志坚早出晚归,侄子吃喝拉撒的琐事,也是谢天琴照顾。本来把侄子弄到家里吃住,这对于很看重家庭的封闭空间的谢天琴,就是个不小的挑战。吴谢宇也很少经历与爸妈之外的人相处。家里来了客人,是每个人从小在不经意间学习模仿的交际能力。但对谢天琴来说,这些都是挑战。
谢天琴感到很苦恼,问马老师该怎么办。马老师坚定地说:“送回去!你是舅妈,孩子管好了跟你没关系,管不好了,都是你的错。”
谢天琴向马老师讨到了这个“方子”,但是该怎么跟丈夫商量,她是直说了,还是开不了口?两个人为此有没有冲突?外人不得而知。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事没有闹得太僵,因为侄子阿勤几年后又在谢天琴家住过一阵。马老师记得,读书这事,不太长的时间后,以阿勤被学校开除为结局。
阿勤长大后,有一阵在福州打工,暂住在谢天琴家。2022年向我们回忆起来时,阿勤最大的感受是,“没想到,他家吃的喝的,也和我们一样!”言下之意是,本来他认为舅舅舅妈比他们过得好很多。他还记得有几个晚上,很晚了,他陪着舅舅一圈圈地在家旁边的操场上散步。舅舅的心事,很难向人倾吐。
阿勤住在这里的时候,他知道谢天琴对家里的碗筷是规定好的,座位也各有安排。有时候他坐错了,小宇会指出来。阿勤不理他,小宇会再说一遍,“你这个座位坐错了”,阿勤仍然不理,发现“也没什么,就这样了”。谢天琴和吴谢宇都不是当面能够与人冲突的人,他们内心活动很多,但是对于人和人之间的正面冲突,基本不会发生。所以阿勤感慨,谢天琴和吴谢宇母子关系真好,他自己偶尔会和妈妈吵架,但是这对母子从来不会。
吴志坚性格温和,尽力回避和谢天琴产生冲突,但有一个“鸭子事件”,可以看出两人的摩擦。有一年小家庭回仙游老家,吴志坚的妈妈杀了自己养的一只鸭,给他们带回福州吃。谢天琴回到家,想直接将鸭子扔进垃圾桶,不要。吴志坚不接受。两人妥协的结果,是将这只鸭子送给楼上的马老师。马老师看到小两口脸色都不好看,知道刚吵过,不接下鸭子不合适。过了一阵,她买了一件老人家穿的棉袄,让谢天琴送给婆婆。
对于谢天琴的举动,马老师认为她本来就有洁癖,不足为奇。她依然认为谢天琴是贤妻良母,“莆田人对女人的要求,就是听老公听儿子的。我们从没看到她和老公、儿子吵过架,都是他们拿主意”。
或许家庭里的每个人能够真的吵起来,反而对所有人,是一种释放。唯一的任务——读书
读书改变命运,这是谢天琴和吴志坚自己的人生现实,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笃信的价值观。对孩子学习成绩的看重,成为这个小家庭的信念。吴志坚病情带给夫妻俩的压力、他的大家庭需要的支持,以及谢天琴对人际交往的回避,都使得家庭氛围很难放松。吴谢宇在一审判决后写的自述材料里说,“我无法控制自己整体去猜、去怀疑、去揣测别人的心”。如果是在一个情感自由流动、父母非常体谅孩子的家庭氛围中,他根本用不着总是去揣测别人的心。父母的不快乐,作为孩子的他没法理解,他却不自觉地背负上了父母的包袱。
吴谢宇对内在情绪的掩藏,似乎没人看出来。从小他就本能地感受到,展露情绪是一件有羞耻感的事情,妈妈没有情绪,也没有能力处理他的情绪。如果是一台机器就好了,只用达成优秀的考分,而不用有作为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可他越想压抑情绪,情绪越成为他的负担,他在被捕后的自述材料里说,“(即使)身体好多了,然后我都考第一名还当了班长,但我心里面还是天天在害怕在疑心,我从小到大最怕的就是被别人看不起”。
与谢天琴私交很深的马老师,看到的家庭表象,也与吴谢宇的感受完全不同。马老师看到的是“谢老师宽松,甚至有些溺爱孩子”,但对吴谢宇来说,妈妈的爱背后有一种执着的要求,他必须要成为“第一名”“最优秀的那一个”。
2019年吴谢宇被捕后,他跟一审律师冯敏提到,他特别想回到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时光。但是一家人在一起有什么样具体的生活场景呢?吴谢宇好像说不出来,只是说,就是那种“我在做作业,爸爸在客厅看电视,妈妈在厨房忙”的样子。
当吴谢宇把爸爸妈妈的要求内化之后,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高度自律的优秀孩子。2021年写给姑姑的信里,吴谢宇说:“小时候还会和阿勤哥哥一起去放鞭炮,他带我出去玩,大了之后,我都是躲房间里看书,原来还会和阿勤哥哥他们玩游戏机、打牌、下飞行棋,后来都没有了。因为我心里天天越来越痛苦、越来越抑郁,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了,我就都在读书。其实我对读书也谈不上兴趣,我只是不停地在逼自己读书,我以为我考第一名妈妈就能开心、就能骄傲,我觉得我只是一台考试机器,我除了考试之外什么都不会,我除了考第一名之外一无是处。”
表哥很可能成了反面教材,让吴谢宇进一步意识到,只有成绩好,才值得妈妈爱。谢天琴也跟马老师提过,不让小宇跟自己妹妹的儿子玩,因为这孩子“成绩不好,说脏话”。
曾经的小姨夫刘裕宗观察到了,谢天琴其实对儿子控制很多。有一次回老家,读初中的吴谢宇找刘裕宗借手机用,说是给同学回个电话。谢天琴当即呵斥,觉得非常丢脸。
吴谢宇似乎只有回仙游老家,在姑姑家的日子是有生活情境的。他很喜欢姑姑家炖的猪脚,特别香特别嫩,他觉得妈妈做饭不好吃。但是爸爸告诉他,要体谅妈妈,妈妈累,以后不要说妈妈做的饭不好吃。他怀念姑姑和姑丈一起,夏天给他用风油精抓背。有一次他假期住姑姑家,问起刚刚吃的一道菜,“这是什么菜啊,这么好吃?”姑姑才知道,12岁的他是第一次吃菠菜。姑姑推测,弟媳谢天琴有很多讲究,可能觉得菠菜对孩子身体不好吧。谢天琴的弟弟说姐姐除了看书外什么都不干,然后跟人家也是融不入的那种感觉。
谢天琴应该没有意识到,吴谢宇的童年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她的特点——没有朋友。这种没有朋友的局面,并不是“右派”家庭和艰苦的家务活带来的,而是谢天琴要求孩子一心一意读书,时间不要花在任何其他事情上带来的。爸爸相对让人放松,可爸爸在家庭生活中出现得太少。吴谢宇在2021年8月的一审法庭上,哽咽着说,“有爸才有家”。
从小到大的第一名,满足了妈妈,也给了吴谢宇一种舒坦的资本。他后来坦言,只要考第一,即使他其他方面做得不好,所有人都是非常包容他的。这让他内心逐渐变得非常自傲,自己能做到的,普通人做不到。
他说从小到大,他每天都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小世界里。爸爸妈妈提供了一个安全、温暖的家,“我窝在里面,不愿也不敢走出来”。课本和考试提供了一个“完全确定,一切都有标准答案、一切都可以在教科书里找到解答”的理论世界。他在这理论世界里如鱼得水。小说和影视为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虚幻世界,在这里面有“完美的主人公、完美的亲情友情爱情、完美的人生、完美的世界”。他沉溺在这个虚幻世界里,不愿也不敢走出来。
而老家的亲人,他只用嘴甜打个招呼,就不用管了。什么也不用付出,大家就拼命表扬他成绩好。同龄人都是竞争对象,考不过他,他也就懒得关注。吴谢宇提到,其实从小学到大学,也有几个朋友是完全向他敞开心扉的,但是他对朋友却不吐露心声,他活在一种“自己能看透所有人看不到的东西”的自信里。一直到2021年面临一审判决的时候,他才反省到,他从来没有想过老家的舅舅、小姨、大姑是否过得好。他也从来没有问过同学准备考哪里的大学,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成绩好就能受到宠爱,他活在一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里。洁癖背后的尊严
洁癖——后来大家找到了这个词,对谢天琴的一些行为,试图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这种洁癖,是谢天琴在建立一套由自己定义的规则,给自己的小家庭画了一个明确的边界。或许是因为她成长的年代里,盲人父母总在摸摸索索地打扫卫生,把洁净等同于自己的尊严。也或许是在动荡的年代里,她需要用一些强迫行为来恢复对失控的世界的控制,以及她需要用这种行为来抵消内心的某种冲突和恐惧。但对于家庭成员来说,跟有强迫症倾向的人一起生活,会感受到很强的压力。因为这些规则是为处理她的焦虑而定的,对于其他人来说是过度的。
谢天琴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幽默的特质,她没有自我解嘲的能力,也就开不了玩笑。一旦笑话自己,那个本就风雨飘摇的自我,马上就会坍塌。高傲、冷淡、自尊,成为她最有用的武器,所以她总是显得寡言、干涩、紧绷。吴志坚的应对方法,是更深地躲入自己的工作情境,以及需要为吴家大家庭谋利的生活里。
张力文印象中,谢天琴唯一的一次开玩笑,是在青岛。那时候张力文仍在青岛分部当负责人,难得谢天琴联系他,提出希望和几个老师一起去青岛旅游。张力文热情地安排老师们在别墅里住宿,吃喝也招待得很好。谢天琴是高兴的,想开玩笑,但话说出来又显得生硬,“你现在有本事了,你是领导了”。张力文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他理解她,一个不擅长表达的人,开玩笑有些生硬。但张力文也能感觉到,谢天琴对于自己小家庭后来的发展,是感到失落的。
在家庭生活里感受到隔绝的吴谢宇,把心思倾注到了追求考分上。当他被捕后回忆起读书时光,得出的结论居然是,“幸亏我活在应试教育体系里而我又恰好很擅长读书考试,在这体系里我考了第一名就万事大吉了……”
吴谢宇觉得开心的时刻,不是来自他与妈妈的直接互动,而是听到妈妈在别人面前评价他乖,不用大人操心。“我从小一听妈妈和别的老师说,’小宇很乖,学习很自觉,一点都不用父母操心’,我就很开心,我觉得这是妈妈对我的认可,于是我尽全力不让妈妈为我操一点心,我尽全力装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一切OK。”让妈妈开心,似乎是一件困难的事。“唉,反正我就是从没能和妈妈交心,我总是在逃避,这就是我最致命的缺陷啊,我总是在胆小懦弱地逃避啊!” 吴谢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