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朗读”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吴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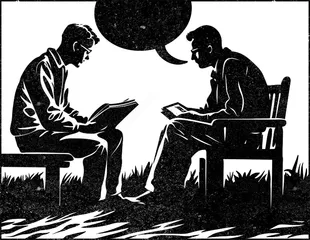 人们常用“书声琅琅”形容学生时代的读书时光,工作以后似乎极少能听到这样的读书声了,其实,并非职场人士不再读书,而是他们好像都认同读书应当默默进行。
人们常用“书声琅琅”形容学生时代的读书时光,工作以后似乎极少能听到这样的读书声了,其实,并非职场人士不再读书,而是他们好像都认同读书应当默默进行。
但也会有例外,我所在的办公室里,就常能听到阵阵低沉而浑厚的朗读声,尤其是每逢重要稿件需要校对之时。面对同事的“问号脸”,朗读声的主人解释说:“校对稿件,相比用眼睛看,我更喜欢用嘴巴读!”当时,我并未细想,而是将这稍显“异类”的举动及其解释埋在心里,直觉告诉我其中必有深意。
果然,在近期参加上级单位组织的一次业务培训时,我的直觉得到了回应。培训中,来自新华社的记者老师介绍说,“出声读”或者“唱校”,是新华社、新华网对重大稿件的一种校对习惯,一般分为一人完成和多人合作两种形式,“读出来,确实比只是看在减少差错方面有效,但也比较耗时间”。虽然老师没有再列举相关的统计数据作为支撑,但也从侧面印证了“用嘴巴读”或者“读出声音”的重要性。
这件事还让我联想起前日偶然看到的一本书,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的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所著的《阅读史》,该书在“沉默的读者”一章中全面接受了匈牙利专家布洛夫一派的学说,即“朗诵是古人正常的阅读方式,与之相对,默读是一种由特殊原因导致的异常”,而仅仅在一个注解中谈及了美籍学者克诺克斯的见解。事实上,正是克诺克斯的见解撼动了布洛夫学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统治地位。
克诺克斯在其著名论文《古代的默读》(该文极大地推进了阅读史的研究)中指出,虽然古人惯常的阅读方式是朗读,但是默读也并不罕见,具体的使用要视具体情景而定。他说,“任何具有即便最微弱文学性的作品均为朗读而写”,换言之,若要欣赏一部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则适宜朗读,若要从事讲求工作效率的学术研究则适宜默读。
在我看来,克诺克斯的观点同样适用于现代。总结起来,朗读常与音乐、情感相系,需要调动各类感官抑或形象思维;默读则是一种更为专注、更加快速的阅读方式,需要运用概念、判断、推理或者抽象思维。现代与古代不同的地方或许只有一点,那就是:虽然今人惯常的阅读方式是默读,但是朗读也并不罕见,具体的使用要视具体情景而定。
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我们对于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近年来大声疾呼、身体力行的“吟诵”传统便有了更多的体认。叶嘉莹认为,杜甫的诗之所以写得这么好,声音这么好,他的秘诀就是吟诵,是“新诗改罢自长吟”。叶嘉莹还进一步引用了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写过的一本书——《诗是怎样作成的》,书中说:“当我一个人摆动着双臂行走时,口中发出不成文字的喃喃之声,于是而形成为一种韵律,而韵律是一切诗歌作品的基础。”也就是说,诗的文字是随着它声音的韵律而形成的。所谓字从音出、字从韵出,懂得了吟诵,好诗会自己“跑出来”。
有研究认为,人的大脑有左、右半边之分,一半是理性的,一半是感性的;理性的学问是知识,比较死板的,感性的学问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鲜活的。学会吟诵可以培养人感性的那半边头脑,感官“打开了”自然可以创作出“兴发感动”的好诗。个人之见,吟诵其实就是朗读之一种。
以这样的视角来理解朗读,我们或许能发现并重视它在校对等实用功能之外审美的价值,在这个人文氛围式微、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或许更应该光复它应有的地位。 朗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