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学何时代之别”
作者:卜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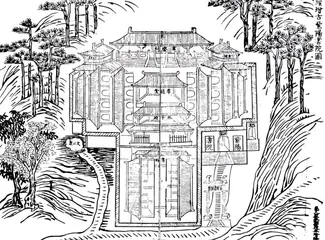 那一年的春节,姚鼐是在泰安度过的,然后去了长清的灵岩寺,从那里取道回京。乾隆四十年二月,姚鼐携眷归乡,暮春时节已回至桐城故园。一个杰出的学者和文章家离开了,对四库馆的影响则是微乎其微。
那一年的春节,姚鼐是在泰安度过的,然后去了长清的灵岩寺,从那里取道回京。乾隆四十年二月,姚鼐携眷归乡,暮春时节已回至桐城故园。一个杰出的学者和文章家离开了,对四库馆的影响则是微乎其微。学者与编辑不同,学者与学者的差异也很大。即以“五纂修”论列,翁方纲、邵晋涵、周永年、汪如藻在编纂过程中很投入,很下力气,时常为珍稀文本的发现欣喜,姚鼐则有些格格不入。此与乾隆帝的选择性题诗表彰相关,而皇上对错讹的苛责,对严谨考证的奖誉,也不无暗示和导向意味,令在事者更加重视细节,重视考辨。厘清端绪,求真求实,自是兴修一部大书的准则,而一切随着皇上的指挥棒转,撰写提要也须颂圣和颂清,又与之不无抵牾。“五纂修”是一个友好亲切的小班子,可在讨论时会出现对程朱理学的嘲讽,总纂也会在文稿上大加点窜,让姚鼐觉得不能忍受。《惜抱先生行状》写道:“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掊击讪笑之不遗余力。先生往复辩论,诸公虽无以难,而莫能助也。”姚鼐在馆时,于敏中多次延揽,在其离开后也命人转述爱赏栽培之意,皆处之淡然。翁方纲知他决计不会再回来,临别时请求留言,曰:
诸君皆欲读人未见之书,某则愿读人所常见书耳。
作为纂修官,渴望读到稀见版本当然不是什么错;而以学术论则落于二义,姚鼐此言所蕴含的哲理,至今仍当为学界所深思。
姚鼐对《四库全书》究竟有什么贡献,今天已无法完全弄清。而其留下了88篇提要稿,收入《惜抱轩书录》,可视为一份真实的见证。以他在馆的时间计,平均不到六天就要写出一部书的提要,要翻阅、比勘、考索作者事迹,梳理版本流变,也要概括其内容,做出客观评价,殊非易易可为。多数人拟写的提要限于一个领域,如《礼》《易》《春秋》,而姚鼐所写提要覆盖经史子集,范围较宽。盖博坚在《皇帝的四库》中,有一节论述“姚鼐的提要稿”,以《古史》等四篇为例,将之与《四库全书总目》比较,颇下了一番功夫。限于篇幅,仅以苏辙《古史》做一点对比。姚鼐在提要分纂稿中写道:
辙为是书,当退居颍上之时,年已老而识愈高。故朱子取之,谓如所云“古之帝王,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其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谷”。此语岂马迁所及!又惜其所云“帝王之学,以无为宗之,类杂于二氏”。此苏氏之所短也。秦火之后,经籍散亡,司马迁网罗放失,以不世出之才,创千古之业,其功伟矣!而议论以屡辩而易明,考证至后世而益密,辙因前人之文修饰之,固不可与初创者比,然迁多爱好新奇之过,辙依儒者之义,纠正其失而补救之,亦可谓司马氏千载之益友矣。
既高度肯定司马迁的《史记》,也引用朱熹评价,基本肯定苏辙之作的价值,认为对《史记》有所匡补。而《四库全书总目》此条已改得面目全非,曰:
班固论迁之失,首在先黄老而后六经,辙所更定,乌在其能正迁耶?……平心而论,史至于司马迁,犹诗至于李杜,书至于钟王,画至于顾陆,非可以一枝一节比拟其长短者也。辙乃欲点定其书,殆不免于轻妄。至其纠正补缀,如《史记》载尧妻舜之后,瞽叟尚欲杀舜,辙则本《尚书》,谓妻舜在瞽叟允若之后;《史记》载伊尹以负鼎说汤、造父御周穆王见西王母事,辙则删之;《史记》不载祷雨桑林事,辙则增之……其去取之间,亦颇不苟。存与迁书相参考,固亦无不可矣。
像是有意与姚鼐较劲,一上来就大加挑剔,对该书多有指责否定。修订者还特地节录了《朱子语录》的文字:朱熹说吕祖谦宗太史公之学,自己与之辩论时,认为“《古史》言马迁浅露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指斥朱熹平日瞧不上苏辙,因与吕祖谦辩难所激,“此时反为之左袒”。但兜了一个圈子,仍不能不承认《古史》的参考价值。
两相比较,各有千秋,原作似稍胜一筹。姚鼐言简意赅,不着痕迹而褒贬自见,其所提出的“议论以屡辩而易明,考证至后世而益密”,持一种发展的学术史观,尤觉难得;《全目》援据细密,论证周详,逐节辩驳,由作者苏辙扯到宋儒之争,顺便给朱熹戴上一个有意偏袒的帽子,则有嫌武断。而琐琐碎碎写到最后,仍无法超越或否定姚鼐的意见,反显得行文别扭,自相矛盾。
由《古史》的两篇提要,或能见出汉学与宋学的不同色泽,亦显露了至今作为学术主流的汉学之软肋。在为门人钱坫书序时,姚鼐肯定了汉儒“贯穿群经”的成就,也分析其“怪僻猥碎”之弊,指出宋儒论学“得圣人之旨”的意义,论曰:“且夫天地之运,久则必变。是故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学者之变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齐其弊,则所尚也贤于其故,否则不及其故,自汉以来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蒐而遗其巨,夫宁非蔽与?”平实而论,所说皆汉学之弊,顶级人物如戴震亦在所难免,又何况等而下之者?
对于辞职,姚鼐毫不回避曾经历过内心的纠结:姚氏先世朱紫相接,而今朝中已没有什么人了,为家族计实不应请辞;更为实际的是他从来都不富裕,一大家子人全靠自己养活,辞官便舍弃了俸禄,以及在四库馆的那份优厚饭食银。但为了传承“桐城文章”,为了矫正汉学之偏,也为了静下心来读书著述、择才而教,他还是决然离去。何以为生?姚鼐能够做的只有教书和写文章。约一年半之后,好友朱孝纯转任两淮盐运使,邀他主讲扬州梅花书院,总算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仅过了两年,妻子突然病逝,失去贤内助,子女尚幼,铭曰“子女各二,幼不甚知哀,而长女之痛不可闻”,读之催人泪下。姚鼐扶柩还乡,本待料理完丧事后再赴扬州,岂知孝纯因病解任,返京去也。无奈之下只得另谋生计,忽忽又是两年,方才受邀主讲安庆敬敷书院。即便如此,也未见他后悔当初的辞官之举。
姚鼐恬淡温润复劲节内蕴,据其门生回忆:“先生外和而内介,义所不可,确然不易其所守”;“先生色夷而气清,接人极和蔼,无贵贱皆乐与尽欢,而义所不可,则确乎不能易其所守”。这里的“义”,应指对中华道统的自觉维护和持守,对从孔孟到程朱的沉沉一脉的尊崇。他本来是希望超然于汉宋之争的,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夫言学何时代之别?多闻择善而从,此孔子法也;善,岂以时代定乎?
大哉此问!他也不止一次说汉学与宋学各有优劣,应该互补,最后为情势所激,高扬起宋学的旗帜,也说了一些有些失态的过头话。学术史上的纠葛,真是剪不断,理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