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诺》:难以逃避的身份
作者:孙若茜 《承诺》里写了四场葬礼,更准确地说,它就是用四场葬礼搭建的。小说的四个部分分别由四个人物来命名:妈、爸、阿斯特丽德、安东,他们正是葬礼上被送别的人——40年的时间里,这个南非白人家庭送走了绝大部分成员,只剩一人。
《承诺》里写了四场葬礼,更准确地说,它就是用四场葬礼搭建的。小说的四个部分分别由四个人物来命名:妈、爸、阿斯特丽德、安东,他们正是葬礼上被送别的人——40年的时间里,这个南非白人家庭送走了绝大部分成员,只剩一人。故事是从母亲的葬礼开始的:临终时,她留下遗愿,要将黑人女佣萨洛米所住的房子赠予她和她的孩子——是萨洛米陪伴她走完了最后的人生。丈夫亲口同意,并做出了承诺。但他食言了。听到这个遗愿和承诺的人,还有家中最小的女儿阿莫尔,于是母亲死后,她成了唯一一个追索承诺何时兑现的人。
阿莫尔的母亲走后大约10年,父亲在自己经营的爬行动物园被蛇咬死。又一个10年,姐姐阿斯特丽德被抢劫者枪杀。接着,十几年后,哥哥安东自杀了。阿莫尔早年就离家自谋生路,但在为每一场葬礼回家时,她都不忘催促家人实现承诺,只是始终没能成功。直到最终,只剩下她去独自面对。
“四场葬礼,每次一两天,中间没有任何叙事性的东西。你可以在四幅不同的快照中得到一个家庭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很自然地就能想到将葬礼设置在不同的年代,以及通过这些时间上的大跳跃是在传达什么。不仅关乎政治,也关于人们的生活。”作家达蒙·加尔格特说,“时间和时间的流逝,是这本书真正的主题。”
达蒙·加尔格特1963年出生,17岁就开始出版作品,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写作40多年,有了十几部作品。在《承诺》之前,他还有两部小说入围过布克奖的短名单。加尔格特早期写过关于自然的诗歌,有评论批评他无视南非的现状,这无疑给他带来了刺痛和反思。他曾经说,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有望给予南非作家写作的许可。只不过,如今再次提起这个话题,他说:“目前的变化还不足以让这一切成为可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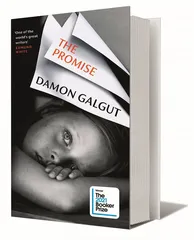 小说《承诺》
小说《承诺》
三联生活周刊:《承诺》的扉页上有一段费德里科·费里尼的话,是他讲述的一个生活片段:一个金鼻子女人问他:“为什么在你的电影里,连一个正常人都没有?”能说说你为什么选了这段话吗?你怎么理解所谓“正常”与“不正常”?“正常”或“不正常”会是你对自己笔下人物的一种判断标准或者写作追求吗?
达蒙·加尔格特:因为我很喜欢这句引文,我也非常喜欢费里尼……不过也是因为它与小说中的人物比较契合——他们都觉得自己是“正常的”,但在其他地方的人看来,也许显得特别奇怪。
我个人认为,“正常”只是一个绝对的相对概念。没有什么行为或情感是其他人未曾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只有在对它们不熟悉的人眼里才显得奇怪。当然了,如果从某个角度来看,即便是我小说中的人物,也会觉得他们自己是完全正常的。
三联生活周刊:记得你曾经说过,《承诺》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分别代表了你自己的一些不同的面向,能不能具体说说?
达蒙·加尔格特:任何一位作家要塑造一个令人信服的人物,都必须从自身的本性中汲取一些元素。当然,这不代表你就等同于你的人物,而是意味着你必须在某些方面与人物的核心品质(甚至是一些可怕的品质)共通。如果你将个性想象成富有弹性的东西,你会从自己身上选取某些特点,再将其拉伸为一种全新的有趣形态。通过找到你自己身上与小说人物的一些相似部分,你就能想象成为一个不是你的某个人是什么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本书中,你最偏爱哪个人物?他/她恰好也是你在这本书里书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吗?
达蒙·加尔格特:我在塑造哥哥安东这个人物时,体会到了许多文学创作的乐趣。他是个遭到损害、迷茫、生气但又充满自我意识的人,这些都是写作的好材料。和谐的人物就少了很多乐趣!至于写得有多成功,我留给其他人去评价好了。
三联生活周刊:近两年的一次采访中,你提到的写作计划是一部短篇小说集,那些小说共同的主题是“出门在外的人”。《承诺》中的阿莫尔恰巧也是一个出门在外的人。对你而言,“出门在外的人”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为什么要着力去写他们?
达蒙·加尔格特:我年轻时有很多年都在躁动不安中度过,在全世界旅行,去过许多地方。如今,我已经没有精力或欲望做这种旅行了……我认为,当人远离家和熟悉的生活,就会变得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当社会规约消失不见,也许会变得更像自己。人们远离家的时候,会做出一些在熟悉的人中间不会做的事情。对我来说,这很有意思,并且能打开许多叙事上的可能性。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阿莫尔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始终执着于兑现承诺的人?这与她离家出走有关吗?或者,她只代表人性中非常偶然的一部分,毕竟没有多少人会像她那样被闪电击中?
达蒙·加尔格特:这取决于你怎么看阿莫尔。她是这个家族里有某种道德冲动的人,但这使得家人们视她为怪人。也许他们是对的!她身上绝对有些怪异和“另类”的东西。有人问我是否有意让她显得“神经多样性”,也就是自闭症,我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可能,但我没法肯定地告诉你。我只是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并不确定她为什么会这样。
三联生活周刊:安东这个人物在逃离军队之后,高调地宣扬自己“将会走上一条与之前不同、与其他人不同的人生之路”,这条路为什么是写作?
达蒙·加尔格特:他想象的道路不只与写作有关。他认为自己是在脱离种族隔离的国家机器,开辟通往未来的道德之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是成为一名作家,因为他可以构想和塑造自己的故事。当然,他的计划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实现……他试图写的小说也没有顺利完成。
三联生活周刊:萨洛米的视角是故意被你隐去的吗?
达蒙·加尔格特:是的。在许多方面,她都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但雇用她的白人家庭没有看到或听到她……正如目前在南非,数百万像她一样的黑人女性没有被她们的雇主(或国家)看到或听到。我想让她的“不可见性”变得显眼,让读者感到不适。这是这本书的核心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我在阅读中有一种感受,相比女性角色的执着和勇敢,书里的男性角色显得相对懦弱、矛盾,这是你的一种有意识的表达吗?
达蒙·加尔格特:我不是这样看待他们的。男人也许的确是懦弱、矛盾的,但他们也处于父权制的顶端。尽管他们受到了伤害,但他们比女性更强大。女性大多扮演着她们被——加尔文主义的、虔诚却无情的社会(我就在这样的社会中长大)——期望扮演的角色,也就是作为男人收集的“美丽”的战利品。
三联生活周刊:在书中,你写到阿莫尔初潮时的尴尬,在一个篇幅不长的葬礼中,这是很特别的一笔。你写作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安置了这个细节的?在我的阅读经验里,这似乎是很少会被男作家处理的问题。
达蒙·加尔格特:没错,其实我自己也很害怕触碰这类话题。这不是男人可以共情或理解的经历。不过我和我所有的女性朋友都谈过,她们大多对我非常坦诚,告诉我她们第一次来月经时的感受,以及这对她们成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我将它写进书里,因为这本书是以阿莫尔在几十年后进入更年期并出现潮热结尾。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读者真实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衰老的过程。我也可以在男性人物身上用同样的策略——事实上,我至少对其中一个人物这么做了,但对阿莫尔来说,这样更直接、更引人注目。身体会变化,我们都会达到力量的顶峰,然后衰退。我想让人们感受到这一点。
三联生活周刊:同样让我印象很深的是阿莫尔样貌的变化在其他人眼中的映射,尤其这种变化对姐姐、对德西蕾产生的影响。
达蒙·加尔格特:阿莫尔外貌的变化与上一个问题有关。我们当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一个看似平凡的人在短短几年内变得有魅力是完全有可能的,反过来也是如此。在阿莫尔身边的女人看来,女性的权力来自外表,所以,当一个在她们看来年轻、没有吸引力的女人(因此也无关紧要)突然变得引人注目,会被她们视为一种威胁。这种反应并不罕见,也不仅仅存在于女性之间。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笔下40年的时间流逝中,人物非自然死亡、政权更迭,少有单纯地由时间改变的东西——除了刚刚说到的一个人的样貌,这是你着重书写了阿莫尔外貌变化的原因之一吗?你怎么看待时间?
达蒙·加尔格特:时间是所有事物发生变化的媒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面孔、我们的道德……它也是政治变化的媒介,但就这本书——以及我的国家——而言,这似乎是时间未能改变的领域。
三联生活周刊:说到书中的人物相继非自然死亡,这样的情节安排是因为你想坚持坏人一定要受到惩罚,背弃承诺的人要付出代价吗?这使你的故事看起来更带有寓言的意味。你如何理解“承诺”?
达蒙·加尔格特: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不,死亡不是作为对这些人物的惩罚。它恰好是所有人生命的终点,因此也是穿越时间的旅程到达终点的时刻。由于我的小说是围绕着四场家庭葬礼展开的,我必须决定这些人中的每一个如何迎接他们的结局。在我看来,如果你不是老死,那么你要么死于疾病,要么死于事故,要么被别人杀死,要么自杀而死。我想在书中囊括这四种可能性。
回答第二个问题:我对待承诺是非常认真的。如果你对某人许下承诺,你基本上是在说,无论生活在你的道路上制造了什么障碍,你都会超越命运,兑现承诺。这是一个很大的承诺,不能轻率做出。当然,我所写的这个家庭根本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承诺。
三联生活周刊:在将近20年前的一次采访里,你谈到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有望给予南非小说家写作的许可,“诸如爱情之类的东西……在种族隔离制度崩溃之前,它被认为是有点不道德的主题”。能不能说说你当时谈及“许可”时,认为它主要来自什么,外部环境还是作家自身?这种“许可”如你所预料地发生了吗?
达蒙·加尔格特:数十年来,在南非,我们生活在一场紧迫的道德危机的中心。当然,我说的是种族隔离。在这种情况下,写一些更私人的话题似乎是错误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好像它们比我们宏大的政治闹剧更重要似的。从理论上讲,种族隔离制度结束时,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我当时所说的似乎是一场深刻的变革。但正如我希望我的书能说明的那样,目前的变化还不足以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唉!爱在未来的某个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就你个人近20年的写作主题而言,有一种更加贴近政治和历史的走向,为什么?这种选择和你早期写作所受到的批评有关吗?
达蒙·加尔格特:不,我不会基于批评来选择主题。但在我20多岁的时候,当我完全意识到我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时,我不可能把目光从历史上移开。我们都被自身所处的历史时刻塑造,但在南非,这一事实明显得不可避免,让人痛苦。我希望不是这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你仅仅是一位作家,而不是南非人,你觉得自己会去书写什么主题?
达蒙·加尔格特:我毫无头绪,因为我就是南非人,这个身份塑造了我,决定了我是谁。这一点无法逃避,甚至连我的想象力也不行。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读者脱离南非的政治、历史背景去阅读你笔下的故事,忽略掉你笔下的人物背后的隐喻,你认为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吗?这样做会让读者在阅读中失去更多,还是得到更多?
达蒙·加尔格特:我假想我的许多读者都不太了解南非。对我来说,吸引这些读者,引起他们的兴趣也很重要。换句话说,我希望我的书首先在普遍人类的层面上是成立的。如果你对故事中的人物不感兴趣,你就不会继续读下去。就这么简单。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小说中出现了很多动物,除了爬行动物园里的冷血动物,还有猫头鹰、野鸽、胡狼等,在你的笔下,它们和人类同样享有第一人称,能说说你这样写的用意吗?在你看来,这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
达蒙·加尔格特:对我来说,这本书一直关乎打破边界。我已经打破了所有的叙事规则,这让我感到自由。所以我想我也要打破一些其他的边界,那些位于我们认知边缘的边界。我不知道鬼魂或精灵是否真实存在,但我也不知道它们是否真的不存在。所以我认为,在一种想象的行为中,让我的思想超越常规边界是正当的。谁知道外面有什么呢?这个世界无限神秘,无限有趣。
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几个重要的文学奖项都颁给了非洲作家,因此那一年被很多人称为“非洲文学年”,就你的观察和感受,这给非洲的写作者带来了什么切实的改变吗?两年过去了,“非洲文学年”还在持续为非洲文学发挥作用吗?
达蒙·加尔格特:很抱歉地说:完全没有。我们装聋作哑的政府至今没有对我获布克奖做出正式回应,而且据我所知,对于你提到的这些非洲作家和书籍的兴奋感来自非洲之外的地方,而不是来自非洲内部。这是这个大陆的悲剧的一部分,它不关心自己的作家。我不指望这种情况会很快改变。